唐朝,李贺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没想到整个唐朝都没人能接上,直到宋朝,一个酒鬼在喝醉后竟随口说出了下半句… 盛唐的气象,放到今天想,几乎是超现实的。长安夜市的灯一盏盏亮下去,能一直亮到城外驿道口,连驼铃声都带着点不舍得散场的味道。酒肆里,有人拍着案吟李白的“将进酒”,茶棚边也有人低声背杜甫的“国破山河在”。诗在那个时代不是书斋的私货,而是空气里都能闻到的香气。就在这样一个余韵未尽的年头,河南福昌出了个李贺。 这孩子的出身,说起来有光,但那光早就像旧铜镜的亮面,被一层暗锈盖住了。他的高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可几代人过去,家道衰得厉害,到了父亲李晋肃手里,不过是个边地小吏。院子深处青苔爬上了石阶,风吹动的是松木门的吱呀声。父亲早逝,家里空得很,灶台常年冷着,连油烟味都稀薄。 李贺偏偏不安分。七岁那年就能写诗,写得快得惊人。韩愈、皇甫湜听说了,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思去看。他提笔那一刻,屋子像被什么按了静音键,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诗成之后,两位大文人对视一眼,那神情,像是认出一块未经打磨却已经会反光的玉。李贺平日出门,不带什么行李,只带个破锦囊,骑着高大的黑驴在村路上晃。遇见一抹好颜色,或脑子里闪过个奇特的句子,就停下,写在纸片上塞进去。那锦囊里装的,是他对世界的捕获。 按理说,少年成名,走科举路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唐代有条“嫌名律”,父亲的名字里若有字与科目名同音,子孙便不得应试。他父亲名中带“晋”,与“进士”同音,门就这样关死了。韩愈替他抱不平,写下“父名晋,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为人乎?”这种话,可制度的门锁不会因一句辩白而松开。他只得靠荫补做了个奉礼郎,从九品的小官,既无实权,也无舞台。长安的三年,他看尽官场里那些冷眼、轻笑、虚与委蛇。更要命的是,年轻的妻子病逝,让他的诗句染上了彻骨的寒色。 他写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是胸中尚有的热血。可更多时候,他的诗像古画里的残山剩水,墨色处浓得沉重,留白处空得发凉。从长安回洛阳的路上,他写了《金铜仙人辞汉歌》。魏明帝迁走汉武帝宫里的金铜仙人,这段史事,被他写成一场关于盛衰的寓言。诗到末尾,“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像是从胸口逼出来的叹息。它不止在说王朝兴替,也在映照自己——若天有情,早该衰老。长安的文人们纷纷试着对下句,不是气力不够,就是意境塌了。时间久了,这句成了唐人眼里的“奇绝无对”。 他二十七岁就走了,留下不多的诗篇,却篇篇锋利。那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唐诗的天幕上高悬了两百年,没人能为它续完。 等到北宋,战火平息,文坛又热闹起来。石延年,字曼卿,文名不俗。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又提起李贺那句,叹唐代才子如繁星,也没能对上。酒正热的时候,他放下杯,随口道:“月如无恨月长圆。”这不是旁人绞尽脑汁的对句,而是像水面落下一粒石子,涟漪自然开去。史料可见于司马光的《续诗话》,记得很清楚——世人以为与上句可敌。至于传说里那天他酒意正浓,话是信手拈来,这只能说是坊间添的故事,添得倒也好听。 后来的人更贪心,把李白的“把酒问青天”、苏轼的“举杯邀明月”,和这两句放在一起,拼成一副集句对联: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工整是工整,意境也远,但那已是后人的巧思,不是古人一气呵成的手笔。 那句上联,从中唐走到北宋,再被后人放进对联里,像一条河绕了很大的弯才汇入大海。想起李贺,一个家道中落的年轻人,骑着驴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道上,锦囊里是刚写下的句子;再想起石延年,在灯火下举杯放下杯,说出那句圆满的下联。两个画面隔着几百年,却像能在某个黄昏的风里擦肩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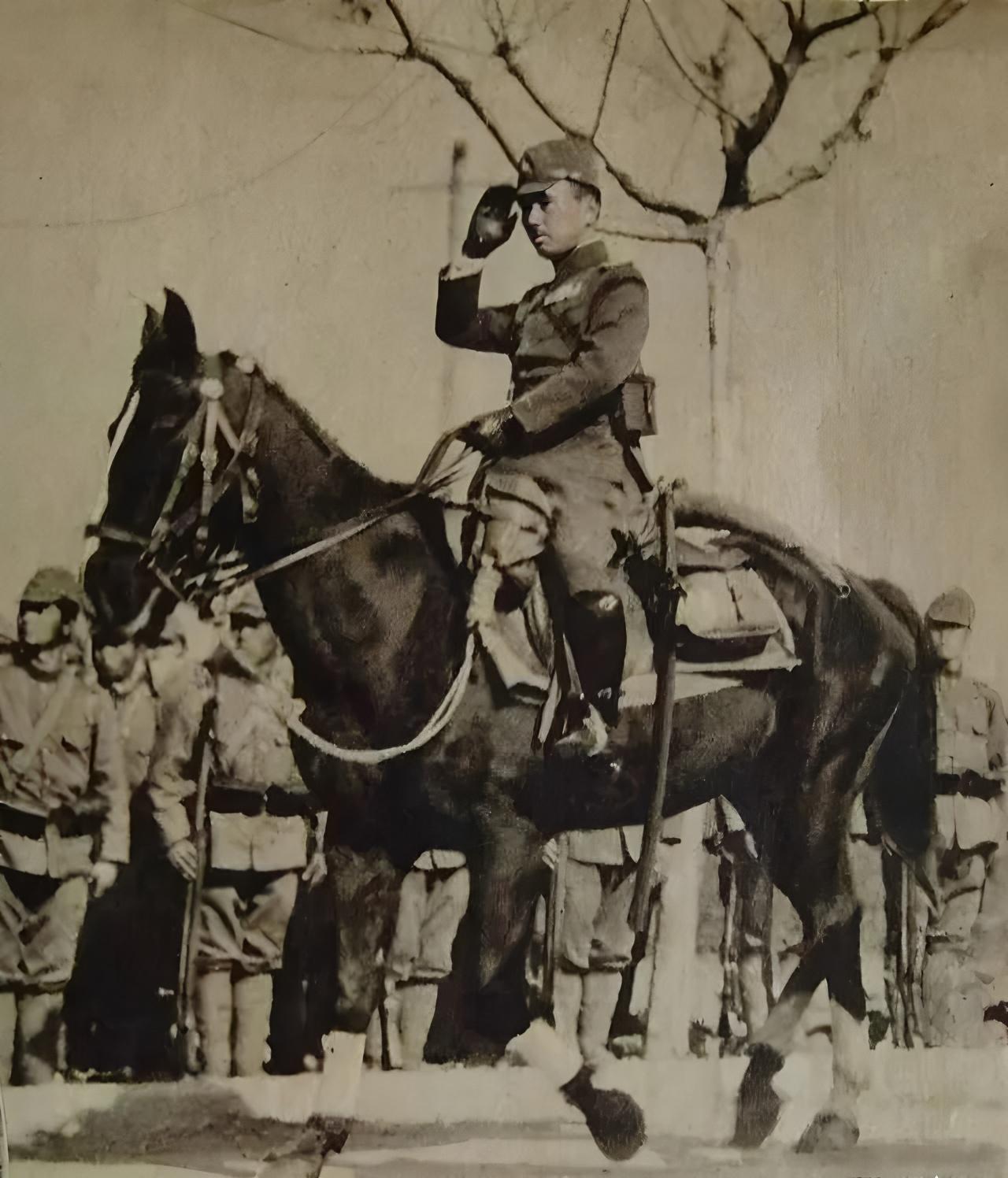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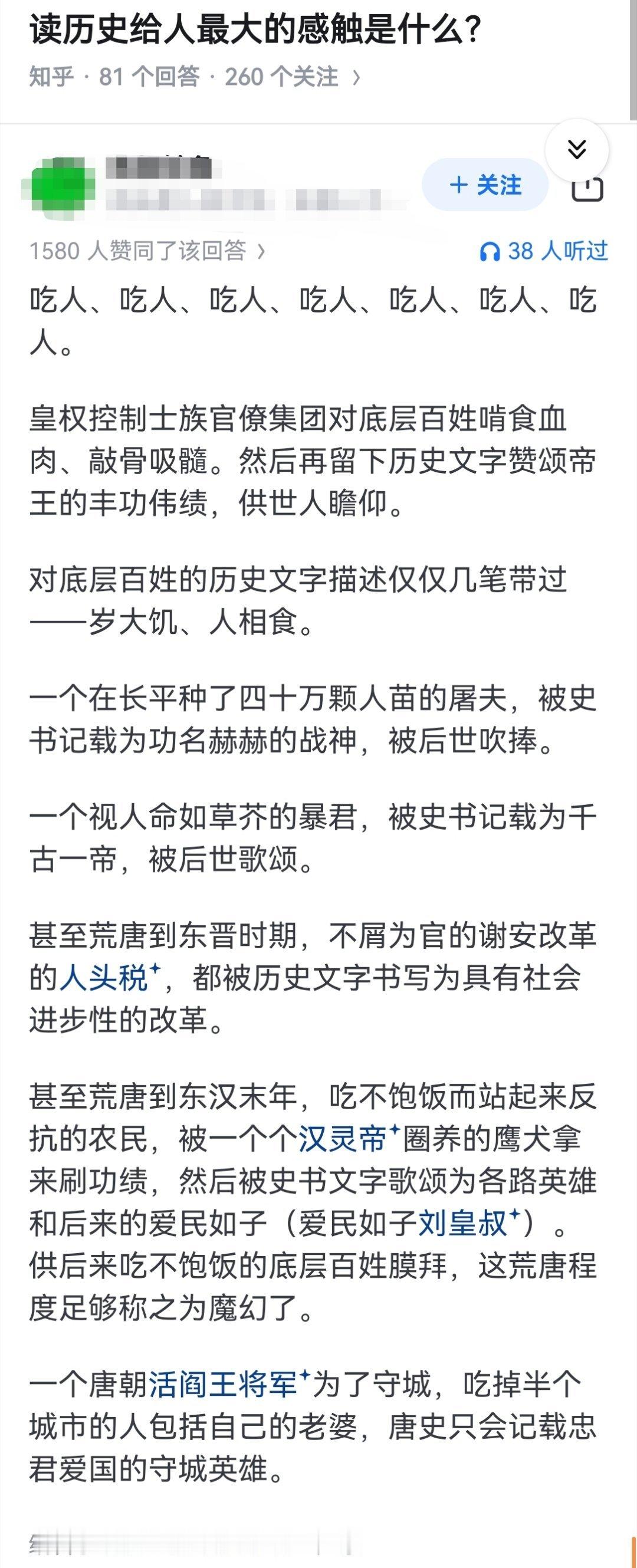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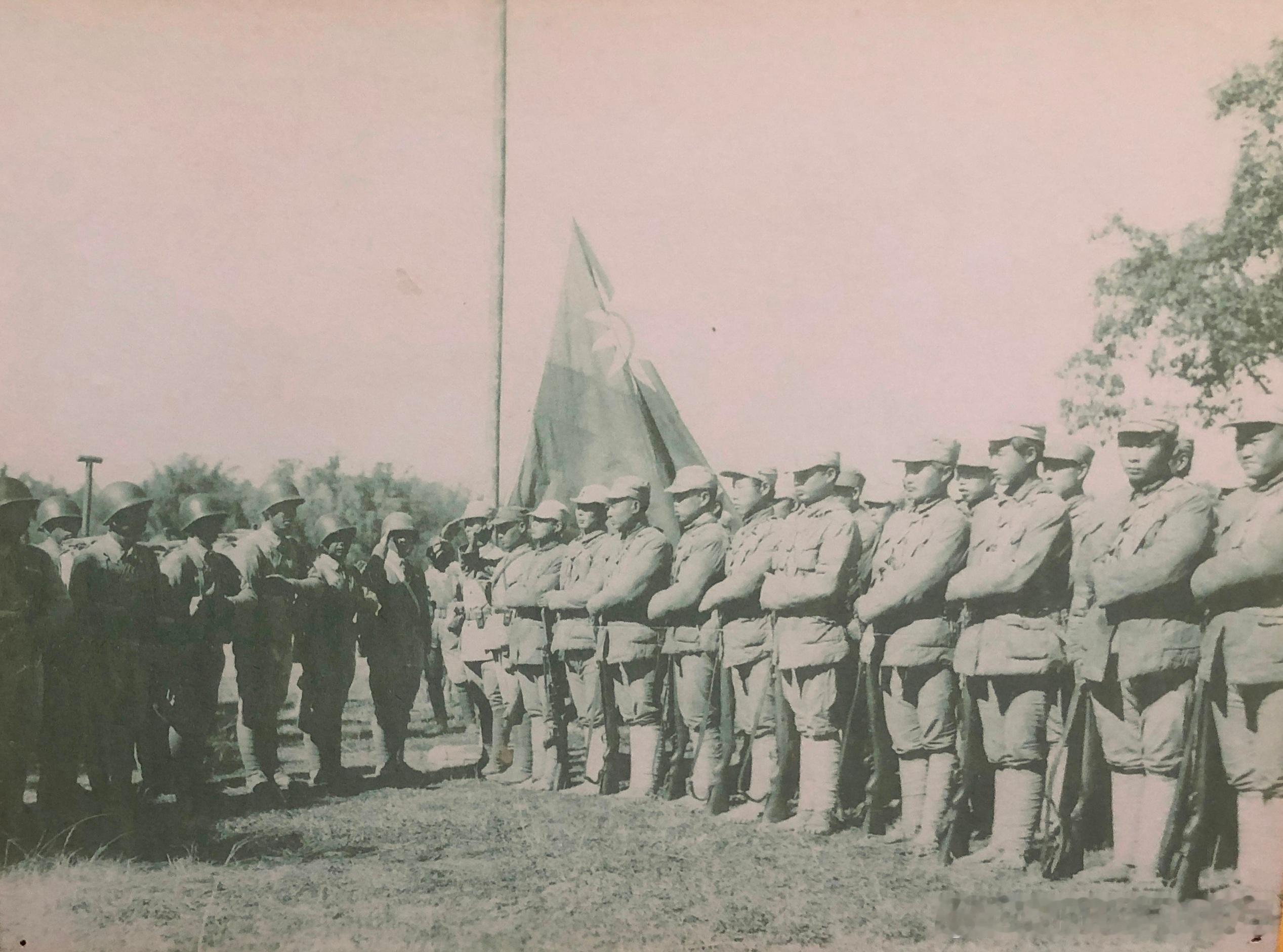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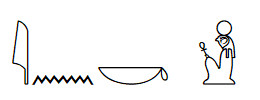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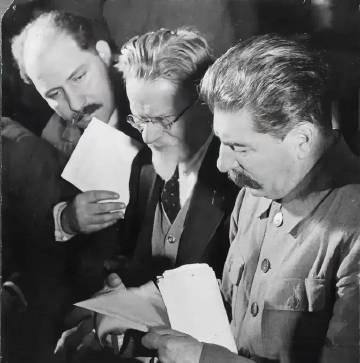

境·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有志人不凡
境·界 回复 08-12 09:02
这样对也行,人因有心人不凡
患不均 回复 境·界 08-12 14:41
不行,选择和结果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