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知青王文清发烧39度,赤脚医生张秀巧看后,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他说打针的地方还痛,张秀巧扒下他的裤子:“奇怪,明明不红不肿啊?”谁知,几天后,张秀巧却因此成了他的女朋友。
在这年秋天,张家坪生产队里出了件有意思的事儿。
城里来的知青王文清淋了场透雨,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
这小伙子烧得满脸通红,额头上都能烙饼了,同屋的知青赶紧把村里的赤脚医生张秀巧请来。
张秀巧这姑娘在十里八乡可是出了名的能干,虽说没进过正经医学院,可跟着老中医学了七八年,头疼脑热的病手到擒来。
她挎着印着红十字的帆布药箱风风火火赶来,伸手往王文清脑门上一搭,眉头就皱成了疙瘩。
这温度少说也有三十九度,要搁在体弱的老人身上,怕是得烧出毛病来。
"得打退烧针,要不晚上该说胡话了。"张秀巧边说边从药箱里翻出玻璃针管。
那年头农村条件差,针头都是反复消毒用的,针管在煤油灯上烤了烤算是消毒。
王文清趴在炕沿上,耳朵尖红得能滴血,虽说都是治病救人,可让个大姑娘给屁股上打针,搁谁脸上都挂不住。
要说这张秀巧也是个利索人,三下五除二就把针打完了。
临走前还嘱咐知青们给熬点姜汤,又往炕头放了包退烧药。
按说这事儿就该翻篇了,可第二天王文清又找上门来,说是打针的地方疼得厉害。
张秀巧心里直打鼓,别是感染了吧?
赶紧让人脱了裤子检查,结果左看右看,针眼周围白白净净,连个红点都没有。
这事儿后来成了村里人的笑谈,有人看见王文清隔三差五往卫生室跑,今天说头疼明天说腿软,张秀巧开始还认真检查,后来发现这小子就是找茬搭话。
要说这王文清也够鸡贼,知道张秀巧喜欢文化人,就变着法儿显摆自己认字多。
今天帮卫生室抄个药方,明天给讲个城里的新鲜事儿,一来二去还真把姑娘的心给捂热乎了。
要说这俩人的缘分,还得从王文清下乡说起。
1969年那会儿,城里的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往农村扎根。
王文清本来在城里念到高中,写得一手好字,说话办事都透着机灵劲。
可偏偏赶上政策变化,说好的回城指标说没就没了。
家里老母亲急得直抹眼泪,最后捎信来说:"实在回不来就在当地成个家吧。"
张家坪这地方山清水秀,可日子过得紧巴。
村里二十好几的光棍能凑两桌麻将,突然来了群细皮嫩肉的知青,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都跟着转。
张秀巧本来在村里就抢手,说媒的能把门槛踏平,可她愣是没瞧上哪个,这姑娘心里憋着股劲,非得找个肚子里有墨水的。
王文清这场病生得真是时候,自打那次打针之后,他往卫生室跑得比上工还勤快。
今天说伤口痒痒,明天说浑身没劲,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村里人看破不说破,有时候还故意逗他:"文清啊,你这两天脸色可不大好,要不要再让秀巧给扎两针?"
要说张秀巧开始是真没往那方面想,她天天忙着给村民看病,东家接生西家接骨,哪有工夫琢磨这些弯弯绕。
可架不住王文清会来事儿,见天帮着整理药材,还把卫生室的墙面用报纸糊得整整齐齐。
最绝的是有次村里要搞卫生宣传,王文清熬了两个通宵,用毛笔写了二十多张防疫标语,把公社来的干部都看直了眼。
转眼到了1975年开春,地里的麦苗刚冒头,村里就传开了喜讯,张秀巧要嫁人了。
结婚那天看热闹的村民把新房围得水泄不通,几个老婶子扒着窗户数嫁妆,看见新娘子手腕上戴着块上海牌手表,啧啧称奇:"到底是文化人,这礼送得体面。"
婚后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王文清在地里干活是把好手,张秀巧的卫生室也越办越红火。
转过年来添了个大胖小子,小两口的日子更有了奔头。
有时候收工回家,王文清抱着儿子在院里转悠,看着灶台前忙活的媳妇,总觉得这场病生得值当。
要说这事儿里头最乐呵的还得数王文清的老母亲,老太太从城里寄来红绸被面,信里写得明白:"踏实过日子比啥都强,待人家姑娘好些。"
这话传到村里,大伙儿都夸王家祖坟冒了青烟,找个媳妇又能干又俊俏。
如今四十年过去,张家坪的老人们提起这事还津津乐道。
村头卫生室的墙上还留着当年糊的旧报纸,发黄的纸页上依稀能看见"赤脚医生向阳开"的标题。
王文清两口子早搬进了县城,可每年清明总要回来给祖宗上坟。
经过当年知青住过的老房子,两个白发老人总要相视一笑,那场大雨浇出来的缘分,愣是暖了半辈子的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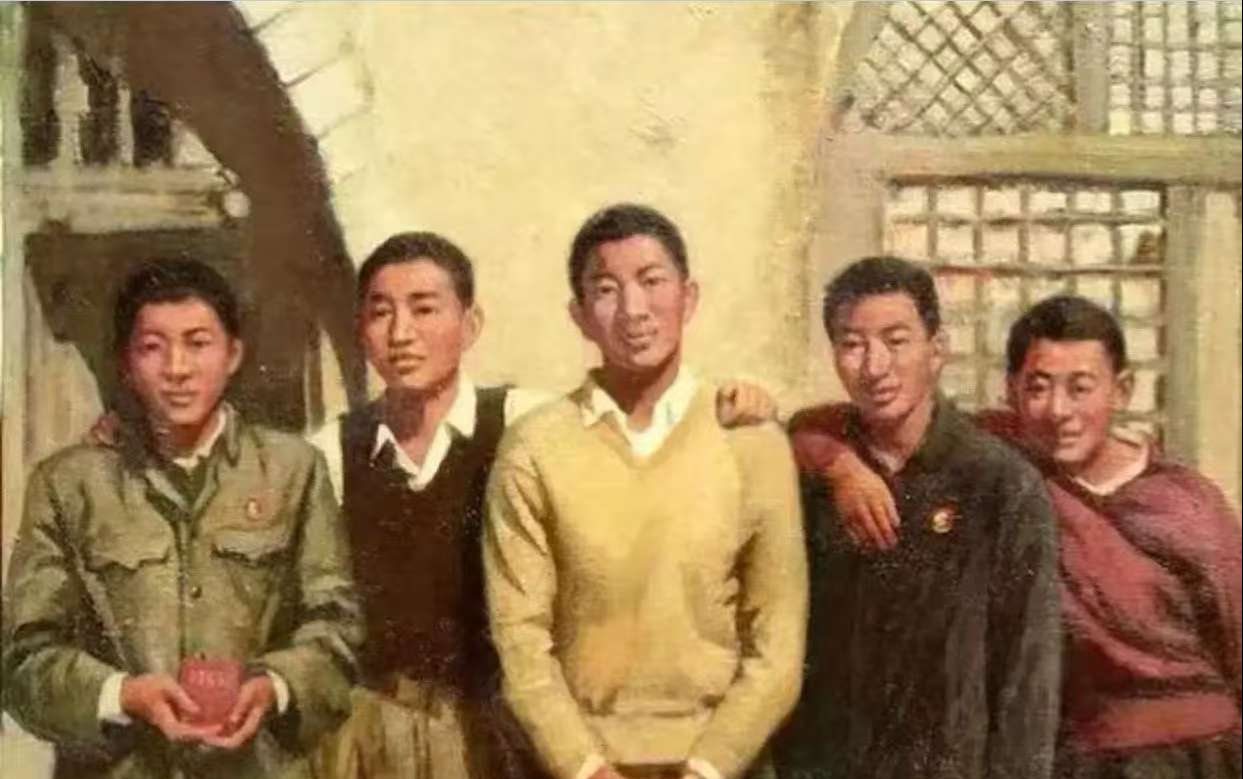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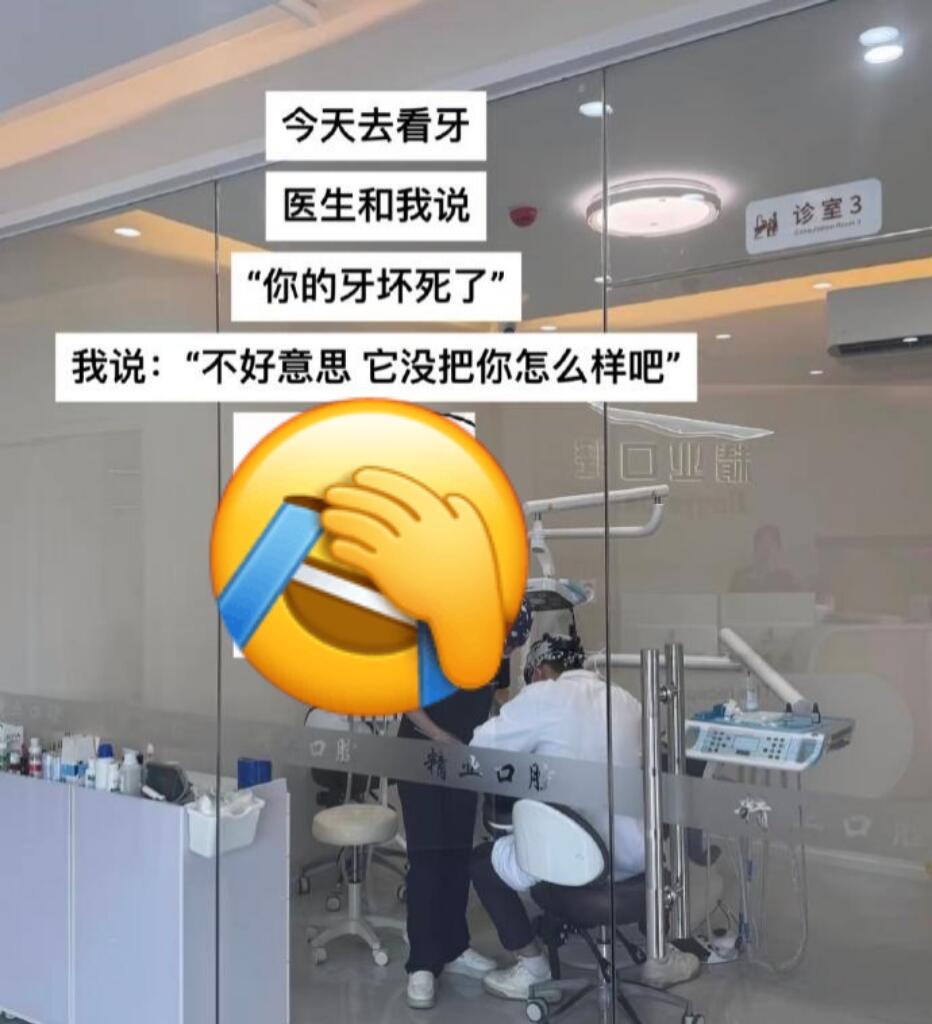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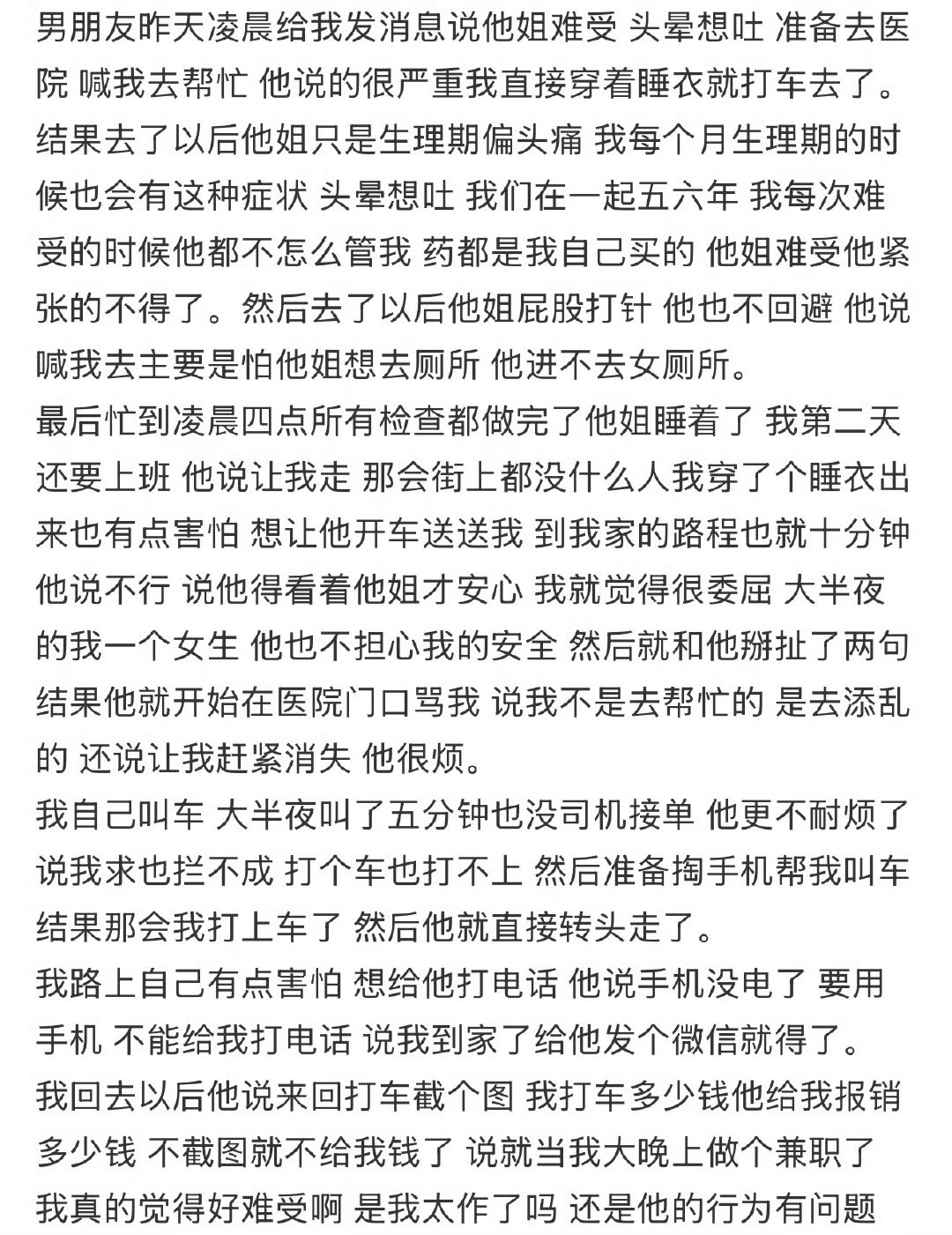

![没想到吧,人家追出国后,又又又回来了[吃瓜][吃瓜]](http://image.uczzd.cn/4217158522888850182.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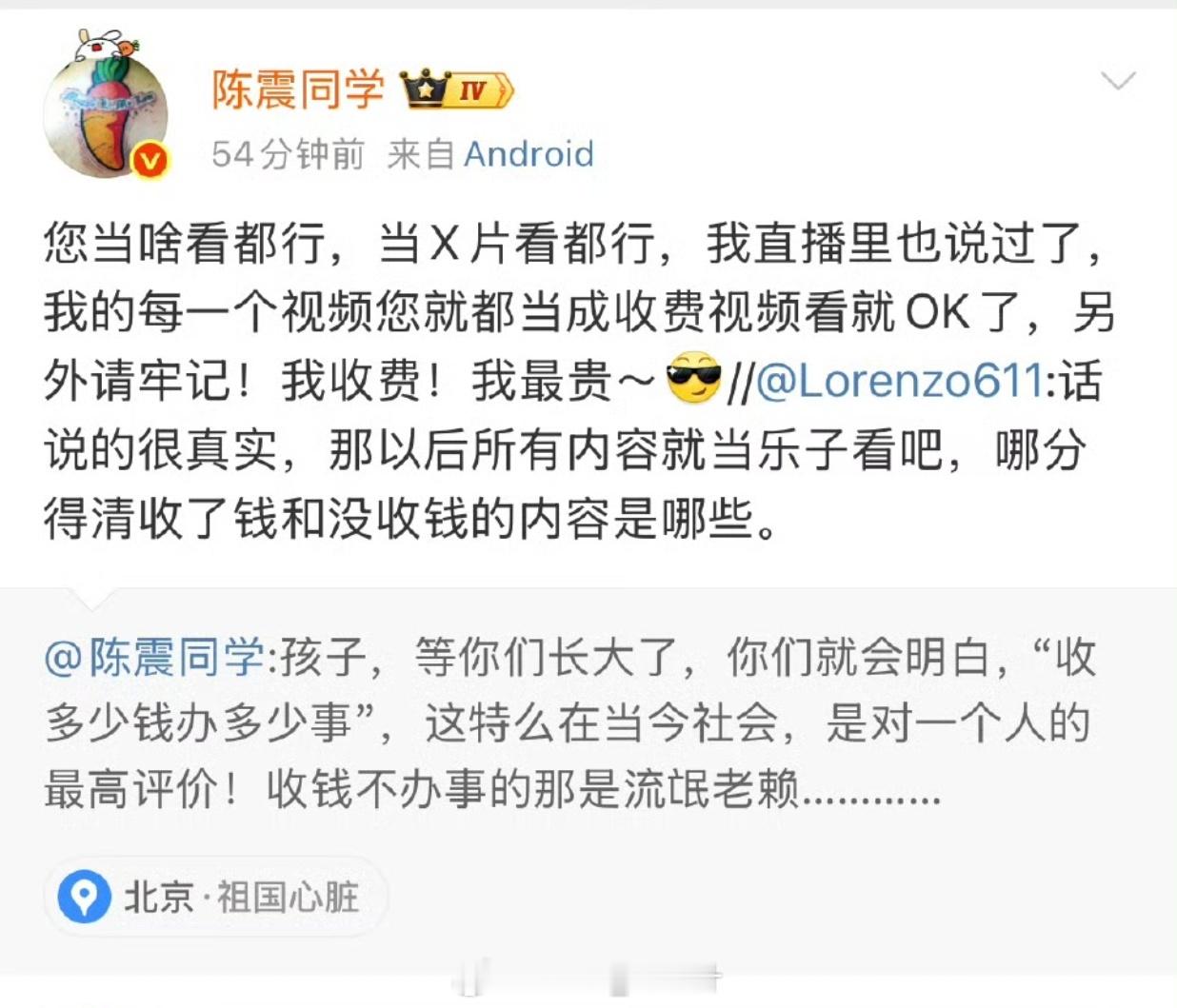
![医生惊讶地问:“果然是因为他!”[吃瓜][吃瓜]😯](http://image.uczzd.cn/5974624987300787431.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