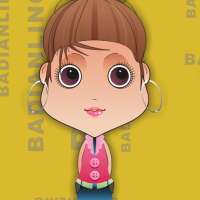1945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意外俘获十余名日军溃兵,团长原欲处决所有战俘,然而战俘名单中的大宫静子颇为特殊,她是岛国战地医院护士,未伤害中国人,并非战斗人员,团长不禁踌躇起来。 1945年初春,缅甸战场上雨季刚过,地面仍是泥泞一片。 中国远征军在连续几日的激烈交战后,终于在拉因公击溃了日军的一个残部。 战斗结束那天,空气里还弥漫着硝烟味,部队搜山时意外俘获了十几名日军溃兵。 原本,这些俘虏的命运早已注定:就地处决,干脆利落。 但就在执行命令之前,团部收到了一份整理好的俘虏名单,末尾那个名字让团长乔明固顿了一下——大宫静子,女性,身份标注为“战地医院护士”。 那是一名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人,身材娇小,脸上苍白无血色,穿着一身破旧的军用护士服,肩膀上还搭着一块沾满泥水的毛巾。 她站在一排垂头丧气的男俘虏中,明显与众不同。 身边的士兵低声议论着她的身份,一时间,枪口下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这并不常见。 战争打到后期,日军已经极少派女性随军,尤其是到了缅甸这种前线阵地,更多是靠男兵死撑到底。 但大宫静子不是自愿来的。 后来通过她的自述才知道,她原本是广岛一所医专的学生,1944年被征召入伍,从上海一路被辗转安排至缅甸。 她没受过军事训练,不会拿枪,主要负责前线医疗站的包扎与急救。 按照远征军当时的处理惯例,所有敌军俘虏无论军衔、职位,一律就地正法。 可面对这样一个女护士,团长乔明固心里起了犹豫。 那一刻,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沉默,但没人出声打破。直到连长刘运达轻轻挪步到他身旁,说了句:“她手上可能没沾过咱们人的血。” 但也正因如此,刘运达的这句劝,让人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情绪不够激烈,而是因为他说得太实在了。 这不是宽容,也不是原谅,而是他凭直觉判断,这姑娘和其他人不一样。 乔明固没回应。 他只是转身走了,连一句“看着办”都没留下。 但在部队里,这就已经是默认的意思。 处决的名单上,那最后一个名字被划去了。 从此,大宫静子没有再穿回那身沾血的制服,也没被当作俘虏处理,而是留在部队,协助后勤做一些基础的医疗工作。 语言不通,她用比划和简单的词汇表达意思,跟着中国护士们学得很快,干活也勤快。 不少战士起初看她都带着警惕,时间一久,也就慢慢放下戒心了。 战斗推进得越来越快,部队很快向内地撤回。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年夏天,她随部队撤到了云南,又辗转到了四川。 仗是打完了,可仇没那么快能消。 在当时的中国,哪怕是一只日本品牌的打火机都容易被砸烂,更别说一个活生生的日本女人。 回国不久,刘运达退伍复员,把她带回了自己在四川白沙的老家。 一路上,她几乎没说话,只把那只已经磨掉漆的木制小箱子牢牢抱在怀里。 箱子里只有几件衣物、一张已经发黄的学生证,还有一张她母亲留下的旧照片。 他们在村里办了婚礼,没有请客,也没有大摆筵席。 村里人一开始全不信,说刘运达疯了,怎么能娶个“鬼子婆娘”?但他没解释,也不争辩,只是照常干活、种地,把家安稳地建起来了。 为了避开流言,大宫静子改了个中文名字,叫“莫元惠”。她不会农活,连菜都分不清品种,常常一边学一边挨骂。 孩子出生后,也没有人帮忙接生,全靠村医和刘运达硬顶着。 有一次冬天,孩子发烧,她冒着雪一路跑了两公里去镇上买药,回来的时候鞋都掉了,脚上结着冰。 村里人才慢慢地不说她坏话了。 日子一天天过,她也逐渐成了村里的“莫家嫂子”,操着一口带川味的普通话,出门买菜、接孩子、劈柴烧饭,跟其他乡妇并没什么区别。 这个名字,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1978年秋天,县里突然来了一批外事接待干部,说是接待一位从日本来的代表团。 日本方面提出,希望寻找一个失联多年的女子,名叫“大宫静子”。工作人员辗转查到白沙镇,说这里有个叫“莫元惠”的中年妇女,可能与此人有关。 消息传到村里,像一石激起千层浪。 县里干部上门那天,刘运达神情异常紧张。他不怕被问责,也不怕被调查,他怕的是,三十多年的生活会在这一刻被打断。 可大宫静子只是平静地听着,直到听到“大宫义雄”这几个字,眼圈才一下红了。 她点了点头,说:“那是我父亲。” 她的真实身份就此揭开。原来,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一直没放弃寻找她。 通过中日关系改善的渠道,他多次恳请中方帮忙寻人。 这次访问,是他以“日中友协”身份促成的。 第二年,他们一家去了日本。对刘运达来说,那是一次完全陌生的旅程。 他努力学了几年日语,结果只会点头说“可以”,遇到急事还是靠比划。 岳父去世后,他们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说是百亿日元,合人民币也是天文数字。 他们的二儿子留在了日本,接手了事业。 可刘运达还是不习惯那边的生活,十年后,他跟妻子一起收拾好行李,决定回国。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