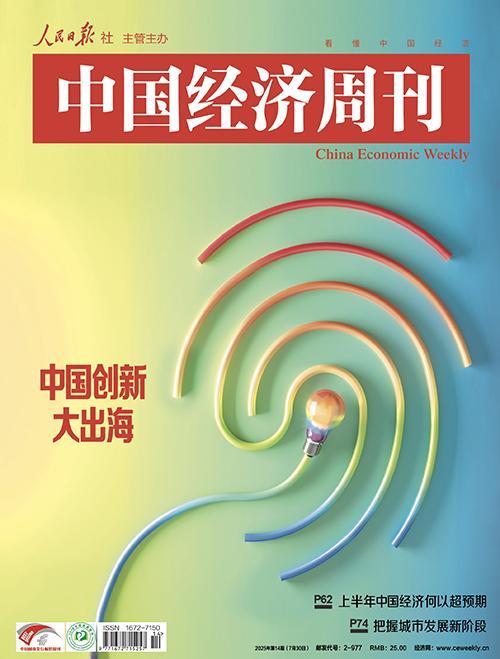文|赵永涛
编者按:7月22日,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今年以来,核聚变概念在资本市场逐渐升温,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宣布布局核聚变能源产业链。更有院士公开表示,预计5年内点亮第一盏“核聚变灯”。究竟什么是“可控核聚变”?为什么它被称为“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技术何时能够实现商业化?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在地球上重现太阳的能量产生方式,那会是什么场景?这就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关的“可控核聚变”。简单来说,就是让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极端高温高压环境下发生核聚变反应,同时确保整个过程安全可控。
之所以被称为“人造太阳”,是因为这个技术原理与太阳发光发热的本质如出一辙。在太阳核心,1500万摄氏度的高温让氢原子不断碰撞聚变,释放出巨大能量。
核聚变释放的能量远高于化学反应。单次核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约为化学反应的10⁶至10⁷倍(百万至千万倍)。因此,核聚变的功率远大于化学燃烧,但其实现难度也更高。
人类如果能掌握这项技术,就相当于在地球上建造了一个微型太阳,为人类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能源。

本刊记者谢玮I摄
核聚变与核裂变:能源技术的代际差异
核聚变与核裂变是两种不同的核反应形式。目前核电站主要采用核裂变技术,其燃料通常选用自然界中最重的元素——铀。在天然铀矿中,仅有约0.7%的铀-235可用于核裂变反应,因此需要通过浓缩工艺提高其浓度。铀-235在受到低能中子轰击时会发生裂变,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较轻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大量能量。
核裂变反应的控制主要通过中子吸收和燃料棒插入深度的调节来实现。这种调控方式使得核裂变技术能够稳定应用于核电站、核动力航母及核潜艇等能源系统。
这种方式虽然已经相对成熟,但也存在明显局限:需要开采有限的铀矿资源,会产生长半衰期放射性废物,还存在核泄漏的安全隐患。
核聚变与核裂变在反应机制和实现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核聚变首先需要使用数亿度的高温来引发燃料反应,并依靠聚变产生的α粒子维持该温度以实现持续燃烧。由于聚变反应所需温度极高(远超常规材料的承受极限),目前主要采用磁约束方式实现可控聚变。其核心在于通过磁场控制等离子体空间分布,以实现反应的稳定维持。
目前,全球可控核聚变研究呈现多元化技术路线并行的格局。从核心要素来看,主要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从燃料维度来看,可分为氘氚(D-T)聚变和氢硼(p-B11)聚变。
从约束方式维度来看,一种是磁约束路线,即利用强大的超导磁场将高温等离子体约束在环形装置中,包括中国的“东方超环”EAST装置、BEST装置、中国环流三号(HL-3)、新奥玄龙-50U等,美国的SPARC项目,欧洲的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都采用这种方式;另一种是惯性约束路线,通过高能激光瞬间轰击燃料靶丸引发聚变,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就是典型代表。
与核裂变技术相比,可控核聚变技术展现出革命性优势:它的燃料氘可以直接从海水中提取,一升海水中的氘通过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燃烧300升汽油;产生的废料半衰期仅几十年,远低于核裂变的数万年;更重要的是,聚变反应一旦出现异常就会自动停止,不存在爆炸风险。
从实验突破到商业化展望
近年来,可控核聚变研究领域取得显著突破。2022年,美国NIF首次实现可控核聚变反应的净能量增益。2024年,该实验再创纪录,实现5.2兆焦耳能量输出(Q值≈2.5)。
今年1月,中国的EAST装置创下了新的全球纪录,首次实现了1亿摄氏度1066秒的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与过去“还需50年”或“30年”的保守预期相比,当前实验证据和技术进展已展现出更乐观的前景。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实现可控核聚变的时间窗口可能缩短。若结合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这一进程还可能进一步加快。
目前,多数实验装置为避免核污染影响设备性能,尚未使用聚变燃料运行。但未来5年内,我国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计划开展氘氚聚变实验,并实现聚变能发电演示。这将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现有参数预估,一旦使用氘氚燃料,聚变功率将足以点亮第一盏“核聚变灯”。
不过,要实现商业化应用,科学家们还需要攻克更多难关,我们还需要保持耐心。乐观估计,我们可能在2030年前看到示范堆建成,2040—2050年间实现首座商用核聚变电站并网,但要大规模推广可能还要等到2060年以后。
可控核聚变承载着人类对清洁能源的终极梦想。虽然完全商业化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缩短这个距离。中国的科研团队正在这一领域奋勇争先,BEST装置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我们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既要对这项技术保持关注,也要理性看待市场的声音。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见证“人造太阳”走入人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