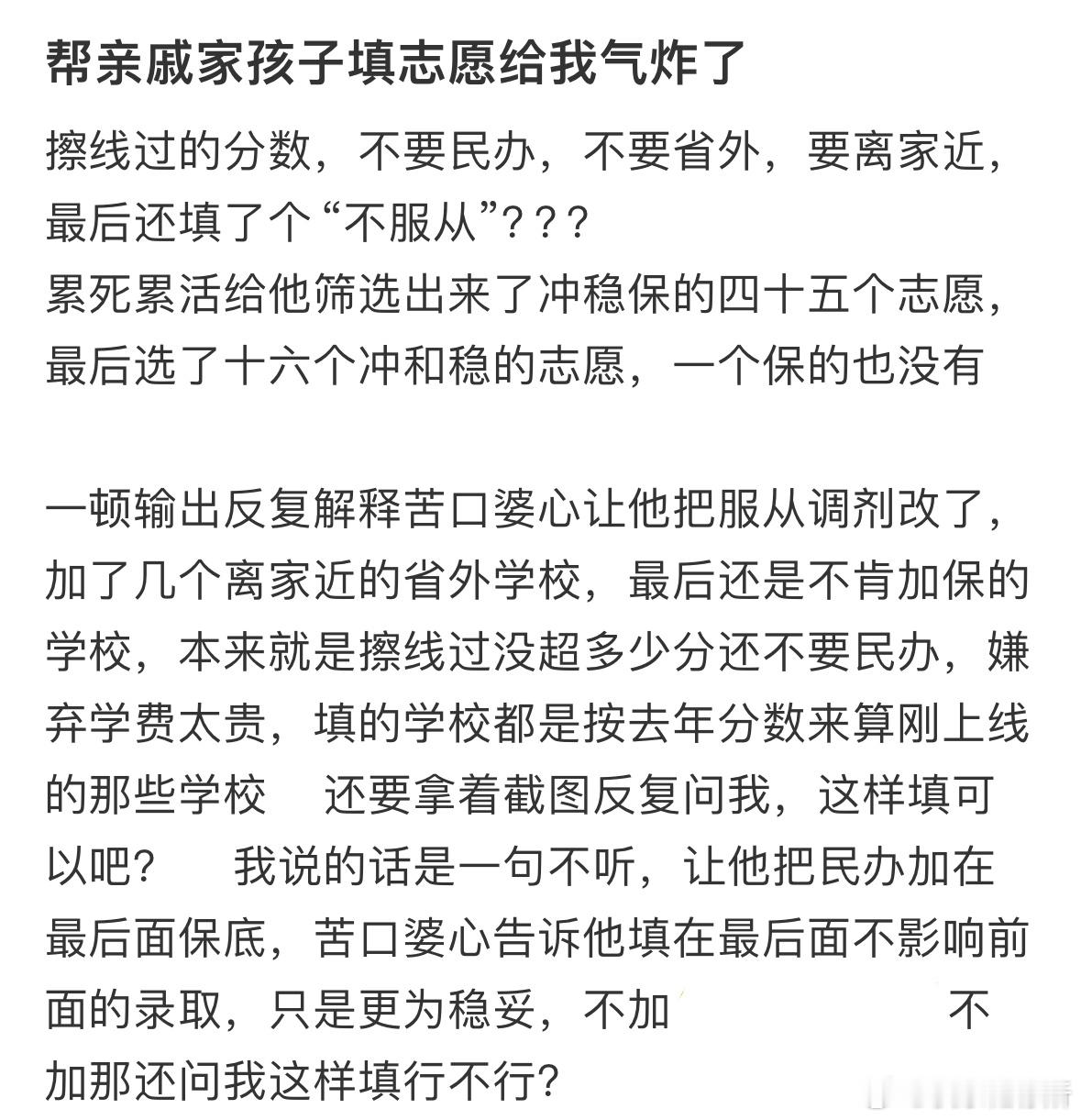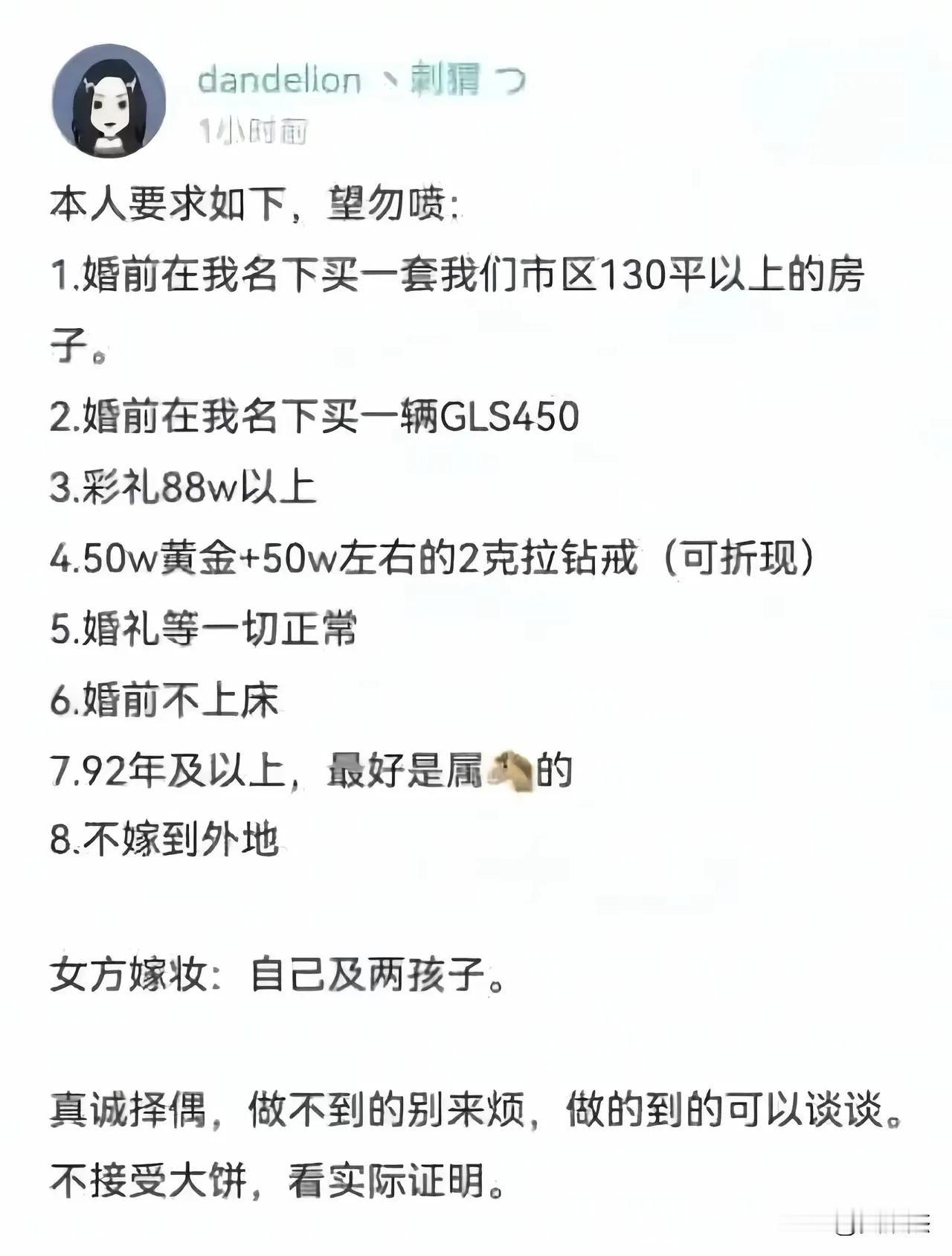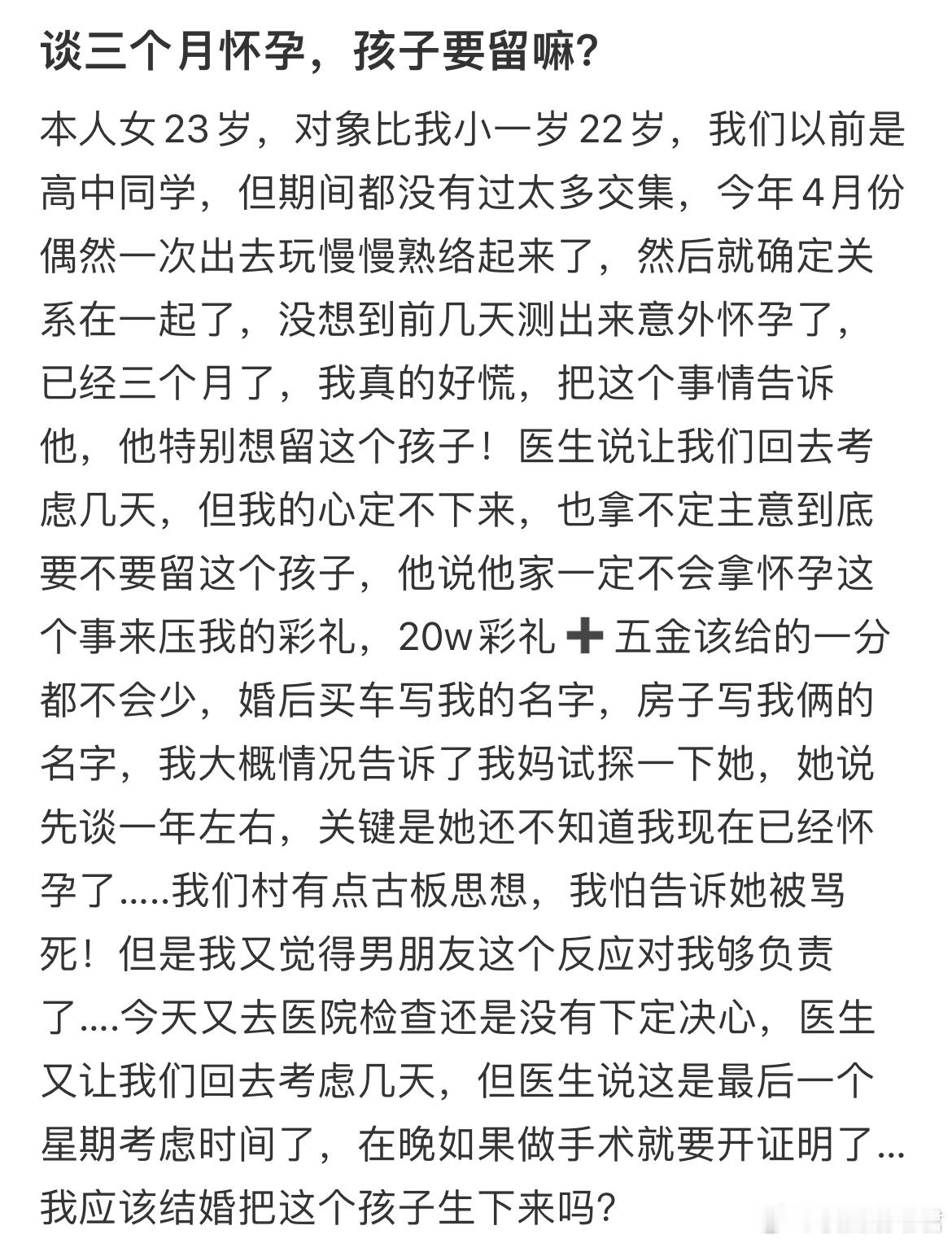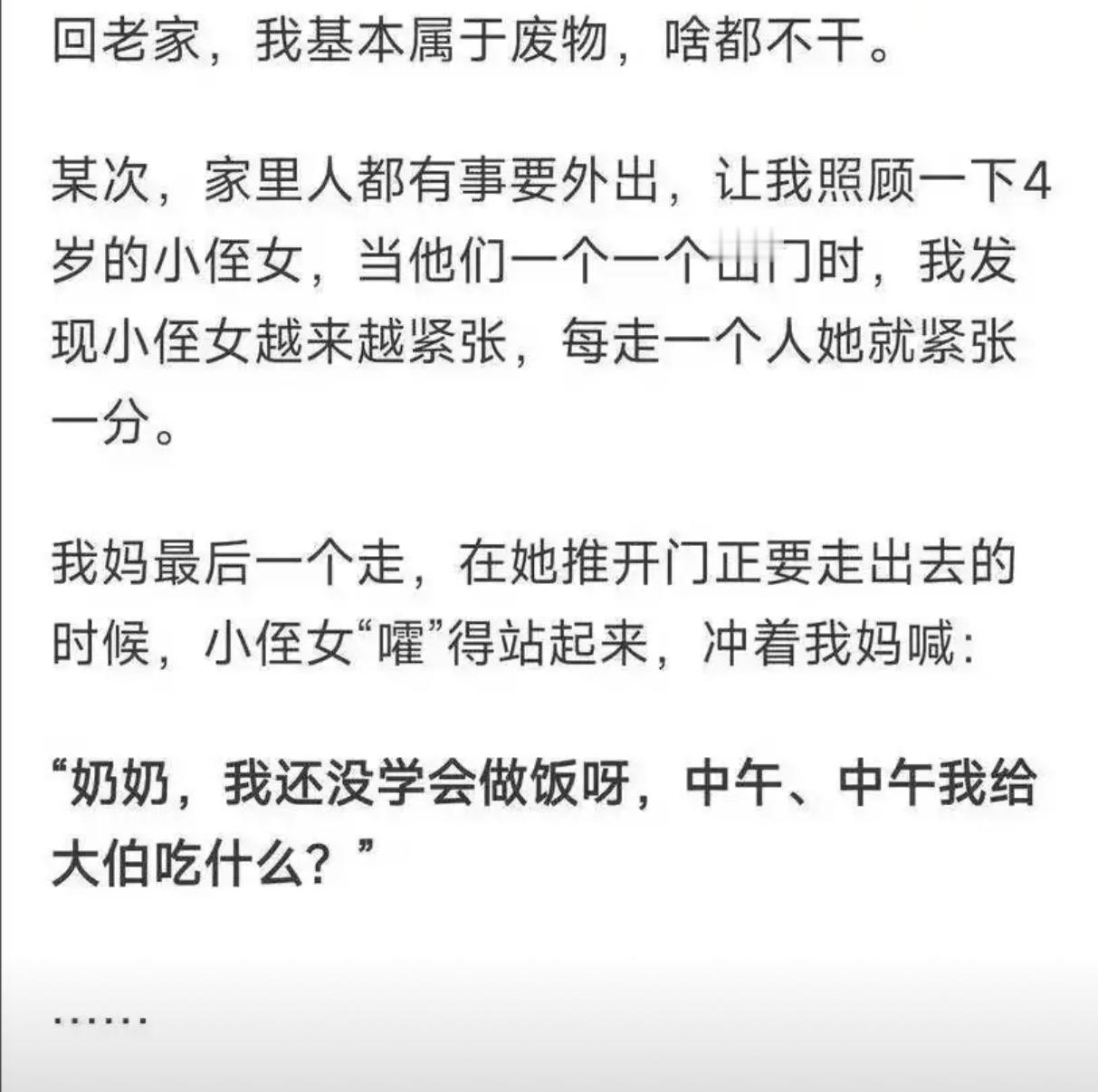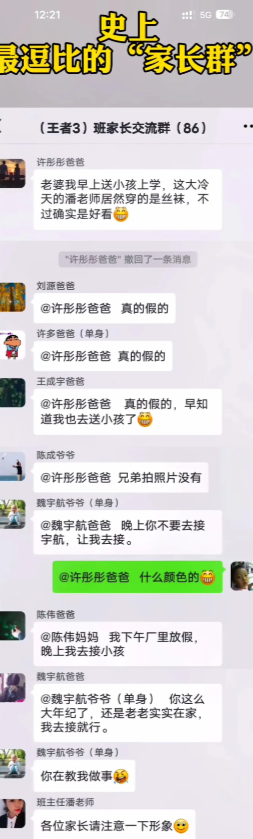这个是我家以前的阿姨,她17岁来我家,陪伴我的孩子们长大。我最小的孩子上小学后,她也回老家结婚了,现在是2个孩子的妈妈。 蓝布包袱里的人生 青岛流亭机场的候机厅里,王娟把登机牌攥得发皱。我指着电子屏上的航班信息给她看,她睫毛忽闪着:“张姐,咱真要坐那铁疙瘩飞日本?” 十七年前她刚到我家时,也是这副怯生生的模样。1998年的北京,秋老虎正凶,她拎着个蓝布包袱站在单元门口,辫梢沾着的黄土被汗浸成小泥点。“俺叫王娟,陕西渭南来的。”她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俺啥活都能干,不挑食。” 厨房里的英语角 头三个月,王娟总躲着我家那台钢琴。有天小女儿练《致爱丽丝》,手指总卡壳,她突然从厨房探出头:“是不是该按那个黑键?” 我们都愣了。她脸一下子红透,撩起围裙擦手:“俺听小姐练了二十遍了。” 后来她成了孩子们的“编外同学”。小女儿写作业,她蹲在旁边削铅笔,耳朵却竖着听英语磁带;大儿子练琴,她就搬个小马扎坐在琴凳旁,手里纳鞋底,拍子打得比谁都准。有次学校开家长会,老师笑着说:“你家阿姨发音比有些家长还标准。” 她其实没上过几天学。有回我翻出她枕头下的笔记本,歪歪扭扭记着“banana——香蕉”,每个单词旁边都画着小图案。“怕忘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等俺回家,也能教俺侄子。” 幼儿园的“孩子王” 2005年,小女儿上了小学,王娟在小区幼儿园找了份保育员的活。园长后来跟我说,开园三年,从没见过哪个老师能让三十个孩子同时安静吃饭。“王娟有办法,”园长啧啧称奇,“她给孩子们编儿歌,‘小手洗干净,饭菜香喷喷’,孩子们跟着唱,吃得比谁都香。” 我去幼儿园接她下班,总看见她被一群孩子围着。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献宝似的给她看画,流鼻涕的小男孩拽着她的衣角要听故事。她蹲在地上,裙摆沾着颜料,笑得眼睛眯成缝。 “张姐,俺想在北京扎根。”有天晚上她跟我说,手里捏着刚发的工资条,“俺报了夜校,想考个保育员证。” 可第二年春天,她突然红着眼圈来辞行:“俺妈给俺说了门亲事,男方在老家开修车铺,俺……” “你不是想考证书吗?”我急了。 她把夜校课本递给我:“留着给小姐当草稿纸吧。俺妈说,女人家早晚要嫁人,安稳最重要。” 大阪街头的叹息 飞机在大阪落地时,王娟盯着舷窗外的灯火,突然说:“俺这辈子,就出过三次远门。第一次来北京,第二次嫁去邻村,第三次就是跟着您。” 在道顿堀吃章鱼烧时,她把芥末酱蹭到鼻尖上,像个孩子似的咋舌。“俺家闺女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稀罕物。”她掏出手机拍照,镜头却总对不准焦。 她手机屏保是两个孩子的合照。女儿扎着和她当年一样的辫子,儿子胖嘟嘟的,正啃她的手指头。“闺女上四年级了,数学考了全班第三,”她翻照片给我看,“就是总问俺,北京的天安门是不是真的像课本里那么大。” 逛街时路过一家母婴店,她在打折的纸尿裤货架前站了很久。“这边比老家便宜三块钱,”她小声算,“要是能多带几包……” 我没说话,悄悄让导购多拿了两包塞进她的行李箱。 黄土里的日子 从济南飞回西安那天,王娟的老公骑着电动三轮车来接机。车斗里堆着棉被,她三岁的儿子裹在被里,看见她就伸着胳膊要抱。“路上堵车,来晚了。”男人挠着头,黝黑的脸上全是歉意。 三轮车穿过西安的小巷,王娟指着路边的修车铺:“这就是俺们家的店。”铁皮棚子下,几辆电动车歪歪扭扭地停着,墙角堆着生锈的零件。 “生意不好做,”她老公叹口气,“油车修得少了,电车又没啥大毛病。”王娟赶紧打圆场:“够吃够喝就行,俺们攒钱给娃盖新房呢。” 临走时,她往我包里塞了袋核桃:“俺妈种的,补脑。”核桃壳上还沾着泥土,像她刚来时那个蓝布包袱上的痕迹。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渐渐缩小的城市,突然想起王娟在大阪说的话:“张姐,俺不觉得亏。俺闺女会背唐诗,俺儿子会叫妈,这日子,比啥都实在。” 或许我一直替她可惜,不过是站在自己的人生里,替她做了选择。就像黄土高原上的酸枣树,长不成北京的梧桐树,可它扎根的地方,总有阳光照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