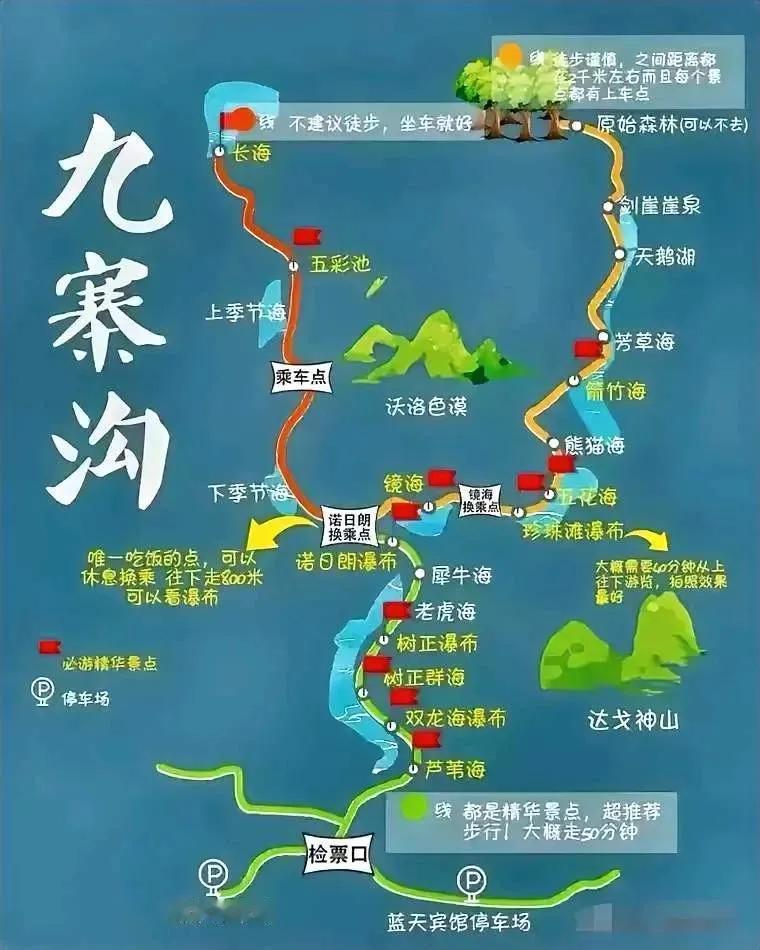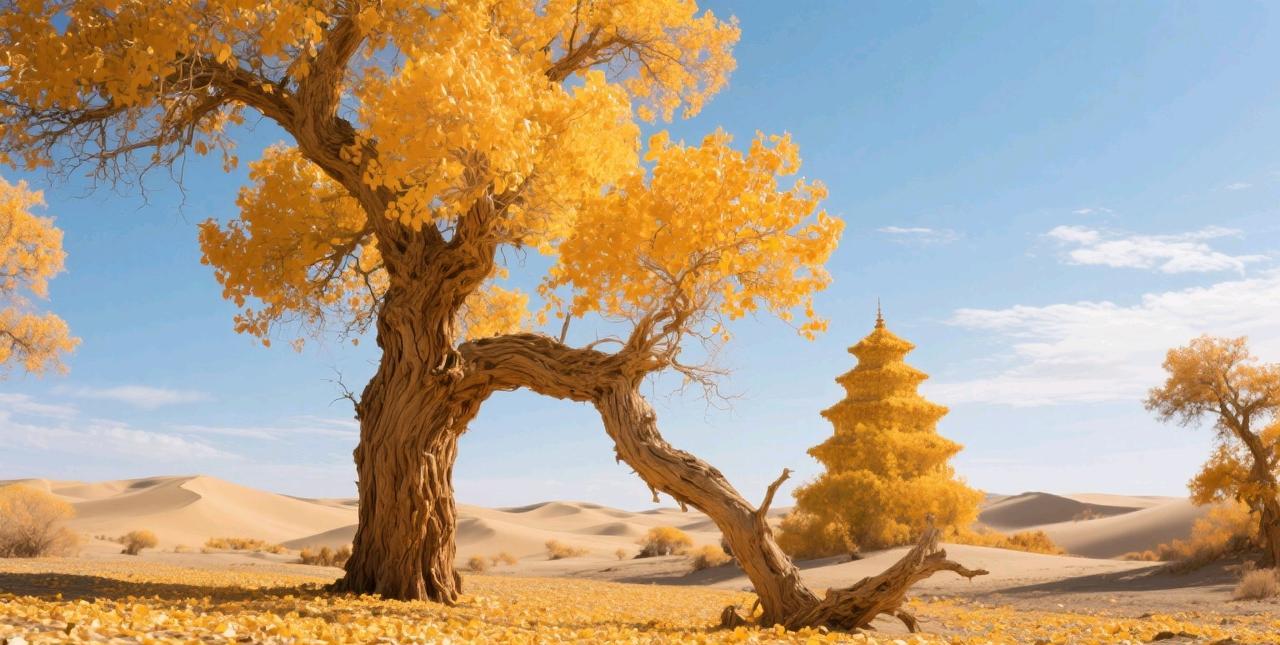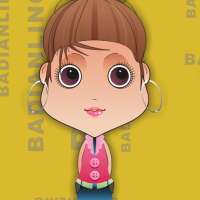未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三峡之巅的全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要说三峡,那可是长江的一段灵魂。 这灵魂不是因为水多,也不是因为山高,而是因为江水和山体之间那种绞在一起的劲儿,就像一根绳子同时拽着天地两端。可偏偏在这片连水都被挤出花样的地方,还有那么一处极高之地,像老天打翻砚台时不小心溅出的最后一滴墨,落得刚刚好——这,就是三峡之巅。 如今很多人提起它,第一反应是风景照里那个站得极高、能把白帝城、夔门、瞿塘峡一并塞进镜头的观景台。可要往前倒个几十年、上百年,别说照相机,那地方连名字都没定型。三峡有名,是因为水走得狠,江刻得深,船行得险,但谁又会真去在意那高出水面千米的山顶?在没有直升电梯、没有观光公路的年代,那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 地理上看,这一带属于重庆奉节,地处瞿塘峡段最东边,也是长江从四川盆地冲出第一道门户的地方。奉节这名字听起来温和,可三峡之巅的脾气一点不软,海拔1388米,在崇山之间像根脊梁骨一样翘了起来。不光高,站在上面一看,整条长江像是一条失去了方向感的龙,头也不回地朝前扑。若碰上大雾天,江面雾卷得像山火,连白帝城的轮廓都虚得像梦。 古人爬得上去吗?这问题常有人问。想登那样的高地,说难是难,说可能也确实有可能。要说那时没有修观景平台、没有登山步道,可人有腿,诗人更有心。杜甫晚年颠沛流离,从成都出来,一路顺江,到了江州,再漂到夔州,这一漂,漂到了自己一生诗魂的落脚点。他在这儿住了三年,岁月并不宽厚,他那时候病恹恹、身无长物,靠着夔州都督的接济才熬日子。可就是在这夔州,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占了他创作的三分之一。 他写《登高》,不是为景区打广告,那是真站在高处,有风扑面,有猿啼入耳,有江流在脚下滚得不肯停。他写“风急天高猿啸哀”,写“无边落木萧萧下”,那气象、那场面,不是从江边回头望一眼就能写出来的。他得看得够高,心境得够辽阔,那“滚滚来”的长江,是他看尽颠沛人事之后仍不肯妥协的笔锋。而他写《夔州歌十绝句》时提到“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那就更像是站在今天这三峡之巅往下看的模样。白盐山、赤甲山,那是奉节城的左右门神,尖得能戳破云。站在山巅,能把整个古城的屋瓦尽收眼底,连哪户人家点灯吃饭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杜甫是不是登过那巅?没人能百分百说清楚。但看他的诗,就知道他离那地方不远。真要上去,也不是没可能。更何况他在那住了三年,山高林密虽说险,但若真想攀登,也不至于全无办法。人的脚走得慢,心思却走得远。不登之巅,也可思之巅。他的诗把那地方写活了,山还没动,字已在前头等着。 奉节这个地方,被称作“千古诗城”,可不是文旅口号随口一喊。这座城跟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实在太紧了。李白写“早发白帝彩云间”,他那一早,可不只是清晨,是清晨加速度,是江流与阳光打了个配合的瞬间;刘禹锡写“竹枝词”,那山桃红花、那春水拍山,他写得那样轻灵,其实也是在把山水唱成民谣;康熙皇帝也在这儿题诗,自封“天下第一景诗”,虽带帝王口吻,倒也承得起那地的气象。 这些诗句都不是空泛描写,它们有景可寻,有地可证,而这些景与地,多数在那高处。三峡之巅不是实指某一块地砖,而是指一段山脊线的极致,一段文化感的叠加,一种立体的凝望。它是诗人在时间里反复描写的那道峰线,是他们心里向往却难以抵达的至境。 今天的人想登那巅,可比过去轻松太多。山修了路,道铺了平,还建了观景台,名叫“迎龙台”。这名字也没取巧——那山脊像龙身,台顶像龙头,整座巅地就像是长江文化的脊骨。站上台子,往东望,是云梦泽旧地;往西看,是巴蜀余脉;下视白帝城、夔门、瞿塘峡一线如雕刻;回头再看,奉节老城在山脚挤得密密麻麻,像旧报纸上铺开的墨迹,静得刚好,乱得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