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器物志》是作家、江南文化学者徐风的最新长篇系列散文力作。全书分别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写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菁要,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从龙骨水车到犁耙锄钎,从碗碟盘盏到鼎龕鬲匜,作者在温习稻饭羹鱼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想象着器物背后的人与中国文化精神,讲述了江南太湖西岸一座代表性的古镇百余年来的器物生活和文化道场,书写南方温润又激烈的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
徐风以一座江南古镇为场域,通过对诸多器物的聚焦,开创性地建构了“器物志文学”的概念范式。这种范式超越了传统的风物志写作,以器物为棱镜,深度折射江南地域的民生百态、社会结构、历史生活与精神脉络。
《江南器物志》最动人的篇章,是揭示器物如何塑造着江南人的精神世界。从“宁折不屈”的竹器气节,到“阴阳平衡”的医器美学;从“湮而不没”的包浆哲学,到“天落地捡”的扫地之道,器物不仅是生活的工具,更是修身的媒介——徐风在他的“器物志文学”中,展示了物质与精神的互文,以承载对民间精神的重掘与器物精神本质的叩问,为思考中华文明与地域文化的承续与再生,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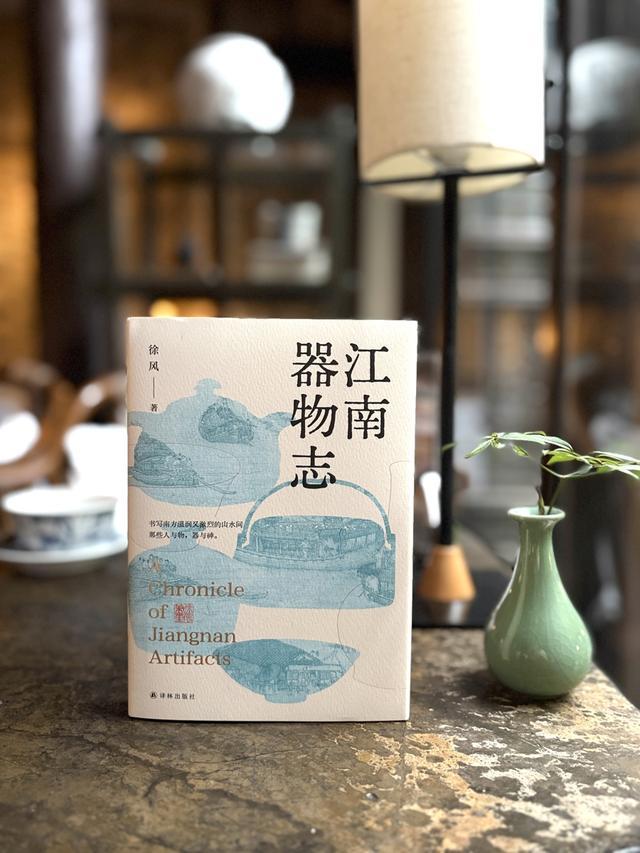
《江南器物志》,徐风/著,译林出版社2025年7月版
作品选读
跋篇|器物有灵光
我世居于江南一隅,一生无缘仗剑远行。平生偶尔也与命运作些有限的抗争,但从来不与自己的遗传基因做无谓的抵抗。
生在壶乡,喜欢吃茶,器物之类却并不收藏。爱写作,此生只缘文学。与紫砂有关的书我写了不少,写到后来,紫砂壶在我笔下,仿佛只是一个道具了,我关切的,是茶壶脚下的文化土壤,是茶壶背后的世道人心。如果将紫砂壶比作一株植物,那么,树种再好,也得水土优良。江南文化的沃土里,这样的植物太多——器物是人创造的,只消落地问世,它与人注定就是分分离离的关系。自从人们把稀罕的器物归类于财富,便有了尔虞我诈的争夺厮杀。更多的人,把它看成是念想,是见证天地的信物,这个世界便因此有了暖意。也有人在乎手艺人在它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器物沉睡的灵性。
在庸常的日子里游弋,我发现器物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假若有心观照,隐约的包浆里,有对人世恬淡的回馈,也有对人们过日子诚意的褒奖。您有过一器在手,胆气频生的片刻吗?您有过见物思人,心眺八荒的时光吗?
于是就有了一摞关于江南器物的书写。器物托志,古今皆然;地理绵密,凉热同心。我心仪此间古代读书人的朗朗风骨,感知月下针织与凿壁偷光之间的异曲同工,在温习稻饭羹渔里的古老用具之余,我更在意“器隐镇”上与器物相关的生老病死。史志记载以外的普通百姓,可以借助器物的还原,以文字的方式复活吗?我喜欢倾听他们的一声喟叹,在乎他们留在古物上的一枚指纹。就此而言,某间茶楼上一壶托付的生死契阔,也可以波澜不惊地荡气回肠。我可以用纸上的文字,为那位颠沛流离的苦行人煮一壶御寒的酽茶吗?纵然,沧海桑田,于今再也找不到风雪之夜的金沙寺庙了,但我想用温煦的文字,抚慰一下无家可归的夜行者。想来,托付一颗冥冥之中的定情珠子,讲述有着难言之隐的家族往事,或许春水东流;而追忆一生给众人扫街70年却不得哀荣的罗氏长辈,为他画一张面影模糊的肖像,也可替代扼腕难平的书生意气,供上一炷文字的香火。
一个小小的野心,起始于用文字搭建、还原一座烟火漫卷的江南古镇,以呈现它气象万千的日常肌理。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庭院、舟车、服饰……都是中国文化语境里永不破败的肉身;俗世生活中的菜单、食谱、药方、茶道、风水、方术、古玩、字画,亦是中国古人精魂里不可磨灭的诸般星宿,乃至茶馆、酒楼、当铺、钱庄、塾馆、文庙、诊所、会馆、别院……都是人世间必不可少的驿站港湾。各种大小自在,俱是人间值得。这些景致都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交替呈现。由此派生出诸多官吏、书生、师爷、农人、商贾、道士、郎中、艺人、民妇、工匠、讼师、洁夫……他们碌碌一生、各谋其所、各求其好。或纠缠于情义,或困扰于器物,在“器隐镇”这个道场上,以各自的阅历,述说着他们的过往人生。
谢谢《收获》杂志,为我开设“江南器物”专栏。然后,谢谢译林出版社一直以来的包容与厚爱,及时地出版《江南器物志》一书。

徐风
有读者问,器隐镇究竟在哪里?
答曰:就在我们的脚下。
请允许我这样来回答——按图索骥去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器隐镇”,或许会让您的豪兴有所减弱。但我想告诉您的是,它肯定安静地待在江南——太湖西岸的一处烟火重地。苍生受哺,天地精华,大默如雷而地久天长。等待您用审美眼光去观照它、走进它——文学的写实绝不是依葫芦画瓢。地方志、历史掌故、宗族家谱、田野调查、江湖传说、坊间逸闻、人生经验、个性思辨……汇聚到文学的旗下,成为我写作的血肉根基。追根溯源,或许更有自己对这片土地和成长记忆的忠诚。我想用不那么中规中矩的“散文”文本,来完成我对“器隐镇”的百年书写。私下里一直认为,偏安一隅亦颇有益。构建一条神性通道,去汲取一隅之丰沛,与广袤的世界进行无处不在的对话。避开浮华与喧嚣,把写出自己所生活的地域的灵魂,作为一生的追求。如此,甚好。
此刻,我正站在“器隐镇”的长生桥畔。万籁俱寂,云淡风轻。我想记叙头顶的明月,我想探究脚下的厚土;我想追述祖辈们铭刻在器物上的恩德,我想解析时代差异留在器物上的胎记;我诅咒把器物沦为私欲的蜕变,我追踪器物成就生命个体的向死而生,我仰慕器物背后流淌的母乳般的中华文明,我痛惜民间精神的日渐衰落,让江南乡镇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消弭殆尽,我在意为了一器之物在这尘世深处悲苦坚守的困顿生灵,我在乎小小器物里流溢出的满满慈悲。我向往那隐藏于江南广袤民间的风土情怀,也流连于那些古老传器中未被忘却的侠肝义胆,我珍藏起旧器物中先贤们被俗世湮没的宽厚仁爱,努力化作支撑我文字书写的拐杖和精神参照。
谢谢你们,亲爱的读者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