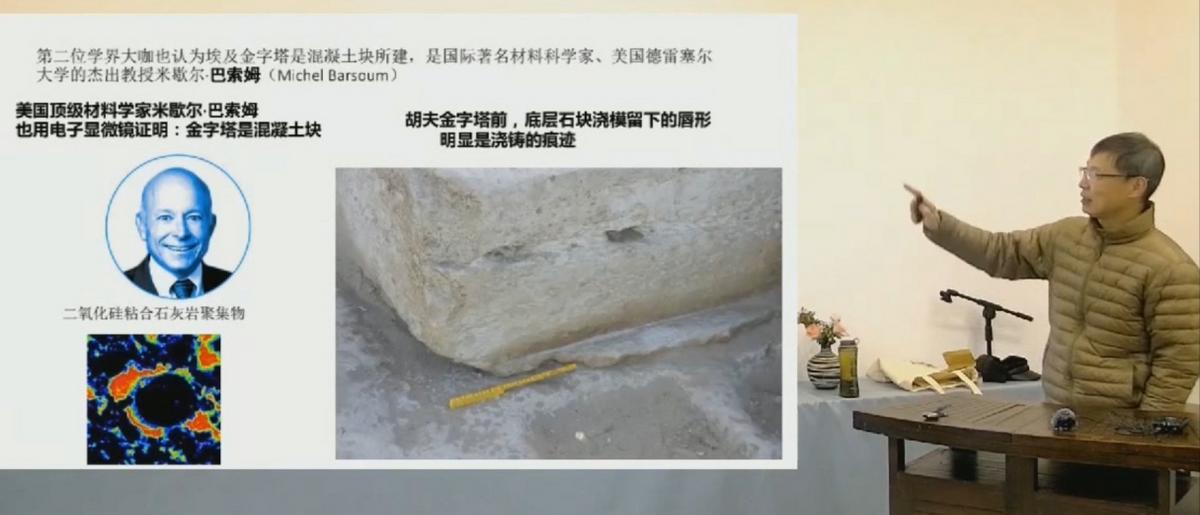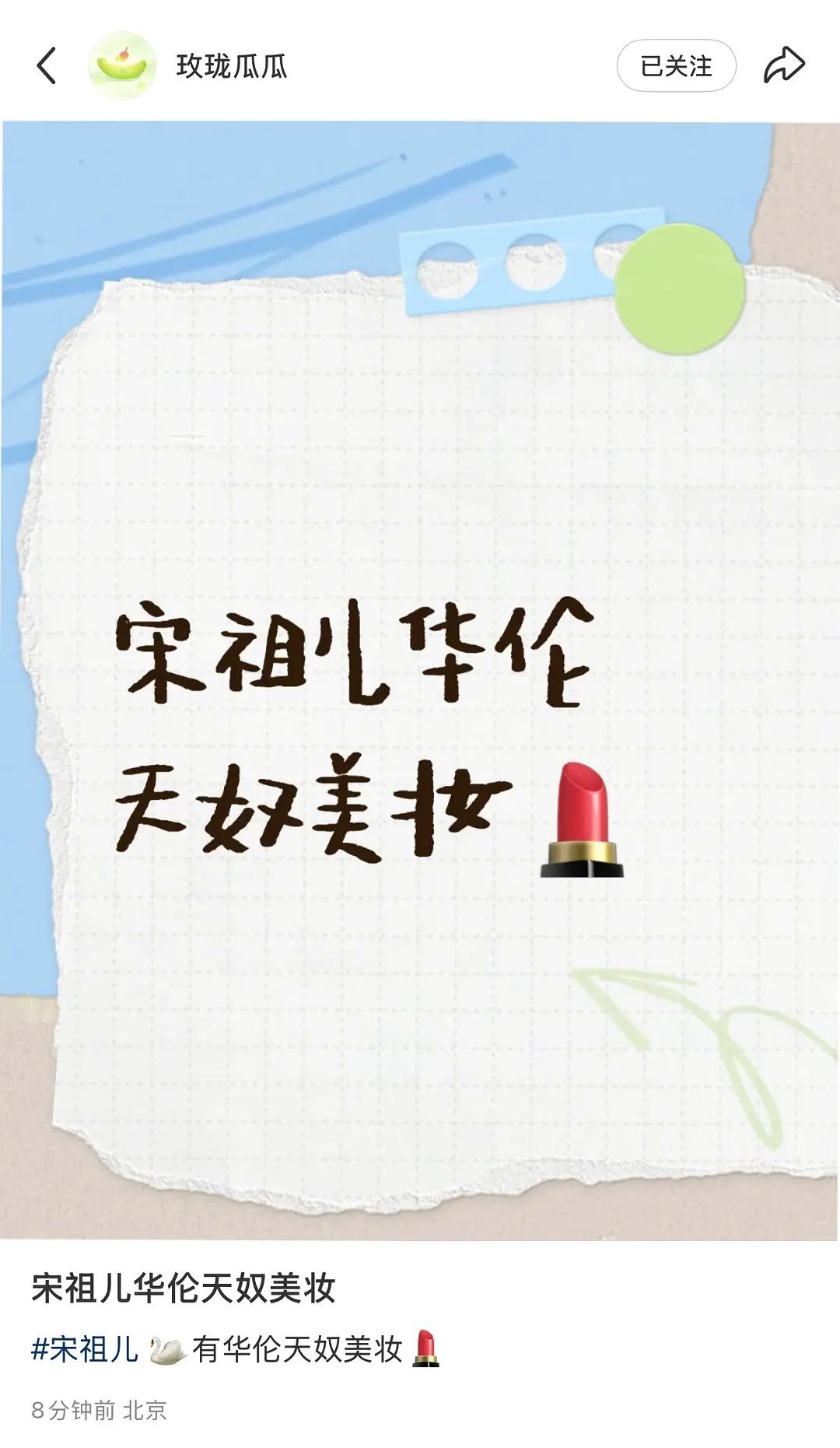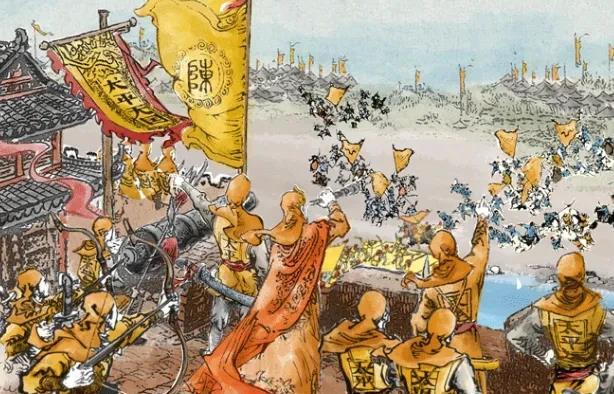1956年,毛主席在怀仁堂看戏,突然停下来问周恩来一句:刘嫂子在哪?瞬间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谁都不知道“刘嫂子”!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35年,同桂荣第一次踏进陕北瓦窑堡时,丈夫刘志丹正在被隔离审查,没有预兆,没有解释,几纸命令将他从战斗前线带走,暂时停职,交由内部机构处理。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被关押意味着危险,也可能意味着终结,同桂荣得知消息时正在甘泉县照顾战地伤员,接到传信后,立刻带着女儿连夜赶往瓦窑堡。 那天深夜,她不顾一切闯入驻地,试图打听丈夫的情况,所有人闭口不言,只有一个年轻士兵偷偷告诉她,刘志丹已被单独看管,原因不详。 第二天一早,同桂荣设法向中央传递了请愿材料,数小时后,毛主席亲自召见了她,毛主席接见时并未多言,详细阅读了她手写的陈述,随后让工作人员调取了刘志丹在陕北期间的全部军务记录。 审查持续了三日,毛主席每天抽时间逐页翻阅汇报材料、战斗命令、后勤记录和干部提拔方案,最终找出当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人为因素。 通过多方交叉调查,毛主席确认刘志丹并无反党嫌疑,而是因地方干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个人恩怨被误告。 毛主席立即指示纠正处理决定,将刘志丹无罪释放,并恢复职务,通知下达的当晚,同桂荣在食堂排队时被工作人员叫走,直接带往刘志丹所在的营地。 两人重逢的场面无人旁观,也无人记录,只是从此以后,刘志丹重新回到指挥岗位,担任红军西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刘志丹在复职后继续主导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整编工作,整顿武装队伍,调配粮草,协助中央推进统一领导,他不计个人得失,将部分起义部队主动合编进红军主力。 他所领导的队伍在陇东战役中完成战略目标,成功吸引敌军注意力,为中央红军突破封锁赢得时间。 1936年3月,红军在东征山西时遭遇强敌围攻,刘志丹在部署战斗时被流弹击中要害,当场牺牲,军委即刻下达哀悼通告。 噩耗传到瓦窑堡的当天晚上,中央考虑到同桂荣病体初愈,决定暂时封锁消息,直到十日后召开追悼会前夕,中央才由贺子珍通知她。 同桂荣听到消息后没有哭闹,只是坚持前往南门外亲自送别,当时她身体虚弱,只能由担架抬去现场,到达墓地后,她坚持起身走向棺木默默站立五分钟,随后晕倒在地。 此后数日,她被安置在贺子珍住处,由医护人员每日照料,女儿也一并接来,安排在隔壁房间,身体恢复过程中,同桂荣没有过多言语,只是主动承担杂务,照看身边病人,协助整理医药物资。 直到一个寒冷的清晨,她发现毛主席站在院中,脚上穿着明显不合季节的布鞋,她悄悄走近,注意到毛主席脚部浮肿,走动迟缓。 贺子珍解释说这是长征期间落下的脚伤,遇寒加重,普通棉鞋因肿胀穿不上,医务组曾试图制作特殊鞋型,但都无法满足。 同桂荣听后当即在院中找来木棍和纸张,用毛主席踩过的地面测量脚印,裁制鞋样,当天下午,她开始亲自缝制,花了三天时间,做出一双适合肿胀脚型的厚棉鞋。 送鞋那天,毛主席试穿后未作评价,只是点头致谢,不久后,同桂荣在厨房洗衣时被临时叫去贺子珍房中,贺子珍突发阵痛,产兆提前,无人在侧。 毛主席让人去找医生,但山中雨雪封路,医生一时难以抵达,同桂荣迅速接手处理,指挥周围妇女烧水、铺垫、加热炭火,自己负责助产。 经过两个多小时紧急处理,贺子珍顺利诞下一名女婴,医生赶到后负责处理后续,同桂荣则将婴儿小心包裹,送回临时保温的窑洞内安置。 此事在营地引起极大反响,不少干部称她是关键时刻救场的功臣,从此以后,干部中开始有人称她为“刘嫂子”,这个称呼逐渐成为一种惯用名。 毛主席本人在公开场合也沿用这一称呼,甚至多年后仍不时提起,这个称谓既承载了对刘志丹的怀念,也象征着同桂荣在革命群体中的特殊地位。 刘志丹牺牲后,同桂荣没有离队,也未提出任何待遇要求,她继续以普通身份参与队伍生活,担任后勤、通讯、卫生等职务,直到抗战爆发随部队南下。 从前线到后方,从家属到战友,她在不断变换的身份中完成了一次次沉默而坚定的转变,这段经历被极少书面记录,却深深烙印在几代革命者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