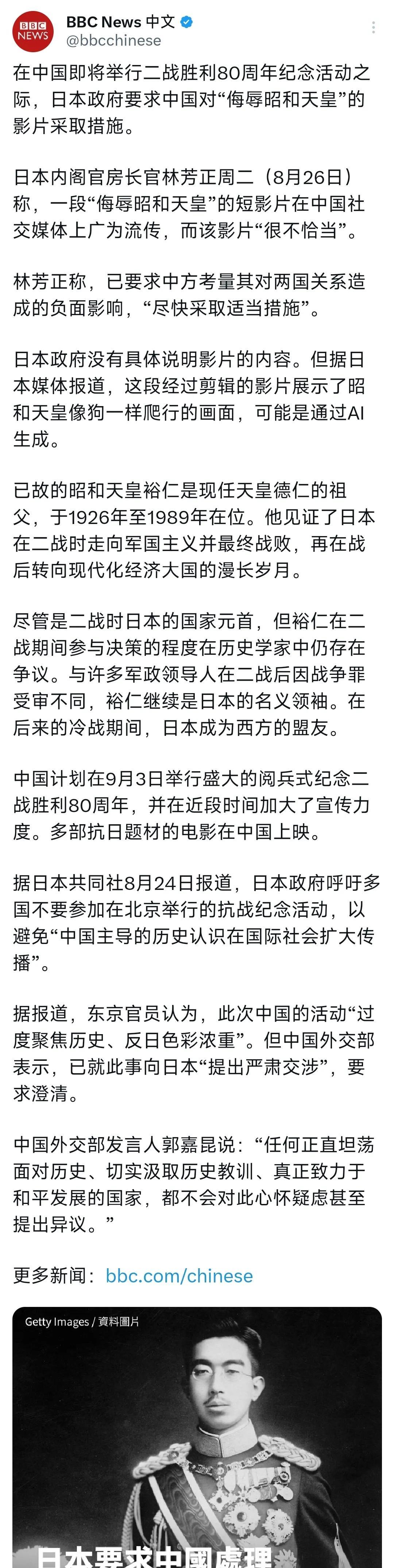公元976年,宋太宗强行临幸小周后。不料完事后,小周后起身穿衣,竟发现10几个男人,在旁指指点点。她羞愤异常,回家对着李煜大骂:“废物!” 开封,寒意已入夜帘。宋太宗赵光义登基才不到一年,宫中密事已传得人心发凉。 那天傍晚,一辆不起眼的步辇从内廷绕道御花园,驶向延和殿,封车重帘,车内人披罗轻裘、面容惨白。是南唐旧主李煜的皇后,周氏,小周后。 她被唤来时没有预告,没有诏书。只一道口令:“赏菊宴请。”她没得选,只能来。 太宗坐在内殿,酒未暖身,人先笑出声,摆手让左右退下,却没让殿外内侍离去。十几个身影站在屏风后,灯影交错,瞳孔发亮。 小周后站着,目光不动,冷得像玉。 赵光义起身,两步走到她跟前,伸手要取她披风。 她没动,眼睫微颤。太宗笑得更响,伸手一扯,丝缎披肩顺肩滑落,砸在地毯上。四周传来低笑,她听得清清楚楚。 没人退,没人躲,没人回避。 她被按进内寝那一刻,外头人脚步声都没断过。帘后窸窸窣窣,有人咳嗽,有人低语,甚至有人蹲下掷骰子,像在看一出戏。 等太宗起身整衣,小周后一言未发,只缓缓穿上被扯下的外袍,步履极轻。 转身那一刻,她眼角瞥见角落一排人影,十几个男人直愣愣站着,盯着她的背,指指点点,有人还带笑意。 她身体猛地一震,脸色发青,连鞋都没穿好就夺门而出。 衣衫不整,鬓乱发散,从御道一路疾行,不顾礼制,不顾禁令。 守门太监见状也不敢拦,只低头作揖,眼神四散。 她冲回住处,一脚踹开厅门,扑到李煜书案前,抬手就扫了他桌上的砚台笔墨。 墨汁溅了一地,她跪坐在地上,脸扭向一侧,牙关咬得发颤,眼泪止不住地掉。 李煜坐在榻上,衣襟未整,一言不发。他知道她去了哪,也知道她去了干什么。她看着他,像在看一堆破布。没说别的,只吐出两个字: “废物。” 那一声不是哭喊,也不是咆哮,是一口冰冷的恨。 李煜脸色煞白,没敢抬头,手攥着衣角,不知躲去哪儿。 他早已习惯这座城里的规矩——跪着活,不准吭。 三个月前,他还在金陵读诗作画,坐拥江山;三个月后,他在开封被叫“违命侯”,住在一座三进院落,出门要通报,进门要验人,窗外每夜都有两个太监盯守。 他被剥光了剑,被抽掉了骨,只剩一张会写词的手。 而他那位美到天下无双的皇后,被这个朝廷当成了一块“贡品”。 赵光义早在攻金陵之前就听说过她的名声,“南唐有美周氏,世间第一”。 如今人到手了,他连脸面都懒得装,设宴就是设陷。 这不是临幸,是羞辱,是故意让她知道,她的夫君保护不了她,她的地位不值一钱。 事情传到后宫,宫女太监心照不宣,只说“周氏美貌,无人及之”,没人提那晚延和殿里的事,连一只灯盏都被换了新。 只有那天夜里宫门口的守卫私下说,那晚送周后回府时,她脚上一只鞋掉了,都没人敢替她捡。 赵光义那几日心情极好,连上朝时都多笑两次。 大臣没人提周后,文官闭嘴,武将低头,谁也不愿多看皇帝一眼。 谁都明白,这女人是南唐旧主的脸,是开封城内最后一块不该碰的骨头,可赵光义偏要踩,还要当众踩。 周后自那日后不再出门,闭居内院,饮食骤减,不再施粉,不再说话。 李煜曾试图安慰,她回身给了他一耳光,一字不说,只哭了一整夜。 这之后不到两年,李煜暴病。 宫中说是秋燥引发旧疾,可南市早就传遍:太宗送来赐酒,李煜饮后未久身亡。 小周后没再哭,她披麻戴孝三日,棺前跪了整整一夜,额头撞得通红。 三个月后,她也死了。死因无记载,有人说是绝食,有人说是服毒。 只有宫中一位老女官悄悄说过:“她死时穿着那日的那件披风,血痕都还在。” 延和殿那块屏风,被人偷偷砍断烧了,内侍说不吉。站在那边目睹那一夜的十几个男人,全被调往冷宫或外省,不得升迁。赵光义下令,此事不得外传,违者斩。 但谁都知道,那一夜开了宋朝后宫百年的风气。 赵光义晚年不提周后,却常常对着黄昏的窗外发呆。他病重那年,梦里多次惊醒,有次还喃喃念着“周氏莫怪”,身边伺候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 没人知道他真怕什么。 小周后的故事,后来散在《南唐书》《闻见后录》里,被人写得模糊又残忍。 她本可是江南最艳的皇后,才名远播,仪态无双,可她的人生,被宋朝这场宫宴活活撕碎。 那天她站在延和殿帘前,看着一排排眼睛在盯她脱衣服。 十几个人,站得整整齐齐,不避,不闪,不羞。她恨得差点咬碎舌头。 她恨李煜,更恨赵光义,但最恨的,是自己活着走出了那个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