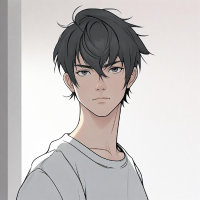在喜玛拉雅山下,居住着一个原始部落,由三千多名卓巴族人组成,他们的性关系开放,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随意住在一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有一块谷地被雪山包围,外界很少有人踏足,那里住着一个叫卓巴的部落,他们的生活节奏,像山泉一样缓慢而清澈,没有人催促他们的时间,他们也不催促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的变化靠观察山花开谢与雪线升降来判断,在这里,时间不是一根鞭子,而是一条温柔的河。 清晨的空气湿润而冰凉,雾气缠绕在村庄的木屋间,天还未全亮,牦牛的铜铃就响了起来,男人牵着牛走向田地,他们不用闹钟,听的是动物的动静和山风的呼吸,女人提着布袋跟在后头,里面装着早春收集的种子,他们犁地、播种的动作不急不慢,像是在完成一场与土地的默契舞蹈。 早餐通常是简单的一碗青稞粥,锅里煮着土豆和豆子,旁边有一小块青稞饼,他们不吃肉,不是吃不起,而是从不杀牲畜,牦牛是帮手,羊是织毛衣的朋友,连山雀飞过时都有人停下手中的活望一望,这种敬重生灵的态度,深入他们的生活细节,溪边洗脸前要闭眼默念感恩,砍树前要给树根系上红布条,曾有科学家想采一段树枝做研究,却被放羊的孩子拦住,孩子没有大声喊叫,只是用手指了指树干,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那一刻,没有语言也足够表达一切。 卓巴人没有结婚证,也不办喜宴,年轻人看对眼,便在节日时送上一束山杜鹃,收到花的人如果系上一根编好的草绳,就代表接受,从那晚起,两人便可以一起生活,若哪天感情淡了,也不用谁责怪谁,女的收拾好背包回母亲家,男的依旧笑着打招呼,没有责难,也不留下伤痕。 孩子出生后不随父姓,而是由部落共同抚养,七八岁的孩子可以叫出村里每一位长辈的称呼,谁家的饭香了,孩子们就往哪跑;谁家门前晒太阳的老奶奶,就会搂着一群娃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没有人指明哪是亲生父母,但每一双手都能把他们抱得稳稳的。 部落的历史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刻在岩石上,山壁上有一些奇特的螺旋符号,学者们发现它们和印度古寺的经文、地中海古代军团的标记有相似之处,传说中,一支在雪山中失踪的古军队曾在这片谷地落脚,后代就成了今日的卓巴人,他们的五官深邃,有着欧亚混血的轮廓,但他们自己并不在意这些传说,对他们来说,祖先的脚印就留在冰川之上,风吹过时会轻声讲述。 每年秋天,部落会有一个丰收节,那时篝火点燃,男人张开双臂模仿苍鹰盘旋,女人转圈跳舞,银饰撞击发出叮当声,孩子们围着火堆跑来跑去,笑声在山谷里回响,火星飞舞到岩壁上,照亮那些牛头图腾和古老的岩画,酒坛在手中传递,酒是用神泉水酿成的青稞酒,入口温热,像山里的阳光。 有一年,谷地经历了四十天的干旱,水源减少,青稞苗干枯,没有人各自藏粮,而是家家户户将剩下的粮食倒进一个大木槽里,分给最需要的人,孩子们光着脚在泥地里跳舞,老人坐在旁边看着,悄悄抹了眼角的泪水,这种共享的习惯不是制度规定的,而是从一代代人的行为中自然流传下来。 卓巴人的生活看似简单,却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秩序感,暴雨冲垮了山路,村民不用吩咐,自动扛着锄头上山修路,修完后,还会在滑坡的崖壁上系上五彩经幡,像是对山神的一种安抚,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山有山魂,水有水性,人只是其中一环。 这些年,外界的变化悄然抵达,卫星信号爬进谷地,年轻人开始用手机拍摄鹰舞和雪景,开始有人进山拍广告,给部落的孩子穿上不属于他们的衣服,牵着牦牛拍照,拍完,孩子们争抢酬劳,第一次在村口的木槽旁立起了篱笆,那是他们第一次因为“财产”而划出界限。 更严重的是生态的改变,冰川退缩,曾经汩汩流淌的神泉变成了断续的水线,青稞田里的裂缝像张开的嘴,干渴地等待雨水,有人提议开始宰杀牲畜换食物,这是部落第一次在长老会上讨论是否破除旧规,信仰和生存之间,裂缝悄然生长。 为了不让文化消失,一项复刻岩画的计划悄然开展,长老带着少年们,用矿石磨成的颜料,一笔一画描摹那些正在风化的古老符号,新一代在岩壁上重写祖先的记忆,也在日记本上写下新的谚语:“钢筋水泥养不活灵魂,雪山的水才能养出笑容,” 谷地里,还有些外来者留下来了,一个曾三次被雪崩掩埋的登山者,如今成了养蜂人,他的蜂箱摆在神泉的下游,孩子们蹲在旁边眼巴巴地看他割蜜,他总会抹些蜜在荞麦饼上,递给他们吃,孩子吃得满脸都是,他笑着说,花蜜明年还来。 信息来源:国际地理——《雪原遗民:喜马拉雅部落的现代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