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去北京开会前,耿飚向军委下指示:不要给许司令员派专机了 “(1982年3月,北京)耿飚同志,这趟还给许老单独安排飞机吗?”办公厅小李探着身子问。耿飚摇头:“民航就够了,让他在群众面前露个脸。”话音很轻,却足以改变一位上将的行程。 那一年,全国人大常会即将召开,来自南京中山陵8号的许世友被列入与会名单。老人已七十三岁,腰腿有时不听使唤,但精神头依旧硬朗。为了这趟出行,他提前一周自己打包——旧军装、草药、还有一本字迹模糊的《孙子》。他向身边人咧嘴一笑:“带专机?多折腾,坐班机省心。” 在北京,那些流言越刮越猛,说许世友固执、说他拒绝新政策、甚至说他成天躲在深山不理政事。谣言像潮湿的雾,越捂越大。耿飚觉得得给大家一个实情,“就让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真真假假一眼便知。” 回看许世友近几年的人生轨迹,确实颇为反常。1976年毛主席逝世,他守灵九天不合眼。1979年中越边境炮火刚停,他却主动请缨撤回二线。别人眼里是急流勇退,他嘴里却只有四个字:“身子骨累。”后来调任广州军区,他嫌那儿湿气太重,一句“南京适合我”便回到了中山陵。 搬进孙科旧宅后,他把原本精致的草坪翻得乱七八糟,改成四畦庄稼地;邻墙贴着马路,他又琢磨着搭猪圈。南京军区的年轻参谋见了直挠头:“堂堂大将,非得喂猪?”许世友笑:“自己动手,才晓得粮食来之不易。” 身体倒是一天比一天闹腾。脚痛风、腰椎骨刺,爬山打猎都成了奢望。为了活动,他发明了“颠车法”——每周两回让司机开吉普在陵园小路蹦蹦跳跳。后来听说国家油料紧张,他索性减到一周一次,“不给国家添麻烦。”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下发,各地讨论激烈。许世友一见“历史评价”四个字,立刻提笔写长信:“成绩讲够,别忘了教训。”信里的每个字都挂着重量,他照例把毛主席的照片摆在案头,看一眼,落一笔。 也正因这份直率,外界猜测更多。有人把他对领袖的忠诚解读成“保守”,有人乾脆断言他“脱离群众”。耿飚和杨尚昆商量,干脆让许世友搭民航,公开亮相,堵悠悠之口。杨尚昆说:“他是个明白人,会配合。” 军委通知下到南京,秘书李福海捧着文件心里直打鼓。许世友听完指示,只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削铅笔。动身那天,他穿着洗到发白的旧呢子大衣,提前半小时抵机场。候机大厅里,不少旅客认出了这位“活传奇”,掌声、招呼此起彼伏。老人拄着拐杖,笑着说:“各位好,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四个小时后,飞机平稳降落首都机场。陪同人员暗暗松气,而许世友下舷梯的第一句话是:“这趟挺顺,民航不比专机慢。”随即被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大手一摆:“要问就问,中午我还得开会。” 会场间隙,杨尚昆快步迎上来。两位老兵握手许久,杨尚昆半开玩笑:“专机没坐习惯吧?”许世友直爽:“我这身板,让群众看看没坏处。”一句话,把流言撞了个稀碎。 会后,他专门留出两天走访老部队,给战士们讲边境实战经验;还到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替孩子们系红领巾。小学生问:“许爷爷,您打过仗吗?”他哈哈大笑:“打过,但和平更好玩。” 然而身体的警报并未因北京之行而消停。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关节病变加剧,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历本愈加厚重。中央多次电请他赴京治疗,他却一句“北京路太窄”,把关心都挡回去。老部下聂凤智飞来劝,他还是两个字:“不去。”你急他慢,最后只能留下一长串叹息。 1985年10月22日清晨,雨点敲打医院窗台。监护仪的指针悄悄停住,许世友安静地在病房里合上眼。消息传到北京,军委通电致哀,邓小平批示“沉痛悼念”。南京城那一天格外阴沉,高粱地、猪圈、老宅,以及半张没写完的批条,都成了永久的纪念。 耿飚后来提起那次“取消专机”的决定,说:“他一辈子刀口舔血,却最怕麻烦国家。民航一坐,反倒让百姓见着了真英雄。”一句平常话,道出一代名将骨子里的坦诚与朴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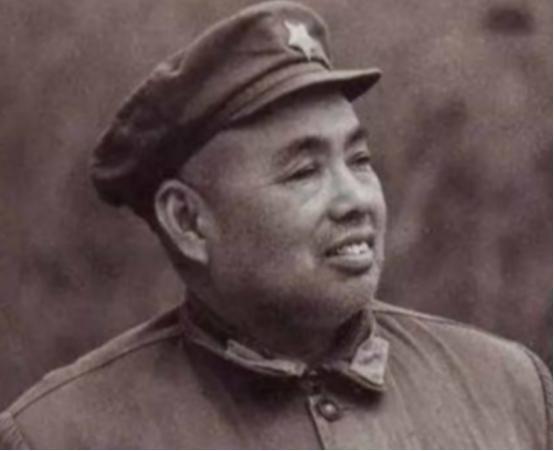


用户10xxx99
文字编写应该这样:耿飚向军委办公厅下指示。这样妥当些
王剑
耿飚是国防部长,向军委下达指示?应该是军委付主席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