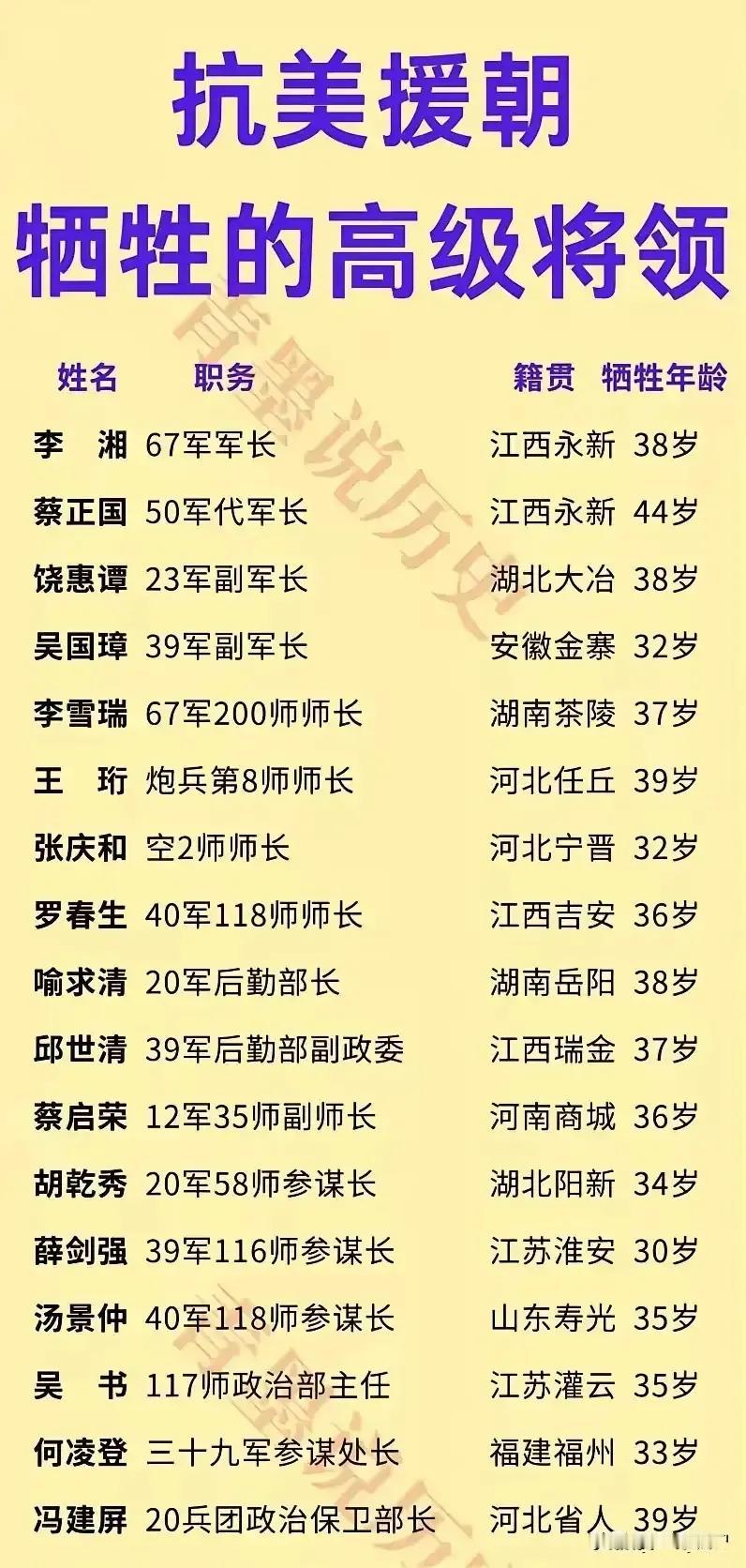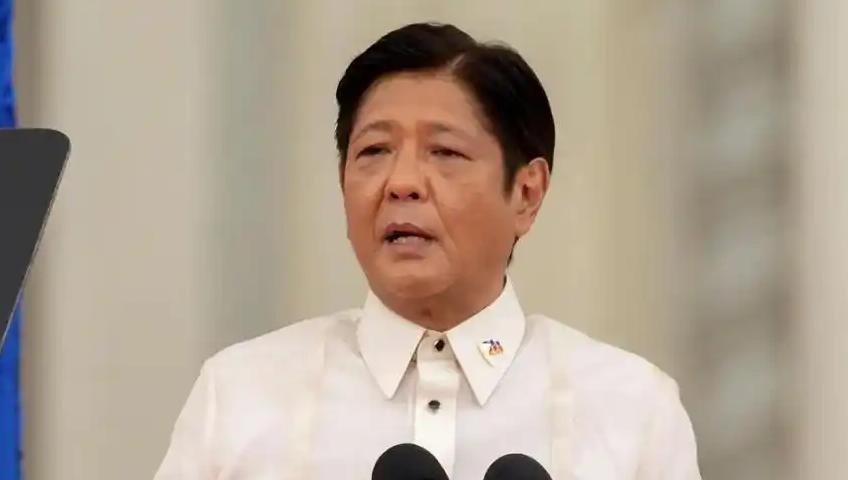在毛主席的晚年生活中,有一位护士长陪伴了毛主席将近21年,这么多年,两个人相处的非常融洽,可以说不是父女,却胜似“父女”。然而,毛主席却在一次谈话中,和她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的起点其实挺普通的。她1928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家里条件一般,父亲是个小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她从小就聪明好学,性格也直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投身医疗事业,先是在杭州当护士,后来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北京。 1953年,25岁的吴旭君被选进中南海,成了毛主席的专职护士长。这个机会对她来说,既是荣誉,也是挑战,毕竟要照顾的是一位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 刚开始,吴旭君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1年。她进入中南海时,毛主席已经60岁了,身体不算太差,但随着年龄增长,各种健康问题慢慢浮现。 吴旭君的工作不光是打针喂药,还得随时观察他的状态,调整生活习惯。她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性格直率,有啥说啥,这点倒是跟毛主席挺合拍。 时间久了,他们之间就不再只是护士和病人的关系,而是多了份信任和默契。 要说这21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真得聊聊那些日常里的点滴。毛主席是个大忙人,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吴旭君就得跟着他的节奏走。 他喜欢熬夜看书,她就得半夜起来给他准备茶水;他抽烟抽得凶,她就得劝他少抽点,虽然劝了也白劝。毛主席脾气有时候挺倔,但吴旭君从不怕顶嘴,有时候还跟他开开玩笑,逗得他哈哈大笑。这种相处模式,慢慢就让他们的关系变得特别。 你知道吗,毛主席对吴旭君的信任不是随便来的。1960年代,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尤其是心肺功能不太好,吴旭君得随时盯着,不能有一点马虎。她不仅要管医疗,还要管生活,连毛主席吃什么、睡多久,她都得操心。 时间长了,毛主席对她依赖得不得了,有啥不舒服第一个找她,甚至有时候心情不好,也会跟她唠唠嗑。这种信任,搁在别人身上还真未必能做到。 他们之间的感情,说不是亲情吧,可又比一般的工作关系深得多。吴旭君比毛主席小35岁,年纪上完全可以当他的女儿。她照顾他那么多年,毛主席自然也把她当家里人看。 1963年某晚,毛主席又一次失眠。他让吴旭君过来,陪他聊聊天。这不是第一次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毛主席思虑渐多,失眠也成了常事。而能听得懂他话、又能给他一点心灵慰藉的人,并不多。吴旭君是其中一个。 这一次,毛主席说起了他的母亲。他说,她是个普通农村妇女,善良、老实、不识字,也不懂什么“群众工作”,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死的时候,很多人自发来送别。 “跟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不一样。”毛主席提到他父亲,语气沉了一下。 他一向对父亲的印象复杂。儿时被父亲管得很严,甚至有些苛刻。这种记忆刻在心里,到了晚年还时不时涌上来。毛主席顿了顿,接着说了一句让吴旭君没想到的话:“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一下子怔住了,赶紧说:“您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您身边呢?” 可毛主席是认真的,他又重复了一遍,“不,我死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在我跟前。” 看着吴旭君迷惑的表情,毛主席缓缓解释:“我母亲临终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在我记忆里,永远是健康、精神的样子。”这句话,吴旭君后来很多年都记得。 毛主席对于生死,其实早有准备。他不是不在意,而是早早就想明白了。他曾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主动提议,中央领导人都应火化、简葬。他是第一个签署火化协议的人。 他不希望身后搞排场、不希望占用耕地,更不想为后人留下任何“形式负担”。在那个年代,这种态度其实非常超前。可惜的是,最终因为政治原因,他的愿望并未实现。 这些安排,其实早已透露出他对生死的坦然。他还跟吴旭君说过,自己死后,想把骨灰撒进长江喂鱼。吴旭君听了急得不行,连连摇头。但毛主席笑着说,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的。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他说得轻松,吴旭君却听得心头发沉。 1974年,她主动辞去了护士长的职位。毛主席说过,希望她永远记住他精神、健康的样子。吴旭君理解他的那份执念,也尊重他的决定。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吴旭君没有在场。她遵从了毛主席当年的叮嘱。但多年以后,她常常穿着鲜艳的衣服去看他。不是为了“显眼”,也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毛主席说过,母亲去世那天,他穿着红小褂,因为希望母亲看到自己最好的样子。 这是一种特别的默契,不用语言表达,但彼此都明白。哪怕再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心里那种惦记、那份敬意,也一直都在。 很多人说,这段关系是“父女”,但吴旭君从没说过。她只说:“我是一名护士。” 可她为毛主席做的,早已超越了职责。她做到了体面、得体、安静,也做到了真正的理解。 毛主席说,“我死时,你不要在我跟前。”吴旭君答应了。 但事实上,她一直在——只是以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