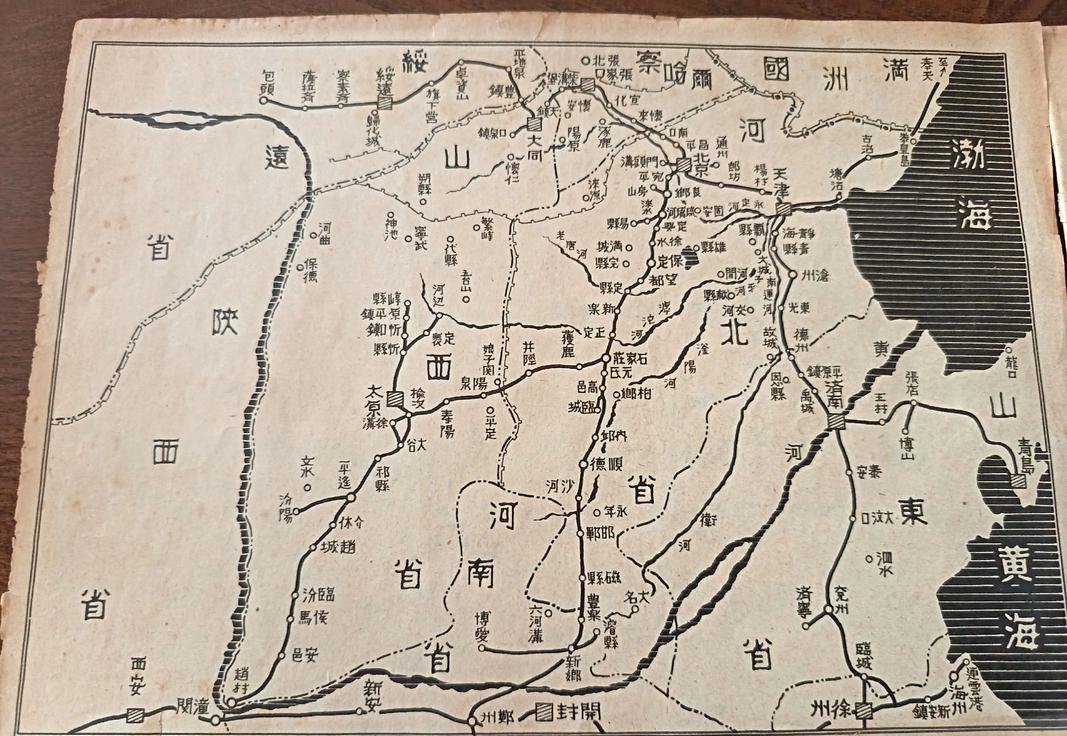1928年,张作霖临死时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他最爱的五姨太。但是张作霖死后,他最爱的五姨太不仅没有给他发丧,反而在他死后,滴泪未落,还整日浓妆艳抹,打牌喝酒。 1966 年台北的梅雨季,张寿懿对着镜子涂最后一次胭脂。90 岁的手颤巍巍拧开雪花膏,瓷瓶上的牡丹花纹让她想起 1928 年那个清晨 。 皇姑屯的爆炸声震碎车窗时,张作霖溅在她旗袍上的血,也像这样晕开在暗花绸缎上。 侍女说日本人的电报又来催问 “大帅安康”,她却对着镜子扯出笑容,胭脂抹得比往日都红,仿佛要把岁月的褶皱都填成戏台的油彩。 1928 年 6 月 4 日的帅府地窖里,张寿懿摸着张作霖军装口袋里的怀表。表盖内侧刻着 “五儿亲启”,指针停在 5 点 30 分,正是专列被炸的时刻。 她把带血的怀表塞进贴身肚兜,转身对吓傻的丫鬟说:“去把大帅的翡翠扳指找出来,今晚要陪日本领事夫人打麻将。” 梳妆台上的香槟冰桶冒着寒气,而她藏在旗袍里的手枪,枪管还留着昨夜擦枪时的润滑油味。 三天前她在奉天女子师范的毕业典礼上,还对着全校师生讲 “女子亦当为国分忧”。 此刻却要对着日本领事夫人的和服腰带数针脚 —— 那上面绣着樱花图案,和皇姑屯铁轨旁的弹壳一样刺眼。 “大帅只是受了风寒,” 她用银勺搅着香槟,冰块碰撞声里藏着心跳,“您看这气色,前儿还说要亲自去旅顺看樱花呢。” 领事夫人的折扇停在半空,没看见她袖口渗出的血迹,那是刚才给张作霖换绷带时蹭上的。 19 岁嫁进帅府的那个雪夜,张作霖把她抱上雕花大床,说 “你这脑子,比我的枪还准”。 此刻她摸着床头张作霖送的金簪,簪头的珍珠沾着泪水,却硬生生被她抹成了脂粉。 厨房送来的 “病号餐” 冒着热气,她掀开食盒一角,看见底下压着张学良从北京发来的密电:“子已启程,母需稳三日。” 而窗外,日本关东军的巡逻马队正踏过帅府青石板,蹄声像极了当年张作霖教她打枪时的后坐力。 最险的是第六天,日本领事突然闯进卧室。她正给 “昏迷” 的张作霖擦身,带血的毛巾藏在被褥下,脸上却笑着递过雪茄: “大帅刚服了洋医生的药,说这牌子和您送的一样好。” 领事的手指划过床单上的血渍,她立刻倒了杯威士忌: “您看这酒色,跟大帅最爱喝的‘烧刀子’一个样。” 酒杯碰在桌角的声响里,她听见自己心跳如鼓,却看见梳妆镜里,当年那个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女学生,正隔着岁月对她点头。 张学良赶回奉天的那晚,张寿懿卸了妆坐在灵堂。铜镜里的女人眼窝深陷,旗袍上的血渍已变成暗紫色,像朵开败的牡丹。 她摸着张作霖的棺材,突然想起 1925 年他亲征郭松龄时,临走前塞给她的勃朗宁手枪: “要是我回不来,这枪比眼泪管用。” 如今枪还在枕下,而她用 13 天的浓妆,给东北换来了三年的喘息。 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时,她带着孩子们逃往天津。 轮船驶过渤海湾,她把金簪扔进海里,簪头的珍珠在浪里闪了闪,像极了当年张作霖看她演讲时,眼里映着的礼堂灯光。 有人说她没心没肺,却不知她藏在胭脂下的算计:若当时哭丧,日本关东军的坦克早该碾过奉天城门。 台北阳明山的养老院里,她常给孙辈看一张泛黄的照片。1928 年 6 月的帅府花园,她穿着艳红旗袍站在牡丹丛中,身后的假山石后,藏着给张学良送信的侍卫。 照片上的笑容明媚,没人知道她袖中攥着张作霖的遗嘱,纸角已被指甲掐出了血痕。 直到 1966 年梅雨季的最后一天,她对着沈阳方向闭上眼,临终前呢喃着:“那年的香槟,该再冰些......” 侍女替她合上眼时,发现她掌心里还刻着三个字:“勿发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