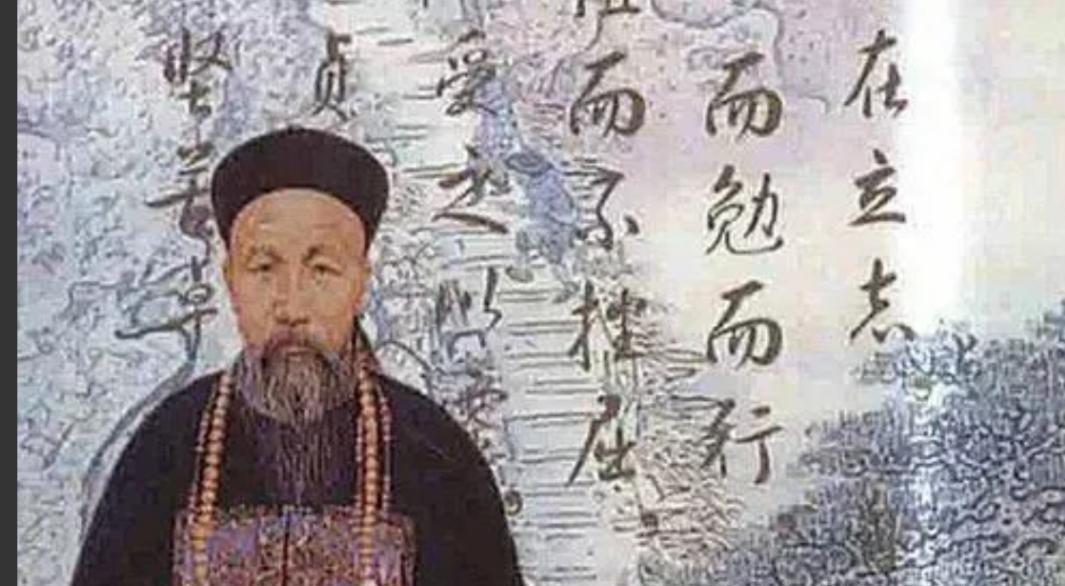1852年,母亲去世,二品侍郎曾国藩回家奔丧。从湘乡县城到老家荷叶塘,五十里路,他没有雇轿子,步行一整天到达村口。 那年夏天,湘乡的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 二品兵部侍郎曾国藩踩着滚烫的黄土路,官靴早就蒙了厚厚一层灰,补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 从湘乡县城到荷叶塘老家的五十里山路,他执意不坐轿子,深一脚浅一脚走着。 仆从荆七跟在后面直抹汗,心里嘀咕老爷这是何苦,京城里那些二品大员,哪个不是八抬大轿出入? 可曾国藩的步子越走越沉,眼神却越来越亮,仿佛每一步都在丈量着与母亲的距离。 十五年前离家时,母亲江氏送他到十里长亭,把攒了半辈子的碎银子全塞进他行囊,反复叮嘱“莫要贪凉”。此刻路边的野菊花黄灿灿开着,和当年母亲鬓边的绢花一个颜色。 他突然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碎花瓣的泥土攥在手心,当年母亲就是踩着这样的土路,把晒好的腊肉送到县学给他加餐。 这段看似寻常的奔丧路,藏着曾国藩人生最痛的转折, 就在半年前,他还是道光朝那个“刺头侍郎”,在咸丰登基后以为新君能纳谏治国,竟接连呈上两道奏折。 头一道《应诏陈言疏》痛陈朝廷“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漕运浮收、官民交困”“兵饷不继、将士离心”四大积弊,把满朝同僚得罪个遍。 第二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更列数皇帝“琐碎”“虚文”“骄矜”三项短处,连龙椅上的咸丰也惹恼了。 京师内外骂声一片,他这个侍郎成了众矢之的,国事艰难之际,皇帝怠政,百官缄默,偏偏曾国藩非要当那个戳破窗户纸的人。 没人知道那天的灵堂里发生了什么,黄金堂的素幡被穿堂风掀起,露出后面“音容宛在”的匾额。 曾国藩扑在棺木上时,榫头缝隙里飘出淡淡的檀香混着石灰味,他疯狂拍打棺盖要求开棺,族老们拗不过只得起钉。 母亲面容比他想象的更安详,嘴角甚至带着若有似无的笑,后来才知道,那是江太夫人接到儿子诰封一品夫人的皇诰时,“一笑成仙”留下的痕迹。 这个发现让他哭得更加撕心裂肺,母亲临终前指着柜子,家人搬出所有物件都不对,最后是父亲悟到她要摸儿子寄回的家书。 那一大捆信被摸得起了毛边,最上面那封还沾着汤药渍,想必是病重时也要让人念给她听。 道光年间的官场失意与此刻的丧母之痛,像两把刀同时剜进心里。 当年那个在翰林院意气风发的青年,十四年间“十年七迁”做到六部侍郎,却因直言进谏成了官场异类。 如今母亲临终前没见到儿子身穿二品官服的模样,自己也没能端上最后一碗汤药。 灵堂烛火噼啪爆了个灯花,惊醒了昏睡中的曾国藩,他发现自己还攥着母亲入殓时穿的蓝布衫袖口,上面有他熟悉的补丁针脚。 三弟国潢凑过来要扶他去休息,他甩开手又扑回棺前,这举动把满屋子人都吓住了,谁能想到平日最重礼法的二品大员,此刻竟像个撒泼的孩子。 夜深时下起小雨,瓦片上叮咚作响像谁在轻轻叩门,曾国藩突然起身往外走,族人们不敢拦,只远远跟着。 他竟一路走到母亲生前住的厢房,从床底下拖出个落灰的樟木箱。 箱里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多双布鞋,从孩童的虎头鞋到官靴尺寸俱全。 每双鞋底都纳着“平安”二字,最新那双的针眼还泛着白,分明是母亲病中强撑着做的。 当年离家时母亲乌发如云,如今灵堂里的棺木却已漆黑如夜。 这个发现比任何奏折遭拒都更刺痛他,在官场碰壁时总以为还有退路,直到母亲坟前的黄土告诉他,有些遗憾永远补不回来了。 出殡那日,湘乡的百姓自发赶来送行。,曾国藩披麻戴孝走在最前头,素白的孝衣沾满尘土。 黄土落进墓穴时,他突然想起十三岁那年贪玩落水,母亲背着他走了五里路求医。 现在终于轮到他扛着母亲了,可却不是为了就医看病,是永远的分离。 这场丧事过后,他在老家守孝的三年里,日日反思自己追逐功名却疏忽至亲,后来在日记里写“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墨迹总在“待”字上晕开一大片。 那个因得罪皇帝被晾在冷板凳上的侍郎,偏偏在丁忧期间被太平天国战火逼出山,阴差阳错成了湘军统帅。 母亲葬礼上坚持抬棺的双手,后来握住了半壁江山的兵权;在灵前哭到脱力的男人,最终成了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可当南京城的捷报传到荷叶塘,曾国藩却独自在母亲坟前坐了一整天。 他或许想起了咸丰二年那个盛夏,如果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他会不会少写两道奏折,多回几次家? 可惜世上从没有如果,只有棺木上“诰命夫人”的金字,默默见证着忠孝难两全的千古困局。 主要信源:(文摘报——曾国藩在京买不起房产;湖南日报——曾国藩之母江氏:一位湖南母亲的京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