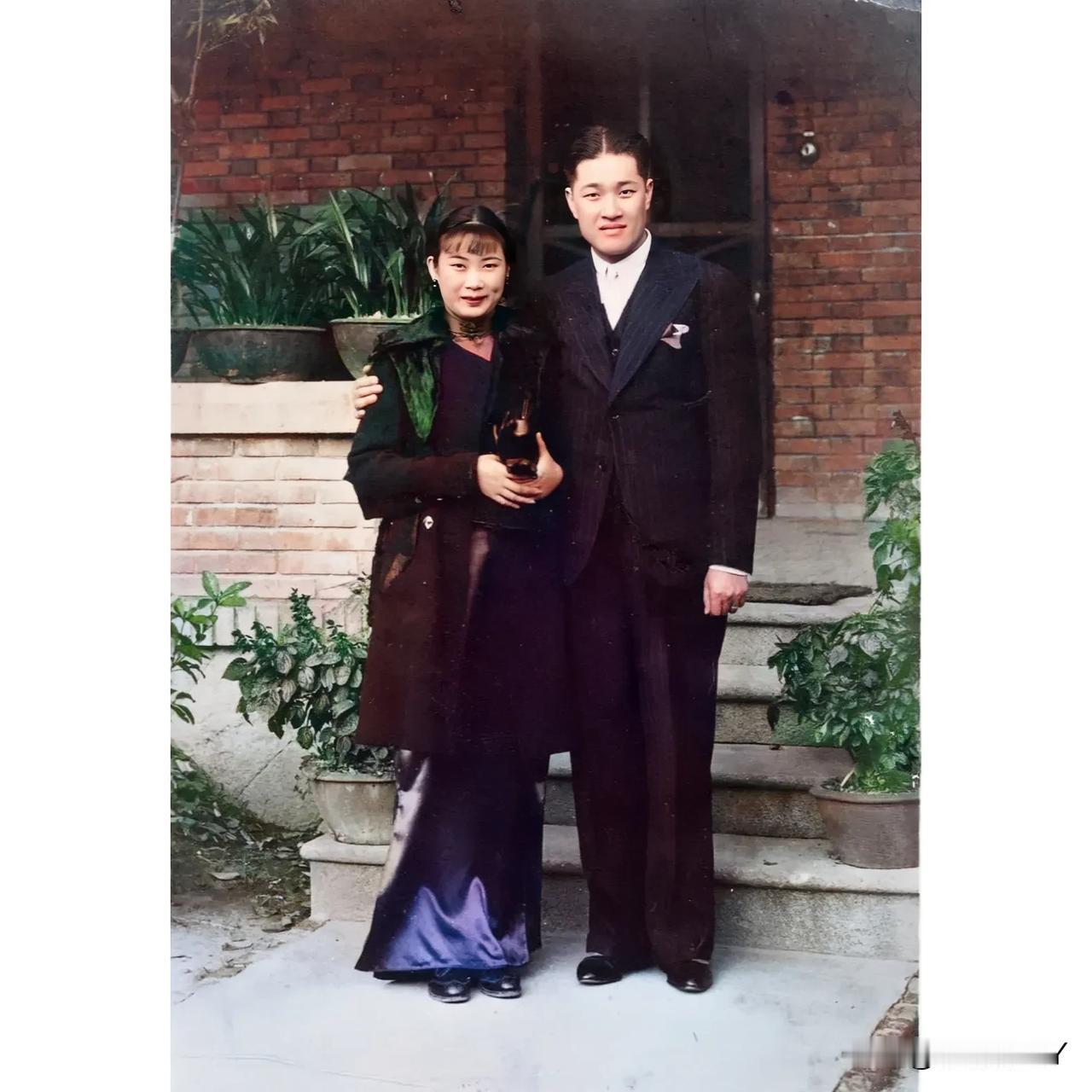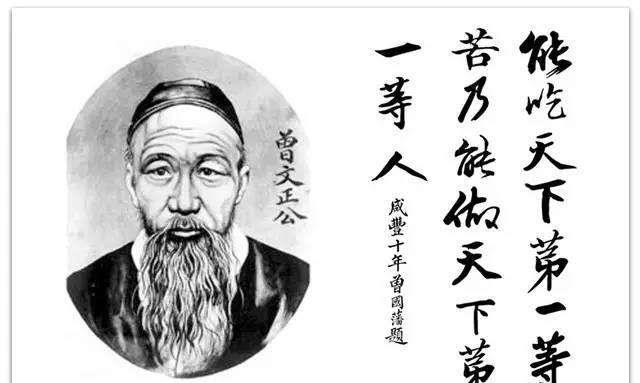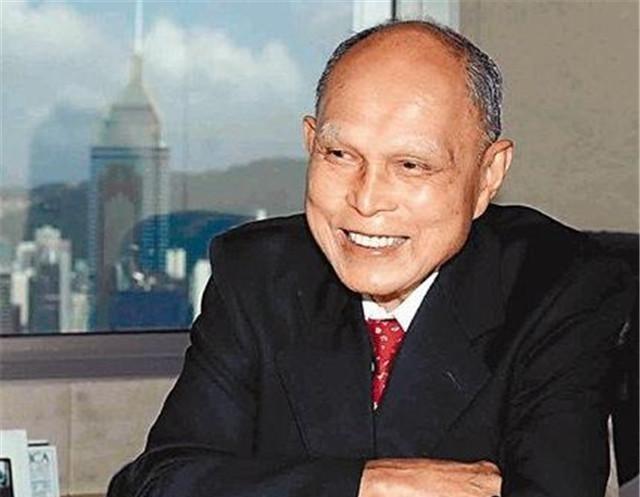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十年。一个人死后还能被“处置”十年,这不是恐怖故事,这是清朝真正发生过的事。那年是雍正四年,十月初三,天刚擦亮,菜市口法场人头攒动。汪景祺,52岁,斩首示众。他的头颅高高悬挂,不像普通死囚,晒一天、两天,风干了就算。这一挂,就是整整十年,直到乾隆登基才准许收尸。 一场“文字狱”的极致演绎。有人写文溜须拍马,结果人头落地,还不能入土为安。是他不识时务,还是这一代帝王心狠手辣?汪景祺的故事,要从头讲起。 这人出身不差,字无巳,号星堂,是江苏人。少年得志,年纪轻轻便中过举人。后来想进士不中,换条路走,靠人脉靠文才混官场。他最风光的时刻,是进了年羹尧的幕府。那时候年羹尧如日中天,青海平定、西藏复归,一时威名压过诸臣。 年羹尧器重他,没把他当下人使唤,而是真当“文胆”看待。随军西征,他带着笔墨卷轴,边走边记,写出一本《西征随笔》。这书写得太猛了,猛在哪?不是骂人,而是夸人,夸得肉麻,夸得夸张。他说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还说“千古未有”,把唐朝的郭子仪、宋代的裴度都贬下去。他不止夸年羹尧能打,还暗戳戳贬圣祖康熙,说什么“今得人矣”,暗示康熙不识人,年羹尧才是真明主。 这些话当时没事。年羹尧得宠,他跟着吃香喝辣。但风水转得快。雍正三年,年羹尧被查。前后不到半年,罪名越查越多,从擅权自大到勾结番地,洋洋洒洒九十多条。最后雍正赐他自尽,算是留了点体面。但跟着年羹尧混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成了“铁证”。皇帝亲自翻阅,勃然大怒:这是讥讽先帝、捧杀我朝大臣的“悖逆之书”。书中文字被拿出来逐字分析,一句句拎出来定罪。于是文人落难,罪名不是谋反,不是通敌,而是“狂悖不经,大逆不道”。 雍正办案讲效率。十月初三,汪景祺在菜市口被斩首。他不是高官,他连年羹尧身边的红人都算不上,但这案子要立威。杀了他还不够,要“警后人”。所以脑袋挂起来,不给收,不给葬,任凭风吹日晒,雨打霜冻。 菜市口是北京最繁华的法场,百姓买菜经过,商贩小贩来来往往,人人都看见那颗头颅。头发掉了,皮烂了,最后剩下一副干枯的骷髅。人们背地说:“这不是脑袋,是皇帝立的招牌。”清代文字狱不少,但像汪景祺这样死后还要被示众十年的,只有这一个。 这还不够。他的妻子,被发配到黑龙江做苦役。兄弟亲族五服以内,统统革职,发配宁古塔。书生写文,本是风雅之事,这一回成了灭门之祸。 这一挂,就是十年。不是因为没人说情,是没人敢说。雍正朝权力集中,敢言者寥寥,哪怕清流言官也噤若寒蝉。文人自此写字谨慎,连“圣祖”两个字都不敢随便提。 到了1735年,乾隆登基。新皇初政,讲究“宽大”,也要洗去雍正的铁血印象。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说:“头颅悬了十年,是不是该让人家入土为安?”乾隆点头。这一年,汪景祺的头终于从菜市口摘下,择地埋葬。 故事到这儿,好像告一段落了。但余波未息。《西征随笔》被列为禁书,连抄本都被追缴。谁收藏,谁传阅,轻则革职,重则治罪。文字狱,从“隐讳”到“颂敌”,每一步都踩在刀锋上。汪景祺死得不是最冤的,但却是最“吓人的”。他的头,像一块活生生的碑,竖在京城最热闹的路口。 历史没有如果。如果年羹尧不败,汪景祺可能官运亨通;如果他少写几句浮夸拍马的词句,也许能全身而退。但历史不是小说,不讲情理,只讲结果。清朝两百多年,文字狱上百起,多少文人因言获罪,汪景祺只是其中之一,却因那颗悬挂十年的头,被永远记住。 他不是谋士,也不是奸臣。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想走捷径的书生。写了几段诗文,想博权贵一笑,却没想过权贵也有垮台那天。更没想到,皇帝的笑脸背后,是冷得让人骨头发凉的杀机。 十年,一颗头。没有更冷的象征,没有更沉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