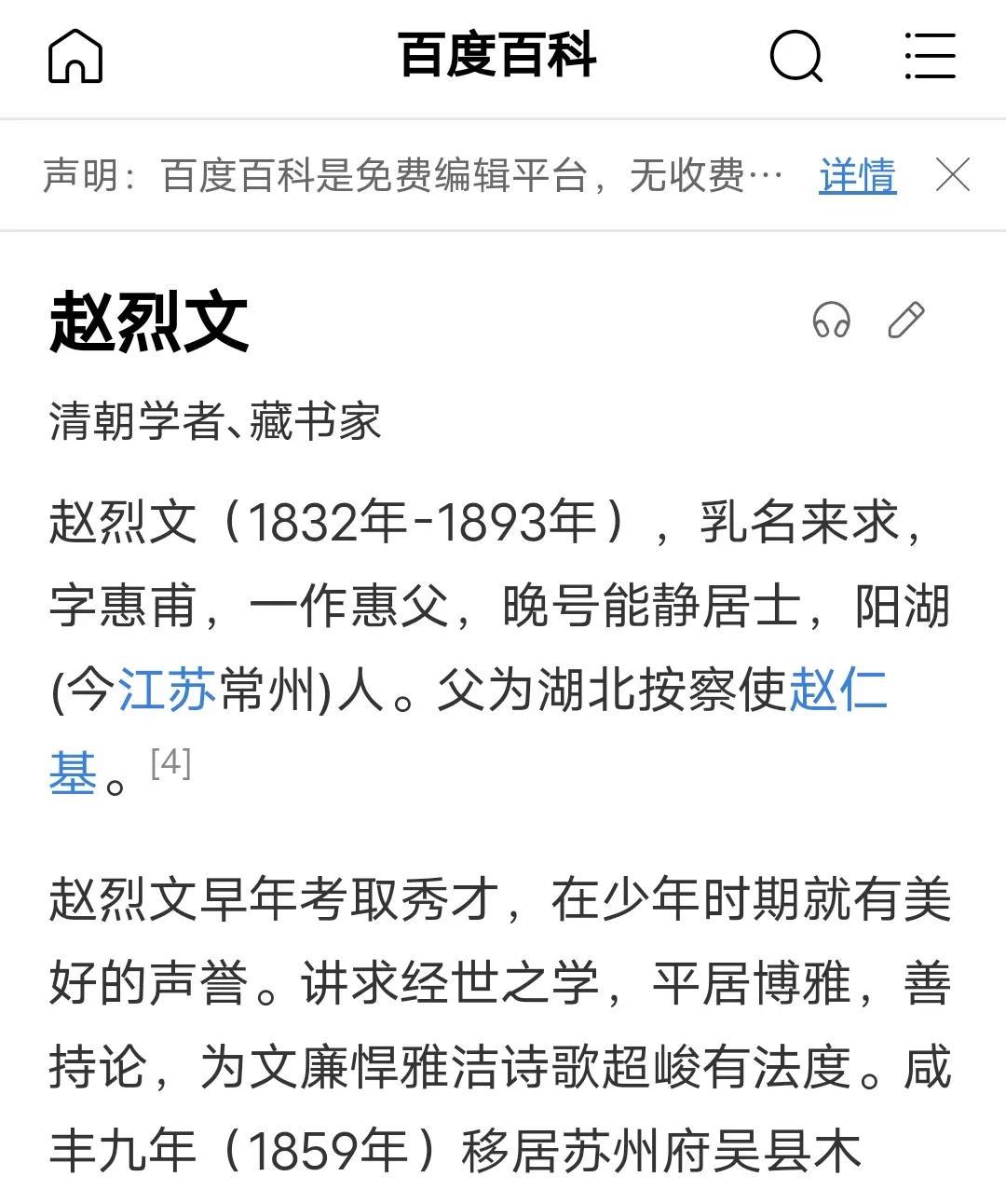1867年,赵烈文对曾国藩预言,大清50年内必定灭亡,曾国藩不信,赵烈文说:得天下太容易,开国时又太残暴,这些都有违天道,岂能长久?44年后,武昌一声炮响,宣统帝逊位,清朝果然彻底覆灭。 1867年盛夏的一个深夜,两江总督府书房烛火摇曳。 曾国藩刚放下前线战报,赵烈文便推开舆图,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中堂,大清气数将尽,不出五十年必亡。” 窗外的蝉鸣突然显得刺耳。 这个在镇压太平军中挽狂澜于既倒的湘军统帅,此刻脸色铁青。 他并非看不清朝堂积弊,却仍抱一丝幻想:“或可效仿南宋,划江而治?” 赵烈文摇摇头: “大清以杀戮得天下,人心尽失。届时恐非分治,而是土崩瓦解,群雄割据。” 烛火爆了个灯花,映着曾国藩额角的冷汗。 这位他视为子侄的幕僚,竟如此断言帝国末路。 故事要追溯到三十年前。 江苏阳湖赵家是显赫的官宦世家,明清两代出过九位进士。 1832年出生的赵烈文四岁开蒙,天资聪颖。不幸十二岁那年,任湖北按察使的父亲赵仁基病逝任上,家道中落。 幸得父亲故交王蓉坡接济,赵家才免于困顿。 成年后的赵烈文虽满腹经纶,却三试不第,心灰意冷下彻底放弃科举。 当同龄人热衷功名时,他在老家闭门苦读。 二十四史、易经理数、佛学典藏塞满书斋,更密切留意时局变化。 这份“不务正业”反倒培养出他洞察世事的眼光。 转机出现在1856年。 在姐夫周腾虎的引荐下,赵烈文赴江西谒见曾国藩。 初见时,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并未引起湘军统帅重视。 途经南康大营时,赵烈文发现湘军将领周凤山部“号令涣散,士卒嬉游”,当即上书直言隐患。曾国藩阅后大为不悦,认为这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赵烈文见不被接纳,借口母亲病重请辞。 就在他收拾行囊时,前线传来樟树大败的消息——竟与其预判完全吻合!曾国藩当即策马追回他,从此将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视作心腹智囊。 随侍曾国藩的岁月里,赵烈文屡献奇谋。 当众人沉迷征伐时,他率先提出兴办实业、筹建海防;当清廷忙于扑灭太平军时,他已看透旧制度腐朽的根源。 1862年姐夫周腾虎病故,他亲赴南昌接回守寡的姐姐和外甥抚养。 这份重情重义令曾国藩更加器重。 南京收复后,保举他出任职官。 在磁州、易州担任知州期间,赵烈文断案如神:磁州有豪强霸占民田,他微服查访人证物证,三日即判归原主;易州遇大旱,他亲率百姓开渠引水,活人无数。 百姓称他“赵青天”,他却总对亲友慨叹:“杯水车薪,难挽乾坤。”。 赵烈文与曾国藩的命运转折同在1867年。 那年夏夜预言之后,曾国藩虽未全信,却夜不能寐。 两年后他调任直隶总督,临行前将赵烈文外放知州——既是酬功,也是避免预言泄露招祸。 1872年曾国藩病逝南京,赵烈文闻讯呕血痛哭。 当时他在易州任上,百姓因他拒征苛捐杂税感念不已,却不知刺史府深夜常亮着青灯,案头摊着未完成的《能静居日记》。 次年四十三岁的他挂印归乡,同僚劝他谋取巡抚高位,他笑答: “譬如看戏,已知终场锣响,何必争坐首席?” 常州郊外的赵家老宅成了他的桃花源。 旧属来访常惊讶其俭朴:书房四壁藏书,院内自种菜蔬。 三任妻子相伴,每日不过读书会友、郊游钓鱼。 偶有官员携重礼求教,他一概婉拒:“江湖之远,不闻庙堂。” 1893年秋,六十二岁的赵烈文于家中安然离世。 他闭目前窗外金桂飘香,彼时距离甲午战争爆发仅余一年,大清国运正如他二十六年前预言的那样,向着崩解的深渊急速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