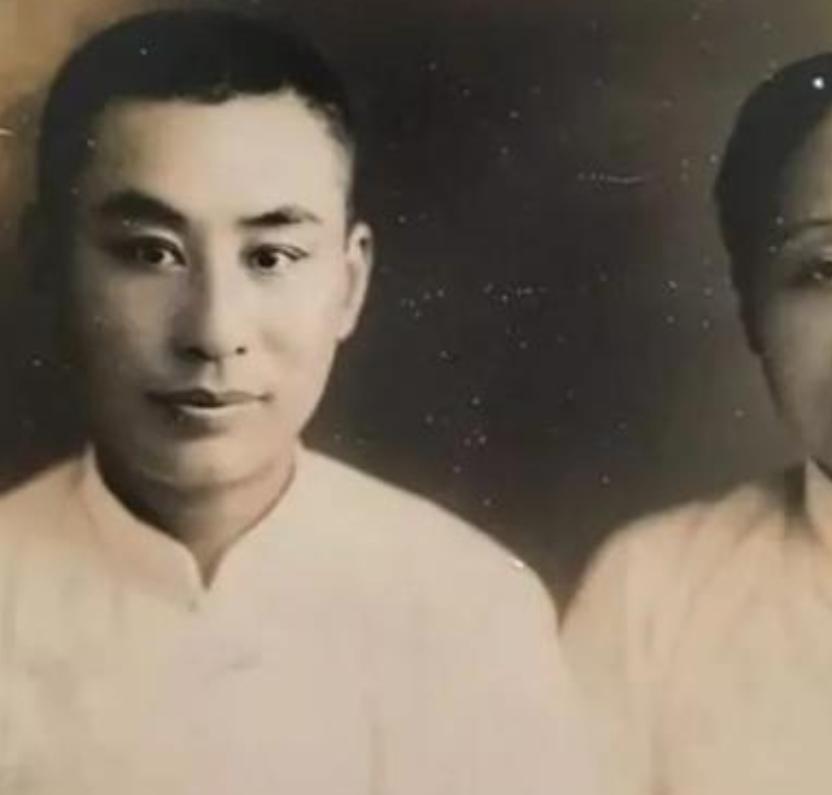[下雨]1916年,叶圣陶迎娶了未曾谋面的妻子。洞房夜,两人第一次见面。他用颤抖的手,掀开了新娘的盖头。看到眼前的一幕,他的心忍不住砰砰跳… 1916年冬天,二十七岁的教书先生叶圣陶站在贴着喜字的房门前,手心里攥着汗——按老规矩娶的新媳妇连面都没见过,新娘子盖头下到底是个啥模样? 胡家姑娘胡墨林命苦,打小没了爹娘,跟着开药铺的姑姑胡铮子长大。 这胡家姑姑是个明白人,自家开着"胡氏女学",愣是把侄女教得能写会算,在苏州城里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新派姑娘。 眼瞅着侄女到了该出嫁的年岁,胡姑姑到处给物色人家——既要门当户对,又得是读过新式学堂的后生。 那年春天在亲戚的婚礼上,胡姑姑遇见了穿着青布长衫的叶圣陶。 这后生虽说生在书香门第,倒没有酸腐气,说起国文教学眼睛发亮。 胡姑姑暗地里打听,听说这人在苏州当小学教员,月俸八块大洋,跟自家侄女倒是般配。 两家换了生辰八字,叶圣陶收到张泛黄的照片:齐耳短发的姑娘坐在藤椅上,膝头摊着本书。那年中秋节刚过,叶家就抬着花轿把新娘子接进了门。 洞房夜红烛高照,叶圣陶掀盖头时手直哆嗦——新娘子比照片上还水灵,低眉顺眼地冲他笑,露出两个酒窝。 蜜月还没过完就遇上糟心事,胡墨林在南通的女子师范谋了教职,叶圣陶得留在苏州教书。 新婚夫妻头回分开那天,叶圣陶在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写:"墨儿不在,觉空落落。"这话后来成了他们三十多年书信往来的开头语。 往后的日子就像走马灯,叶圣陶先是被调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后来又带着家小搬到甪直镇。胡墨林挺着大肚子跟着搬家,路上还得哄着哭闹的老大。 等抗战炮声一响,全家更是像断了线的风筝——叶圣陶在成都华西大学教国文,听说老婆孩子困在乐山,连夜雇了辆破马车往山里赶。 路上遇见日本飞机扫射,车把式吓得钻了山沟,叶圣陶愣是徒步走了二十里地,半夜三更敲开亲戚家门,看见老婆孩子睡在稻草堆上,这才一屁股坐地上。 1949年北京城解放那年,叶圣陶当上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胡墨林也没闲着,在社里当校对科长,两口子天天一块儿上下班。 出版社的老门房还记得,胡科长总拎着个竹壳暖瓶,晌午给叶社长送饺子——叶社长胃不好,吃不得食堂的硬米饭。 好日子过了没几年,胡墨林查出了癌。协和医院的老专家直摇头,叶圣陶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稿子堆在病床边上校。 到最后那几个月,胡墨林疼得睡不着,叶圣陶就整宿念《倪焕之》的手稿给她听。那是他二十年前写的小说,里头教书先生的爱情故事,跟他们年轻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老伴走后,叶圣陶在卧室墙上钉了个相框。照片是结婚那年拍的,穿阴丹士林旗袍的胡墨林抱着襁褓里的儿子。 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来送稿子,常见老先生对着照片发呆。每年清明前夜,叶圣陶准在台历上画红圈——那是他独创的记时法子,每个圈代表老伴走后的又一年。 八十六岁那年冬天,叶圣陶躺在病床上嘱咐儿女:"我床底下樟木箱里,有三百二十七封信,都是你娘写的。 等我走了,记得把信搁在我棺材里。"小女儿翻出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头整整齐齐码着泛黄的信笺,最早那封的落款是"民国五年冬月初八"。 如今苏州甪直镇的老街上,叶圣陶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摆着本翻开的日记。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迹依然清晰:"墨逝世三十四年矣,昨夜又梦少年时,伊在南通寄来红叶两片,夹在教案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