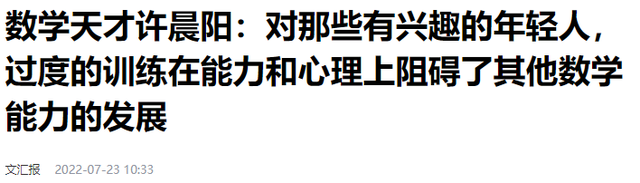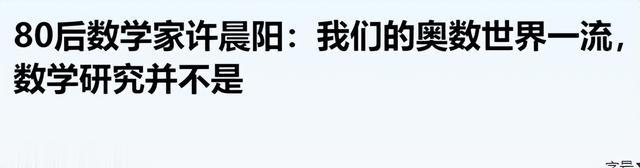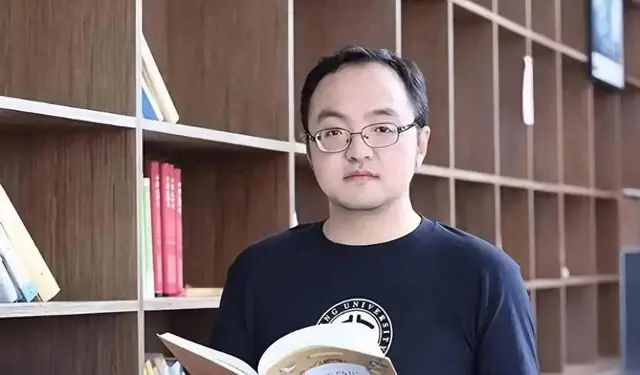
文|璧呈
编辑|娱叔
28 岁拒绝 MIT 终身教职、放弃 30 万年薪回国 “种树”的许晨阳,为何在 6 年后又重返美国实验室?
有人骂他“忘恩负义”,有人说他“用脚投票”。
引起众多争议的同时,他留下的三句“逆耳忠言”也让人深思。
更令人好奇的是,这位传奇数学家的背后究竟经历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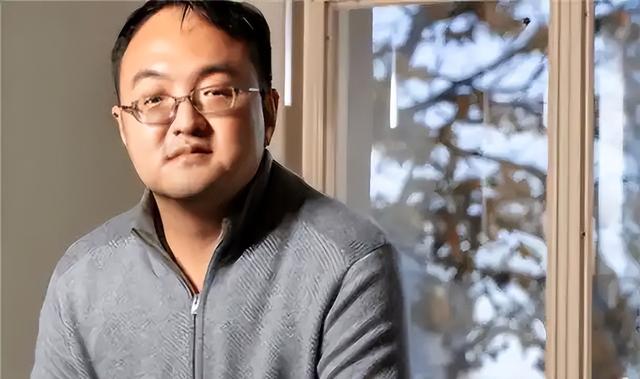 回国初心
回国初心2012年,28岁的许晨阳在普林斯顿已经是学术界新星。
MIT早早抛出终身教职橄榄枝,年薪30万美元,还有华尔街的高薪邀约。
但他却做了个“傻决定”。
卖掉美国房子,打包2000多本专业书,回到北大住筒子楼。

“中国代数几何落后欧美几十年,总得有人回来种树。”
他在入职演讲时的这句话,让台下老教授红了眼眶。
那时的他,穿着旧T恤在校园骑车,逢人就说“咱们要搞出世界一流的数学”,眼里全是光。

在北大,他干了三件“离经叛道”的事。
第一是每周开“挑刺会”,学生必须找出他论文里的漏洞,找不到就不算完成作业。
其次是他花了15万创办英文内刊,规定“不管教授还是学生,论文必须匿名评审”。
他还申请“几何与量子物理”交叉项目,想要打破传统数学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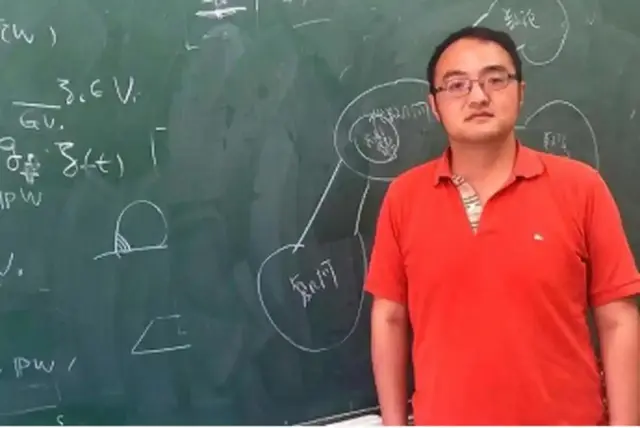
但现实很快泼来冷水。
办刊,被质疑“崇洋媚外”;
交叉项目,因为“偏离国家重点”被驳回;
甚至连邀请外国学者讲学,都要盖7个部门的章,等半年才能批下来。

带着 “种树”的热忱扎根燕园,许晨阳未曾想到,现实的土壤远比想象中贫瘠。
当 “挑刺会”“匿名评审 ”等创新尝试遭遇阻力,那些看似“ 离经叛道 ” 的改革,究竟触碰到了哪些深层积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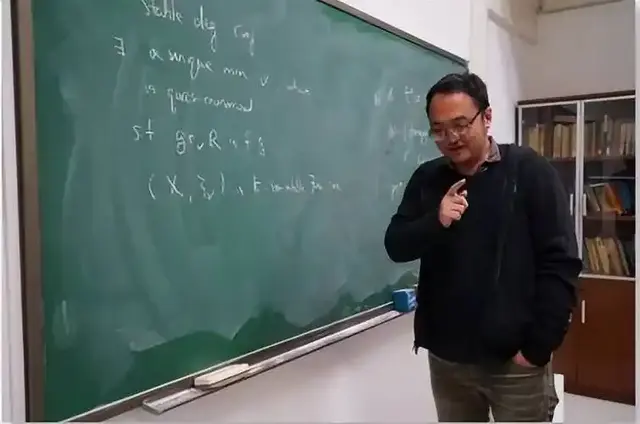 内心挣扎
内心挣扎在美国,他每年能拿230万美元经费,40%来自企业赞助,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回国三年,却只有120万国家基金,其中的70%还需买设备,剩下的钱连开国际会议都不够。
为了省钱,他带着学生用免费软件做模拟,自嘲“像从米其林餐厅回到路边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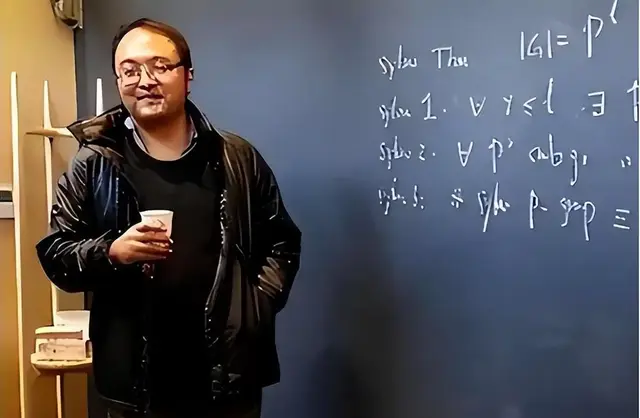
在 MIT,学生可随时打断教授论证并提出质疑,这种“挑战权威”的学术文化被视为创新动力。
而在北大,许晨阳的学生因公开指出某院士论文错误,被暗示“应注意学术礼仪”。
在MIT,他曾在咖啡厅偶遇计算机教授,聊了半小时就敲定合作项目。
可在北大,他想请哈佛教授来讲学,光填表就填了27页。

等5个月批下来时,人家签证都快过期了,最后只能线上聊45分钟。
学生们看着屏幕里的外国学者,小声说:
“要是在美国,许老师早和人家在实验室干起来了。”
还有一点,美国博士生可以同时选3个研究方向,导师只给建议。

可他带的学生王璐,只因想研究“数学+AI”,就被学院警告“跨学科风险大”,最后只能乖乖跟着做传统课题。
毕业时,王璐捧着论文叹气:
“这不是我想做的,只是最保险的选择。”
后来同事发现许晨阳变了。

以前每天最早来办公室,后来却经常一个人在走廊抽烟。
以前开会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很少开口。
学生指出权威错误,他当面表扬,背后却提醒“下次注意方式”。
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苦笑着说:“有些规矩,你不得不懂。”

当每周在走廊抽烟的次数越来越多,当 “有些规矩不得不懂”成为口头禅。
这位曾经眼里有光的学者,终于在学术环境的巨大落差中被迫做出选择。
2018年,无法继续忍耐的许晨阳向北大提出了离职,再次踏入了MIT的校园。
而他重返 MIT 后的 “如鱼得水”,恰恰成了一面刺痛人心的镜子。
 无奈转身
无奈转身熟悉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这一次,许晨阳的内心五味杂陈。
曾经离开时,他满怀壮志要改变国内代数几何的面貌。
六年后归来,他怀揣理想受挫的疲惫,却也坚守对纯粹学术环境的向往。
一回到MIT,他迅速重启被搁置许久的“朗兰兹纲领”研究。

让他惊喜的是,仅仅一周时间,硅谷企业赞助的500万美元专项基金就到账了。
这笔资金就像一场及时雨,让他能够毫无顾虑地购置先进设备、邀请顶尖学者合作。
他感慨道:
“在这里,只要你的研究有价值,资金就不是问题。”
跨学科合作的顺畅更是让他直呼“像换了个世界”。

与计算机系教授共同申请的“量子几何”项目,从提出想法到正式立项审批,仅仅用了15天。
回想起在北大时,申请一个项目要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耗时数月还不一定能成功,他不禁摇头苦笑。
学生们也发现,许晨阳又变回了那个充满激情的导师。
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醒目的便签:
“随时欢迎讨论,哪怕推翻我的假设。”

每周的研讨会上,他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自由表达观点,曾经在国内被压抑的学术氛围,在这里彻底被打破。
这番操作,让人不禁想起他当初留下的三句“争议性言论”:
论资排辈使年轻人晋升受阻;学术造假严重侵蚀公信力;过度功利化则背离研究初心。
这三句话犹如重锤,敲打着国内学术界的痛点。

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仍通过线上讲座持续指导国内学生,甚至将MIT的跨学科合作模式同步到北大。
他促成的“中美几何量子联合实验室”,让国内博士生首次实现跨国双导师制培养。
这些跨越太平洋的学术纽带,恰如他留在办公室的那张老照片。
2013年北大筒子楼里,他和学生们用草稿纸贴满墙壁推导公式,阳光正透过窗棂照亮“中国数学未来”六个粉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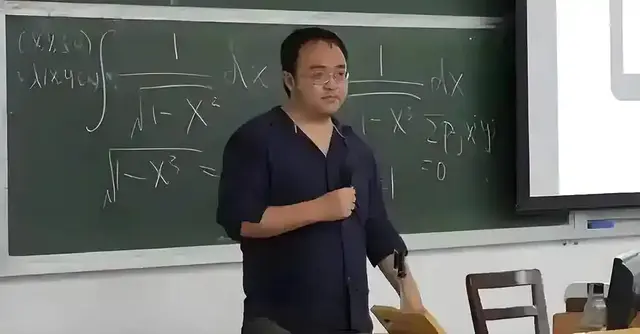
许晨阳的离去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国内学术生态的改革紧迫性。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国内也在积极求变。
“破五唯”政策的推行,让学术评价不再只看论文数量、奖项级别,更加注重研究的质量和实际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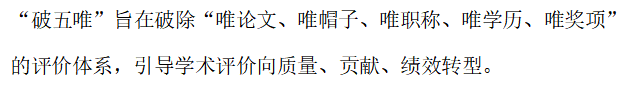
而“非共识项目”资助计划,为那些冷门但有潜力的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
这些改变鼓励着学者大胆创新,不必再因担心不符合主流观点而畏缩不前。

在学术交流方面,审批流程大幅简化。
国际会议的筹备时间从过去的半年缩短至20个工作日以内,越来越多的国际顶尖学者愿意来国内讲学、合作。
许晨阳的选择,不是不爱国,而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环境的诚实反馈。

当科研需要靠人情、创新需要看脸色、质疑需要顾面子,再强的理想主义也会被消磨。
而且,真正的学术强国也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
而是让每个“许晨阳”都能安心做研究、大胆提想法、自由追真理。
这一天来得越早,中国离世界学术中心,就越近。
 结语
结语许晨阳的选择,不是简单地“爱国”或“逐利”,而是一代学术人对 “纯粹治学” 的永恒追寻。
当我们惋惜“天才出走”时,更该思考:
如何让科研回归本真,让学者不必在“人情”与“真理”间艰难抉择?
毕竟,比起留住一个天才,更重要的是培育让千万个天才破土而出的沃土。
相信那时的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版图的中心。

部分参考资料:
文汇报|数学天才许晨阳:对那些有兴趣的年轻人,过度的训练在能力和心理上阻碍了其他数学能力的发展
澎湃新闻|80后数学家许晨阳:我们的奥数世界一流,数学研究并不是
澎湃新闻|许晨阳:加入麻省理工是去世界顶尖的地方看看,不代表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