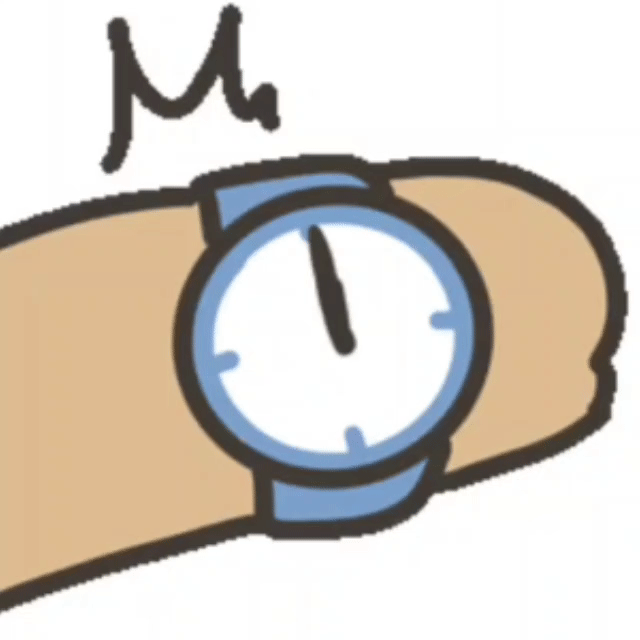日历一页页薄下去时,年味便从时光的褶皱里漫出来了。不是突然涌来的热闹,是像老灶上炖着的腊味,先有一缕若有若无的香,慢慢渗进屋子的每一寸,等反应过来,早已被那股暖烘烘的气息裹住了。

最先察觉的是母亲的手。她开始在阳台晾起一串串香肠,红亮的肉肠垂在阳光下,风一吹就晃,带着花椒与料酒的醇厚。我蹲在旁边看,她指尖还沾着肠衣的黏液,却笑着往我嘴里塞一块刚切好的腊肉:“今年的肉肥,熏出来香。”从前总嫌她忙活太早,如今才懂,她挂在阳台的不是香肠,是把日子里的零碎,一点点串成盼头。
后来,父亲会搬出自家腌的酸菜坛子。坛口揭开时“咕咚”一声,酸香混着坛子的陶土味扑出来。他戴着老花镜,把酸菜切成细丝,准备包过年的饺子。我帮他剥蒜,蒜皮落在瓷砖上,清脆的声响里,他忽然说:“你小时候总嫌酸菜饺子酸,现在倒会主动要了。”我一愣,才发现年味里藏着时光的刻度——原来那些曾觉得寻常的味道,早已跟着年岁,成了心里最软的牵挂。

街上的年味也悄悄浓起来。杂货店的门口堆起成箱的红纸,老板扯着嗓子喊“福字对联便宜卖”,路过的老人停下,眯着眼挑拣,手指抚过红纸,像在触摸旧年的记忆。小孩攥着大人的手,盯着路边卖糖画的摊子,转盘转起来时,他们的笑声比糖还甜。我站在路口看,忽然明白年味从不是什么盛大的仪式,是杂货店老板的吆喝,是糖画师傅手下的龙,是陌生人脸上都挂着的、心照不宣的温和。
最暖的是夜里。一家人围在客厅择菜,电视里放着老歌,母亲忽然说起我小时候过年的事:“你三岁那年,穿着新棉袄非要去雪地里跑,结果摔了一跤,哭着要吃糖葫芦。”父亲在旁补充:“后来我带你去买,你攥着糖葫芦,糖汁流到袖口都不管。”我听着,心里像被温水浸过,原来那些模糊的片段,都被家人好好存着,等过年时拿出来,就成了最珍贵的故事。

其实年味从未变淡,它只是换了模样。从前是盼着新衣服和压岁钱,如今是盼着一家人围坐的灯火;从前是好奇烟花如何绽放,如今是看着父母的白发,想多陪他们说说话。它藏在母亲晾晒的香肠里,藏在父亲切酸菜的刀刃上,藏在一家人闲聊的笑声中,一点点漫出来,把岁末的日子,染得格外暖。
当窗外的灯笼亮起来,我知道,又一年的年味,已经悄悄裹住了这个家。而那些关于团圆的期待,会像老灶上的腊味,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为心里最踏实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