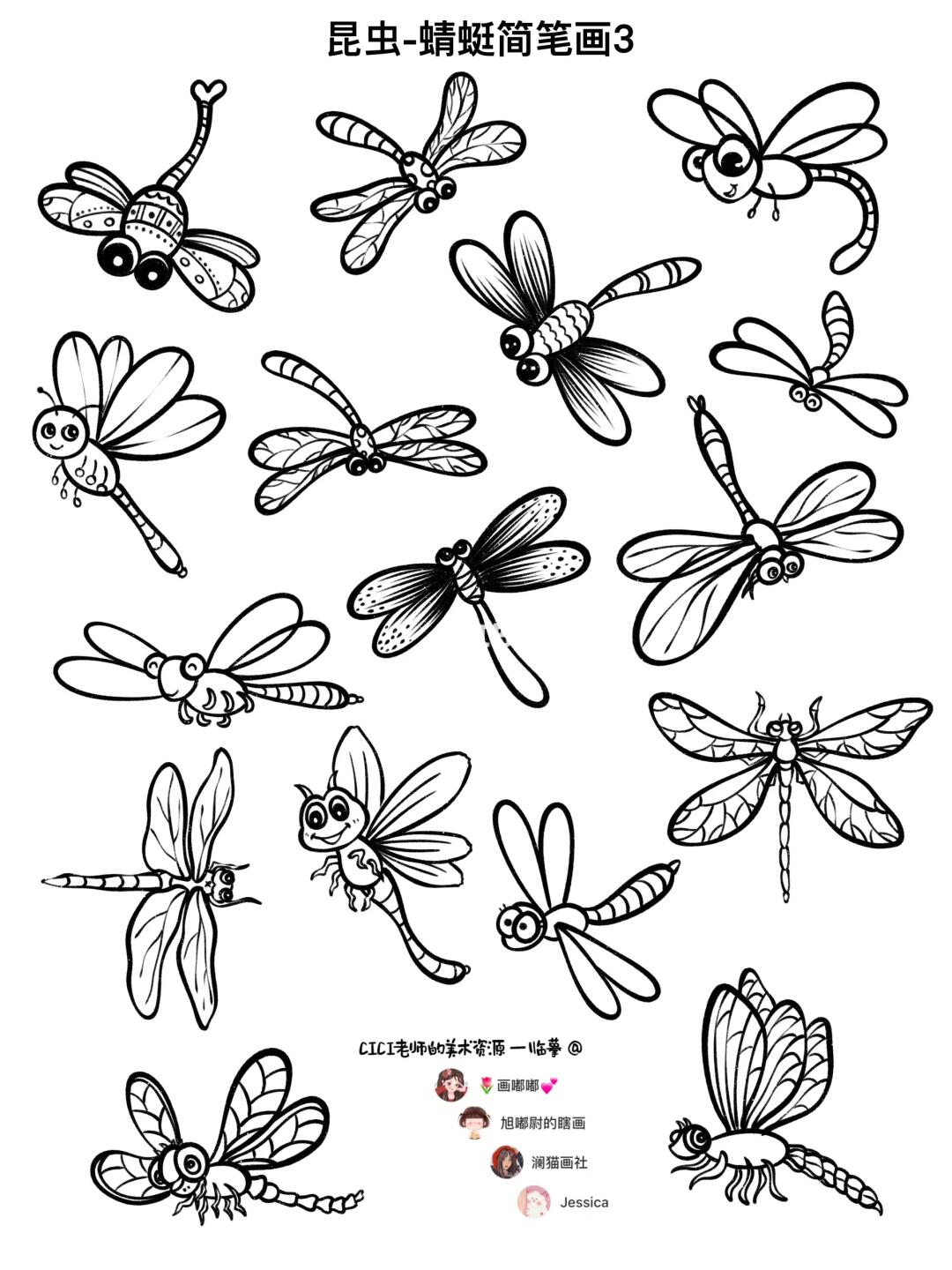资深老中医撑起药店口碑,年终仅得滞销维生素,新来的销售总监靠天价糖水 “神药” 拿五十万大奖,老中医离职后,老板带着重金跪求救命
......
01
腊月二十八,仁心堂的年终总结大会。
会议室里暖气开得足,但我却觉得骨头缝里透着寒气。
投影仪上红色的PPT刺眼,全是“业绩”、“转化率”、“爆品思维”。
李凯站在台上,头发抹得锃亮,像刚舔过油的碗底。
他手里挥舞着一张巨大的现金支票模型,上面写着:五十万。
台下掌声雷动,那些刚毕业的小姑娘手掌都拍红了。
李凯对着麦克风喊:“什么是销售?就是把梳子卖给和尚!就是把糖水卖成神仙水!”
老板陈志强坐在主位,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带头鼓掌。
“李总监就是我们要的狼性人才!仁心堂要上市,就得靠这股狠劲!”
李凯得意地晃着脑袋,眼神扫过角落里的我。
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堆即将被扫地出门的垃圾。
颁奖环节结束,陈志强似乎终于想起了我。
“哦,对了,还有咱们的镇店之宝,王老。”
全场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盯着我。
陈志强随手从桌子底下掏出一个落了灰的盒子,扔到我面前。
盒子滑过桌面,那是我们要处理的临期复合维生素。
“王老,今年大环境不好,中医科那边一直亏损。”
陈志强皮笑肉不笑,“这盒进口维生素,给您补补脑子,明年争取学会怎么开单。”
哄笑声瞬间炸开。
李凯笑得最响:“王老,这可是好东西,比你那些苦汤药值钱多了。”
我看着那盒维生素,生产日期是两年前的。
又看了看李凯手里所谓的“神药”——那其实就是兑了色素的糖水,一瓶卖398。
我坐堂三十年,这双手摸过几万人的脉搏,救过的人能站满这条街。
现在,我的尊严就值一盒快过期的维生素。
心里没有愤怒,真的。
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像是看着自家养大的孩子突然变成了畜生。
陈志强清了清嗓子,宣布重磅消息:
“明年开始,缩减中医诊室面积,改成保健品体验区。”
“至于王老嘛……”他看了我一眼,“底薪降一半,以后主要负责给VIP客户端茶倒水,讲讲养生故事。”
这是要逼我走。
还要把我的老脸踩在地上,给那个李凯垫脚。
我慢慢站起身。
满屋子的笑声像刀子一样刮在耳膜上。
我没拿那盒维生素,把它推回陈志强面前。
“陈总,这药留着你自己吃吧。”
我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全场闭嘴。
“我看你印堂发黑,气血两虚,确实需要补补脑子。”
陈志强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我没理会他的表情,转身就走。
李凯在身后阴阳怪气:“哟,王老这是嫌少?要不我私人赞助你两百块买烟抽?”
他说着真的掏出两张红票子,揉成团扔过来。
纸团砸在我背上,轻飘飘的。
我停下脚步,慢慢回过头。
盯着李凯的眼睛,足足看了三秒。
那眼神里没有怒火,只有一种看死人的怜悯。
李凯被我看得发毛,往后缩了缩:“你……你那是什么眼神?”
“积点德吧。”
我淡淡地说,“钱赚多了不仅烫手,还索命。”
说完,我推开会议室大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里面传来陈志强的咆哮:“老不死的!有种别回来!”
02
回到家,屋里没开灯。
儿媳妇刘梅坐在餐桌边,计算器的按键声在黑暗里显得格外刺耳。
“哒哒哒,归零。”
听见开门声,她猛地回头,眼里闪着狼一样的光。
“爸,回来了?发了多少?”
她快步走过来,甚至没顾上给我拿拖鞋。
“鹏鹏下学期的补习费要两万,还有房贷,这月压力太大了。”
她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看,想找装钱的信封。
我换好鞋,把那个用了十年的保温杯放在桌上。
“没发钱。”
空气凝固了。
刘梅愣了三秒,脸上的笑容像受潮的墙皮一样剥落。
“没发?怎么可能?”
她的声音尖利起来,“隔壁康得大药房那个老张,技术比你差远了,人家年终奖都拿了八万!”
“爸,你是不是又把钱藏起来了?”
我疲惫地坐到沙发上:“今年没效益,老板给了一盒维生素,我没要。”
“维生素?!”
刘梅尖叫一声,抓起桌上的抹布狠狠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在狭窄的客厅里回荡。
儿子王强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拿着锅铲,一脸唯唯诺诺。
“梅梅,你别这样,爸也不容易……”
“你闭嘴!就是因为你们父子俩都这副窝囊样,咱们家才一直被人看不起!”
刘梅指着我的鼻子,手指头都在哆嗦。
“爸,您清高,您了不起!”
“您给穷人看病不收挂号费,给老太太开药只开几块钱的。”
“名声是好听了,可能当饭吃吗?能给鹏鹏交学费吗?”
“那个李凯我都听说了,人家一年赚上百万!您呢?”
“坐堂三十年,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
我并不是没赚过钱。
早些年,这套房子,还有儿子结婚的彩礼,都是我一针一针挣出来的。
只是这几年世道变了,人心浮躁,没人愿意喝苦药汤子了。
我也想赚钱,但我不能为了钱,把良心喂狗。
王强给我倒了杯水,刚递过来。
刘梅一把抢过去,连水带杯子砸在地上。
玻璃炸裂,滚烫的水溅了一地。
“喝什么水!去跟你们老板闹啊!去要钱啊!”
“他是资本家,剥削你三十年,你就要个说法怎么了?”
我看着满地的碎玻璃,心里的最后一点热乎气也没了。
“没用。”我平静地说,“在他们眼里,良心不值钱。”
“那就别怪我不养你老!”
刘梅哭着冲进卧室,狠狠摔上门。
门框上的灰都被震落了几层。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儿子蹲在地上收拾碎片,不敢看我。
我抬起头,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块匾额——“悬壶济世”。
那是师父临终前传给我的。
师父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做医生,心要正。
我一直守着这句话。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陈志强发来的微信。
“王老,考虑到你有困难,公司决定不开除你。”
“但是明年你的诊费要降到5块,主要负责给店里引流。”
“李总说了,只要把老头老太太哄进来,剩下的交给他。”
看着屏幕上的字,我仿佛看到了陈志强和李凯那副得意的嘴脸。
5块钱。
引流。
把我当成了菜市场上招揽生意的烂白菜。
我关掉手机,站起身,走进书房。
书桌上压着一张药方,红纸黑字。
那是陈志强老婆偏头痛的老毛病,看了无数专家都没好,只有我的方子管用。
这也是陈志强即使再嫌弃我,也不敢彻底赶我走的原因。
这张方子,我琢磨了五年,用药极险,但也极效。
我拿起那张纸。
“爸,你去求求陈总吧……”儿子在客厅里小声哀求。
我没理会,手指捏住纸角。
嘶——
红纸一分为二。
嘶——
再撕。
直到那张价值连城的独门秘方,变成了指甲盖大小的碎屑。
我把碎纸屑扔进垃圾桶。
碎屑像雪花一样落下,埋葬了我的三十年。
我拿出纸笔,铺开一张白纸。
只写了三个字:辞职信。
每一笔,都力透纸背,划破了纸张。
03
夜深了,我却睡不着。
闭上眼,脑子里全是三个月前的那个下午。
那天店里来了一位大爷,穿着朴素,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他一进门就捂着胸口,脸色潮红,呼哧带喘。
李凯像见了血的苍蝇一样扑上去。
“大爷,您这是血管堵了!得赶紧通啊!”
“我这有最新研发的‘通络神丹’,纳米技术,吃一颗就能疏通血管,两万一疗程。”
大爷疼得满头是汗,哆嗦着要掏存折。
我当时正在给人抓药,回头看了一眼。
只一眼,我魂都吓飞了。
大爷舌苔厚腻发黄,双目赤红,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气血逆乱。
那个所谓的“通络神丹”,里面全是活血化瘀的猛药,这时候吃下去,那就是爆血管的炸弹!
“住手!”
我扔下药秤冲过去,一把打掉大爷手里的药瓶。
“这药不能吃!吃了会死人的!”
李凯愣了一下,随即大怒:“王承安!你疯了?敢断我财路?”
我没理他,扶住大爷,掏出随身的银针。
“大爷,忍一下。”
我在他耳尖和十宣穴迅速放血。
几滴黑血挤出来,大爷长出了一口气,脸色肉眼可见地缓和下来。
“哎哟……这气顺了,顺了……”大爷瘫坐在椅子上。
这是一次典型的脑卒中前兆急救。
如果刚才吃了李凯的药,这大爷现在已经躺在太平间了。
救护车来把大爷接走后,李凯把我堵在角落里。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老东西,你知道那一单提成多少吗?五千!”
“那是一条命!”我吼回去。
“命?那是我的业绩!”
李凯啐了一口,“这老头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又没死在店里!”
这件事闹到了陈志强那里。
我以为老板至少会明白其中的利害。
结果陈志强坐在老板椅上,转着手里的核桃,冷冷地看着我。
“王老,你确实救了人。”
“但是,你让我们店损失了两万块营业额,还得罪了李总监。”
“这个月绩效全扣,写份检讨。”
那一刻,我看着挂在头顶的那块“仁心堂”牌匾,觉得无比讽刺。
仁心?
这店里早就烂透了,只剩下铜臭和血腥。
回忆到这里,我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那个陪伴我四十年的旧皮箱。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我的银针、脉枕,还有几本翻烂了的古医书。
白天那些李凯看不上的“破烂”,此刻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这是吃饭的家伙,也是救命的家伙。
我一件一件把它们擦拭干净,装进那个不起眼的蛇皮袋里。
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店里,它们是垃圾。
但在某些人命关天的时刻,它们比金子还重。
收拾完东西,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把蛇皮袋放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刘梅还在卧室里睡觉,梦里也许还在数落我。
我没打招呼,提着袋子,推门而出。
早春的风带着寒意,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但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哪怕去摆地摊,哪怕去乡下种地。
我不伺候了。
04
虽然辞了职,但有些场面不得不应付。
大年初二,全家要去亲家那边拜年。
刘梅一路上都在警告我:“待会儿嘴巴甜点,别摆你那臭架子。今天我有几个有钱的亲戚要来。”
到了酒店包厢,一推门,我就看见了一个不想见的人。
李凯。
他穿着一身名牌西装,正坐在主位上,旁边围着一圈人给他点烟。
原来他是我亲家的远房表侄。
世界真小,小得让人恶心。
“哎呀,李总真是年轻有为啊,听说那个什么神药卖疯了?”亲家母笑得一脸褶子。
“小意思,一个月也就百来万业绩吧。”李凯喷出一口烟圈,眼神飘到了我身上。
他故作惊讶地站起来:“哟,这不是我们店的吉祥物王老吗?”
全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李凯走过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用力拍了拍。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店那个不开单、光领工资的老中医。”
“每个月就开点几块钱的草药,连电费都不够付。”
“也就是陈总心善,养个闲人。”
哄笑声再次响起。
亲家母嫌弃地看了我一眼,转头对刘梅说:“梅梅啊,你公公这也太不争气了。看看人家李总,再看看他。”
刘梅的脸红成了猪肝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在说:都是你让我丢人。
我默默找了个角落坐下,没说话。
菜过五味,李凯喝高了。
他端着满满一杯白酒,摇摇晃晃走到我面前。
“王老,来,我敬你一杯。”
他的酒气喷在我脸上,“听说你辞职了?太好了!”
“早就该滚蛋了,你在店里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这一杯,祝你早点进棺材,别浪费空气!”
全场死寂。
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看我这个“窝囊废”怎么把这杯羞辱酒喝下去。
刘梅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示意我赶紧喝了息事宁人。
我看着李凯那张扭曲的脸, slowly 站了起来。
我接过酒杯。
李凯得意地笑了:“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
哗啦!
我手腕一抖,满满一杯高度白酒,直接泼在了李凯的脸上。
酒水顺着他的发胶往下流,辣得他眼睛睁不开,哇哇乱叫。
“啊!我的眼睛!老东西你敢泼我?!”
全场惊呼,有人站起来要冲过来。
我把酒杯重重地墩在桌子上。
“啪!”
一声脆响,震住了所有人。
“这杯酒,祭奠仁心堂的未来。”
我冷冷地看着狼狈不堪的李凯。
“另外,告诉你那个老板。”
“人在做,天在看。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陈志强打来的。
估计是想问我库房钥匙在哪,或者是那个偏头痛的方子。
我拿出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按下了挂断键。
然后,拉黑。
动作行云流水。
我提起脚边的蛇皮袋,转身向外走去。
身后传来李凯歇斯底里的咒骂和刘梅的哭喊声。
“王承安!你疯了!你以后别进这个家门!”
我停下脚步,背对着他们说:
“这个家,我本来就不想回了。”
推开包厢门,外面喧嚣的世界扑面而来。
但我听到的,只有自己坚定的脚步声。
虽千万人,吾往矣。
05
年初八,我回店里办最后的手续。
刚进门,就发现我的诊室没了。
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
原本挂着“妙手回春”锦旗的墙壁,现在贴着一张巨大的海报。
海报上印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外,写着“纳米量子波,包治百病”。
我的办公桌被扔在走廊的过道里,像一堆没人要的垃圾。
上面还堆着几个装修工人的盒饭盒子,油汤流了一桌子。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
那张桌子,我用了三十年,上面每一道纹路我都熟悉。
李凯正指挥着工人在挂灯箱,看到我,鼻子里哼了一声。
“哟,来收破烂啊?”
他眼睛还肿着,是被酒辣的。
我也懒得理他,径直走到过道,开始收拾我的东西。
除了之前的银针和医书,桌肚里还有个小本子。
上面记着几百个老病号的联系方式和病历。
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刚把本子揣进怀里,一只手突然伸过来,一把按住了我的包。
是李凯。
“慢着。”
他歪着嘴笑,“公司规定,离职员工带走的东西必须检查,防止泄露商业机密。”
“让开。”我冷冷地说。
“不让怎么着?还要泼我?”
李凯给旁边的保安使了个眼色。两个保安围了上来。
李凯一把抢过我的蛇皮袋,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了地上。
哗啦啦——
银针包散开了,几百根银针撒了一地。
那几本泛黄的医书也摔在地上,书页折了角。
“哈!我就说是个收破烂的!”
李凯用脚尖踢了踢那一地银针,“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扎死人的玩意儿?”
“这些破铜烂铁,送给收废品的都没人要。”
他一边说,一边故意用锃亮的皮鞋在那本《黄帝内经》上碾了碾。
留下一个灰扑扑的脚印。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可以忍受他侮辱我,但不能忍受他侮辱中医。
我猛地推开保安,冲过去一把推开李凯。
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捡起那本书,拍掉上面的灰尘。
然后一根一根,把银针捡起来。
我的动作很慢,很仔细。
周围看热闹的店员都在指指点点,但我仿佛听不见。
捡完最后一根针,我站起身,把针包紧紧贴在胸口。
“李凯,你记住。”
我看着他的眼睛,字字千钧。
“这些不是破铜烂铁,这是救命的东西。”
“总有一天,你会跪在地上求这几根针。”
李凯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求你?我要是求你,我管你叫爹!”
“行,我等着。”
HR这时走过来,一脸不耐烦地扔给我一张离职单。
“赶紧签了走人,别影响我们做生意。”
我签下名字,那笔划像是刻在纸上。
没有欢送会,没有告别。
只有那个平时我经常帮她看腰疼的保洁阿姨,偷偷在门口塞给我两个苹果。
“王老,您保重啊。”阿姨眼圈红红的。
我接过苹果,笑了笑。
走出仁心堂的大门,阳光正好刺眼。
陈志强的迈巴赫停在门口,他正陪着几个穿金戴银的富婆看货。
看到我背着蛇皮袋出来,他假惺惺地喊了一句:
“王老,以后常回来看看啊,买药给你打九折!”
富婆们发出刺耳的笑声。
我头也没回,挺直了脊梁,走入茫茫人海。
这一刻,我不是丧家之犬。
我是入海的蛟龙,终将腾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