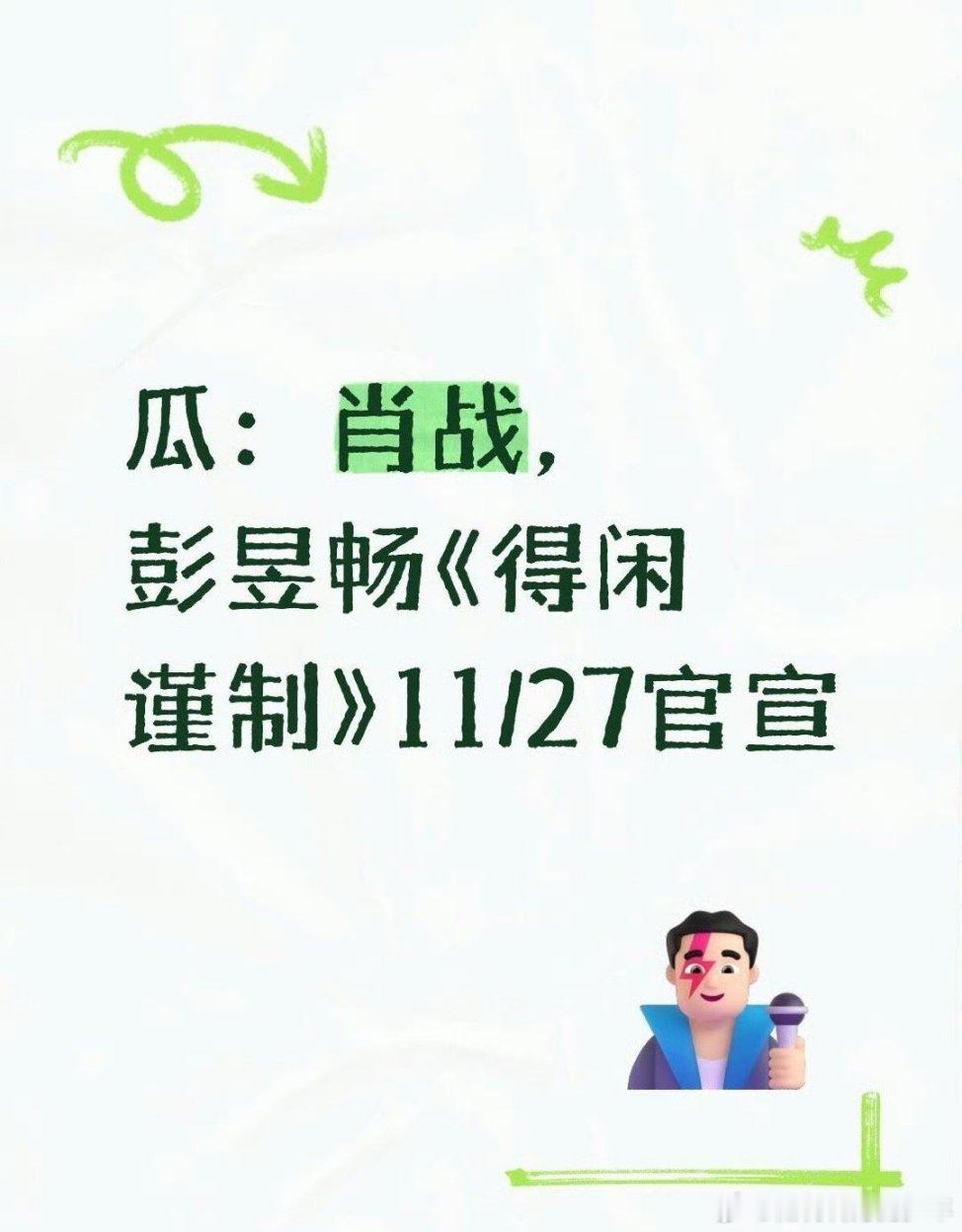叔叔年轻时,婶婶跟别人跑了,丢下了叔叔一个人,后来经人介绍,和现在的婶子结婚了。婶子长的一般,腿有残疾,走路一米六一米七,还经常吃药,啥体力活也干不了,我们都没看好这桩婚事,就叔叔自己同意。 当时爷爷奶奶气得好几天没理叔叔。爷爷蹲在门口抽旱烟,烟杆敲着石阶 “咚咚” 响:“你是不是疯了?前一个跑了,你还找个这样的,以后家里的活谁干?你要累死自己?” 奶奶坐在炕头抹眼泪:“我苦命的儿啊,怎么就遇不到个好的?她连自己都顾不住,怎么跟你过日子?” 亲戚们也跟着劝。 叔叔年轻那会儿,头一个婶子跟人跑了,留下他守着三间土坯房,灶台上的锅都生了锈。 后来媒人领着现在的婶子上门,我们瞅着都犯嘀咕——她左眼眉梢有道月牙形的疤,左腿比右腿短半截,走一步身子就往左边歪一下,像被风吹得晃悠的麦子。 不光腿脚不利索,兜里还总揣着药瓶,一天三顿药片掰着吃,地里的活扛不动锄头,灶台上连满桶水都提不起。 爷爷奶奶气得好几天没给叔叔好脸色。 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杆敲着青石板“咚咚”响,烟灰掉了一衣襟:“前一个跑了,你还找个这样的?是嫌日子不够糟心?” 奶奶坐在炕沿抹眼泪,手里的帕子拧得能出水:“她自己都顾不住,以后谁给你缝补浆洗?” 叔叔蹲在灶台边烧火,柴火“噼啪”响,他往灶膛里添了根柴:“我愿意。” 就这三个字,把全家人都噎得说不出话。 婚结得简单,没办酒席,婶子自己拎着个旧木箱,一步一晃地进了院门,箱角还磕掉了块漆。 我们都以为这日子过不长——叔叔白天去镇上工地搬砖,晚上回来还得自己做饭,婶子顶多坐在门口喊句“慢着点”。 可过了半年去串门,我竟看见灶台上温着粥,碗筷摆得整整齐齐,叔叔那件磨破袖口的蓝布褂子,袖口上补了块方方正正的补丁,针脚比新买的还密。 婶子坐在小板凳上,正拿顶针纳鞋底,左腿伸直搭在另一个板凳上,线头在嘴里抿湿了,穿过针眼时手都不抖。 “你婶子说,我白天干活累,回来得吃口热乎的。”叔叔蹲在门口削土豆,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手里的土豆皮削得薄如蝉翼。 后来才知道,婶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扶着墙挪到灶台,用小锅一点点煮粥,怕火大了糊底,就拿个小板凳坐着,守在灶边拿勺子搅,一搅就是半个钟头。 叔叔的袜子总磨脚趾头,婶子就把自己嫁妆里的旧毛衣拆了,纺成线织成厚厚的袜头,缝在袜子上,穿两年都不破。 有回叔叔在工地摔了腿,躺了半个月。 婶子每天挪着步子去村口井边打水,一桶水得分三次提回家,胳膊上勒出红印子,晚上给叔叔擦身时,疼得倒抽冷气也不吭声。 她跪在炕上给叔叔揉膝盖,左腿使不上劲就拿胳膊撑着,嘴里念叨:“慢点好,别着急,有我呢,你饿不着。” 我们这才明白,当初叔叔为啥非要娶她——前一个婶子长得好看,却把家里的粮食偷偷往娘家搬,叔叔发烧到说胡话,她还在跟人打麻将;现在这个婶子,腿不好,药不断,却把叔叔的日子当成自己的命来护,连他咳嗽一声都要追着问半天。 爷爷后来跟人说:“我那会儿只看见她的腿,没看见她的心,人心这东西,比啥都金贵。” 去年冬天我又去,见婶子正给叔叔织毛衣,毛线是叔叔用打工攒的钱买的,枣红色,婶子说叔叔穿这个显年轻。 叔叔坐在旁边剥花生,剥好的花生仁都堆到婶子手边上,堆成个小小的山尖:“慢点织,别累着眼睛,灯暗了就开大灯。” 婶子抬头笑,阳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在她歪着的肩膀上,倒像是给那半边身子镀了层暖融融的金边。 谁能想到呢?当年我们都觉得不般配的两个人,如今叔叔的白头发都比村里同龄人的少,婶子药罐子没离手,却把家里的日子过成了蜜罐子。 过日子啊,哪是看腿长腿短、能干不能干? 关键是两个人心里有没有彼此——你把我磨破的袖口补好,我把剥好的花生仁堆到你手边,就算走得慢一点,也能一步步挪到白头。 就像婶子纳的鞋底,针脚密密麻麻,看着普通,踩在脚下却比啥都稳当。
山美水美人也美
【2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