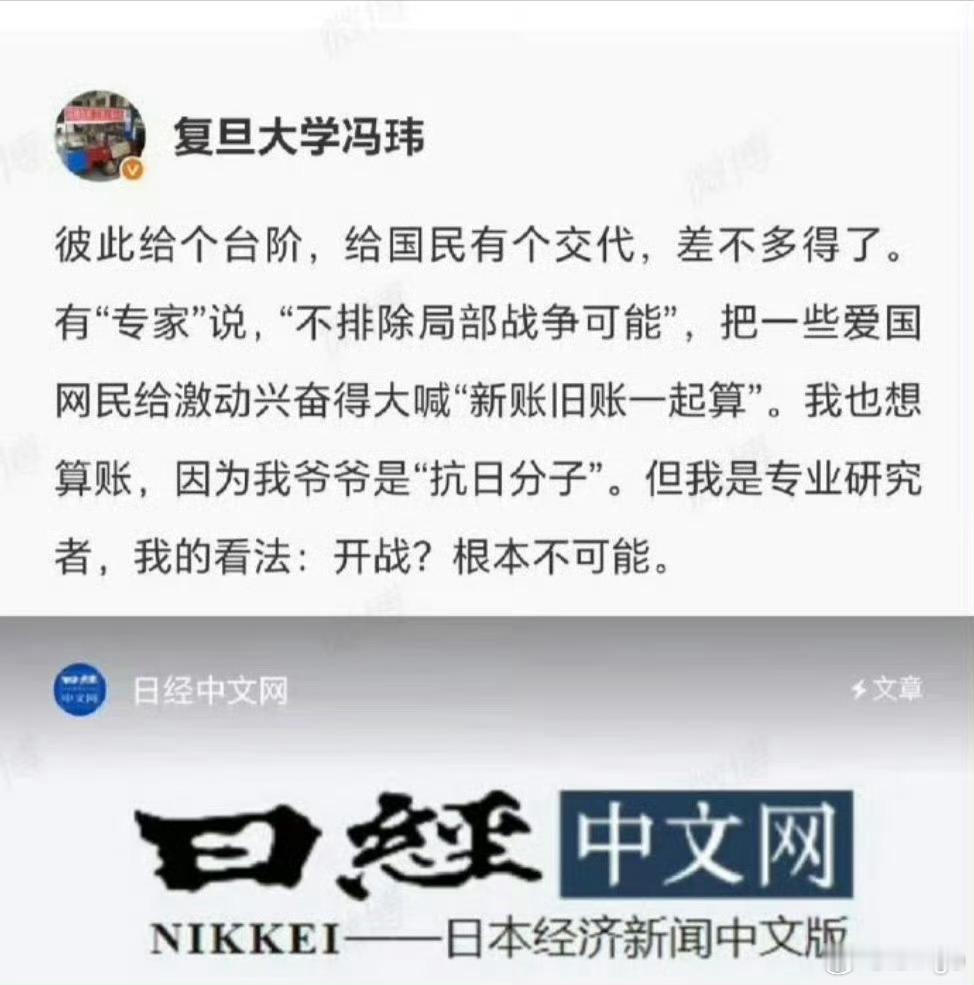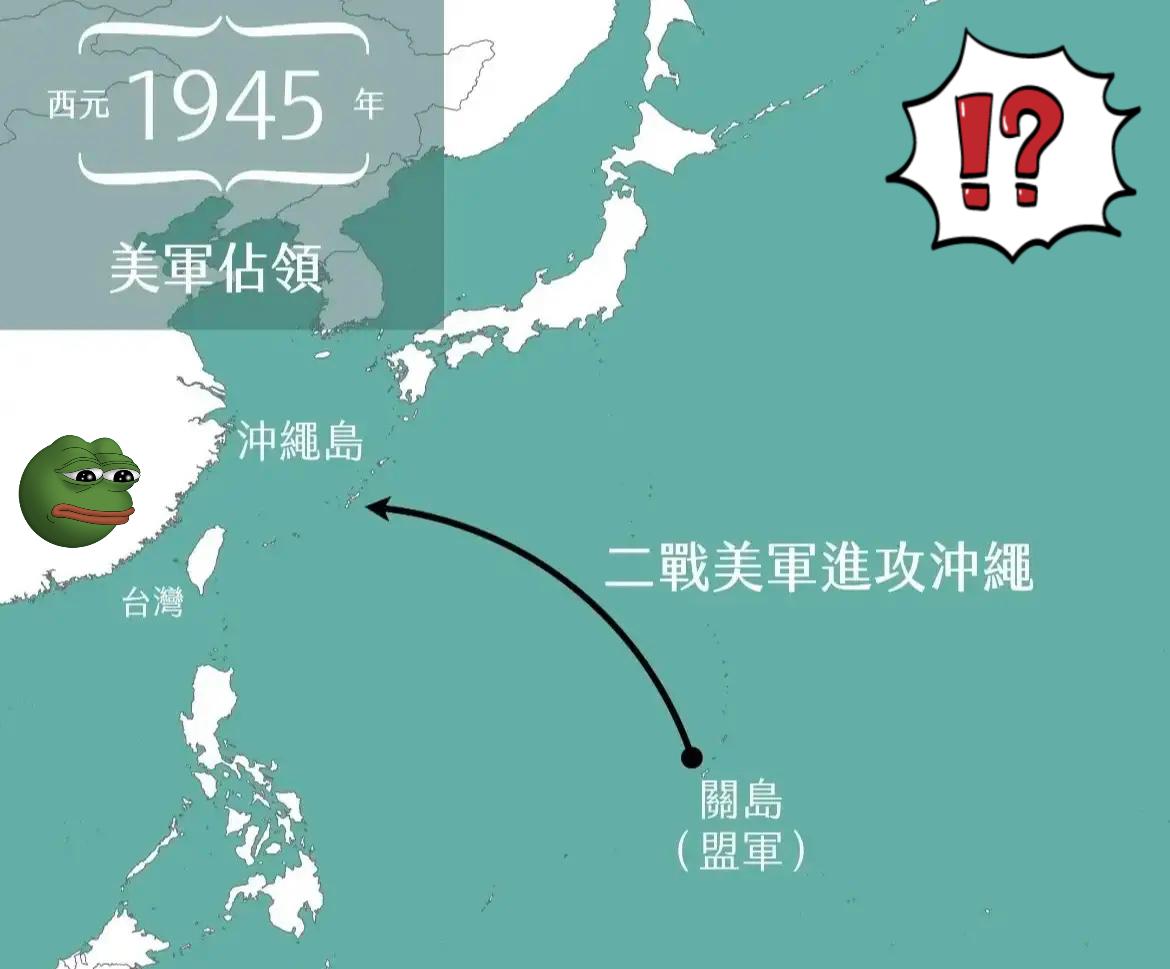1703年,权倾一时的索额图活活饿死在宗人府,其家人或被杀或流放。五年后,康熙还不解恨,将一顶“千古第一罪人”的帽子,扣在了索额图头上。昔日亲密无间的君臣,为何以这种方式落幕? 三年前,索额图就已经被排挤出核心权力圈。康熙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改设南书房与军机房。作为反对者之一,索额图一度上疏请求保留议政会议制度。 他的说法在当时并非无理,毕竟作为清初定制,该制度曾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但康熙此时的心思已不在贵族分权上,而是要彻底集中皇权。索额图这份奏章,被认为是阻挠变法,态度保守。康熙虽未明言责怪,却从此视其为“阻政之人”。 索额图之所以能获得康熙宠信,离不开“擒鳌拜”之功。1669年,鳌拜以辅政大臣身份独断专行,康熙虽已亲政,但鳌拜仍手握实权。索额图放弃吏部侍郎职位,转任内廷侍卫大臣,实际上是为擒拿鳌拜秘密布阵。 他亲自训练少年武士,埋伏于宫内,待鳌拜独入觐见时一举擒下。这场政变成功,使康熙权力彻底回到皇帝之手。索额图因此进入最核心的亲信圈。 但也是从此时起,索额图逐步养成独断作风。在“礼仪之争”中,他支持皇帝亲行斋戒,否决明珠等人依旧礼部代行的提议。这让朝堂两派日益分裂。索额图笼络一批汉臣,又与太子胤礽的关系日渐紧密。康熙初年曾信任胤礽,不仅幼年立为太子,还特意让索额图作为“舅祖”辅导他成长。 到了康熙三十年前后,索额图已经公开拥护胤礽,并与其亲信形成所谓“太子党”。他在朝中扶持的官员多是胤礽提名,且在处理奏折时经常绕过内阁,直接送呈皇帝或太子过目。更严重的是,他多次暗示太子可“提前准备登基”,这话传入康熙耳中,成为刺入骨髓的叛逆之言。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南巡归京,立即密令宗人府逮捕索额图,以“结党营私”“妄议储位”“图谋不轨”三罪定案。他的长子格尔芬、次子阿尔吉善被立斩,其余亲族全数流放宁古塔。康熙更下令:“宗人府不得供水食。”就这样,索额图被困于幽暗牢房,日夜饥渴,耗尽气力,慢慢饿死。 而索额图的“千古第一罪人”之称,是康熙在五年后亲自敕封于朝会之上。他说:“鳌拜之擒,固有其功,但终因狂悖误国,若不明正其罪,后世以何为鉴。” “宠之至极,弃之如草。”这是康熙帝对权臣最冷酷的态度,而索额图,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