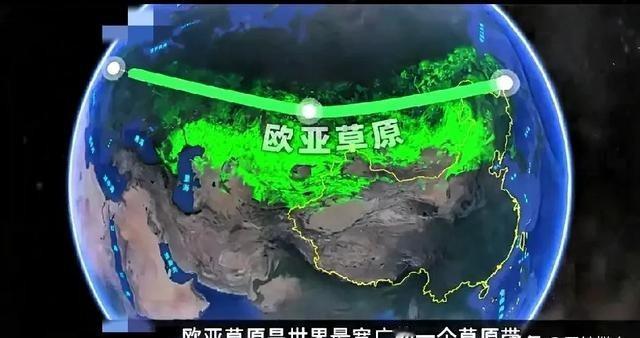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厉声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024 年国家博物馆 “正义之光” 展厅,灯光柔和地打在玻璃展柜上。 一件黑色法袍静静陈列,领口处的丝线虽褪色却依旧整齐。 游客们围着展柜,听讲解员念展签上的文字:“1946-1948 年东京审判物证。” 有人伸手轻触玻璃,仿佛想触碰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讲解员不知道,此刻游客注视的法袍,曾见证过震撼世界的博弈。 1946 年 5 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首日,座位排序引发争议。 梅汝璈看到中国法官席位被排至末尾,当即拒绝入座。 “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中国位列第二,席位必须调整!” 他据理力争。 最终法庭妥协,中国法官席位按国际惯例排到第二,这是他为国家争得的第一个尊严。 审判期间,面对日本战犯的狡辩,梅汝璈展现出扎实的法律功底。 他整理出南京大屠杀百余份证人证词,其中包括 12 名西方记者的记录。 将影像资料与文字证据串联,形成完整证据链,驳斥 “战争无罪行” 论调。 在东条英机否认侵略事实时,他当庭出示其签署的作战命令原件。 这份证据让战犯无从抵赖,也为后续判决奠定关键基础,这是他在法律层面的核心突破。 1948 年 11 月,审判进入最后量刑阶段,是否判处绞刑争议激烈。 部分法官认为 “绞刑过于严苛”,梅汝璈据理力争:“战犯的罪行远超绞刑。” 他列举南京大屠杀中 30 万平民遇害、731 部队活体实验等史实。 最终以 6 票赞成、5 票反对的微弱优势,推动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 7 人绞刑。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在国际法庭上主导对侵略国战犯的重罪判决,意义深远。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拒绝国民政府的高官任命,选择回国投身法治教育。 1949 年,国民党撤往台湾,家人劝他一同离开,他却选择留下。 “新中国需要法律建设,我不能走。” 他将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副本仔细珍藏。 此后数年,他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提出多项重要建议。 其中 “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被采纳,成为我国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 回溯至 1931 年,梅汝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后,毅然回国。 拒绝京城高薪职位,主动前往山西大学任教,开设《国际法》《刑法》课程。 他编写的《法学概论》教材,首次将西方先进法治理念与中国实际结合。 抗战期间,学校多次搬迁,他带着教材辗转南开、武大、复旦等地。 在重庆防空洞旁的临时课堂,他坚持授课,培养出数百名法律人才,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骨干。 1950 年,梅汝璈参与创建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 北京政法学院。 担任教授期间,他创新教学方法,组织学生模拟法庭,增强实践能力。 他常对学生说:“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是保护百姓的武器。” 在他的推动下,学院首次开设 “国际司法实践” 课程,填补国内空白。 这门课程后来成为政法类院校的核心课程,培养出大批国际法专业人才。 1966 年,特殊时期来临,梅汝璈的家被冲击,东京审判法袍险些被烧。 他死死抱住法袍:“这是中国讨回公道的证物,烧不得!” 同时将珍藏的审判判决书中文稿藏在地板下,避免被毁。 即便遭受批斗,他仍偷偷整理多年的法学研究笔记,不愿让成果流失。 这些笔记后来成为研究我国早期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料,部分内容被收录进《中国法治史》。 1973 年,梅汝璈因病逝世,临终前仍念叨着 “法律精神不能丢”。 他的家人遵照遗愿,将法袍、审判判决书副本等遗物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1988 年,我国首次举办 “东京审判史料展”,他的事迹开始被广泛传播。 2014 年,梅汝璈被追授 “中国法治建设杰出贡献者” 称号,以表彰其一生功绩。 如今,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那件法袍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 旁边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的发言录音,声音铿锵有力。 每年都有大批法律专业学生来此参观,感受前辈的正义坚守。 他参与起草的法律条文仍在守护着社会公平,他培养的学生多已成为法治领域的中坚力量。 现在,翻开《中国国际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建设史》等书籍, 梅汝璈的名字和事迹都占据重要篇幅,他的贡献被永久铭记。 那件黑色法袍所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法治精神的传承。 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维护正义、建设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 主要信源:(新华网——“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洞见与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