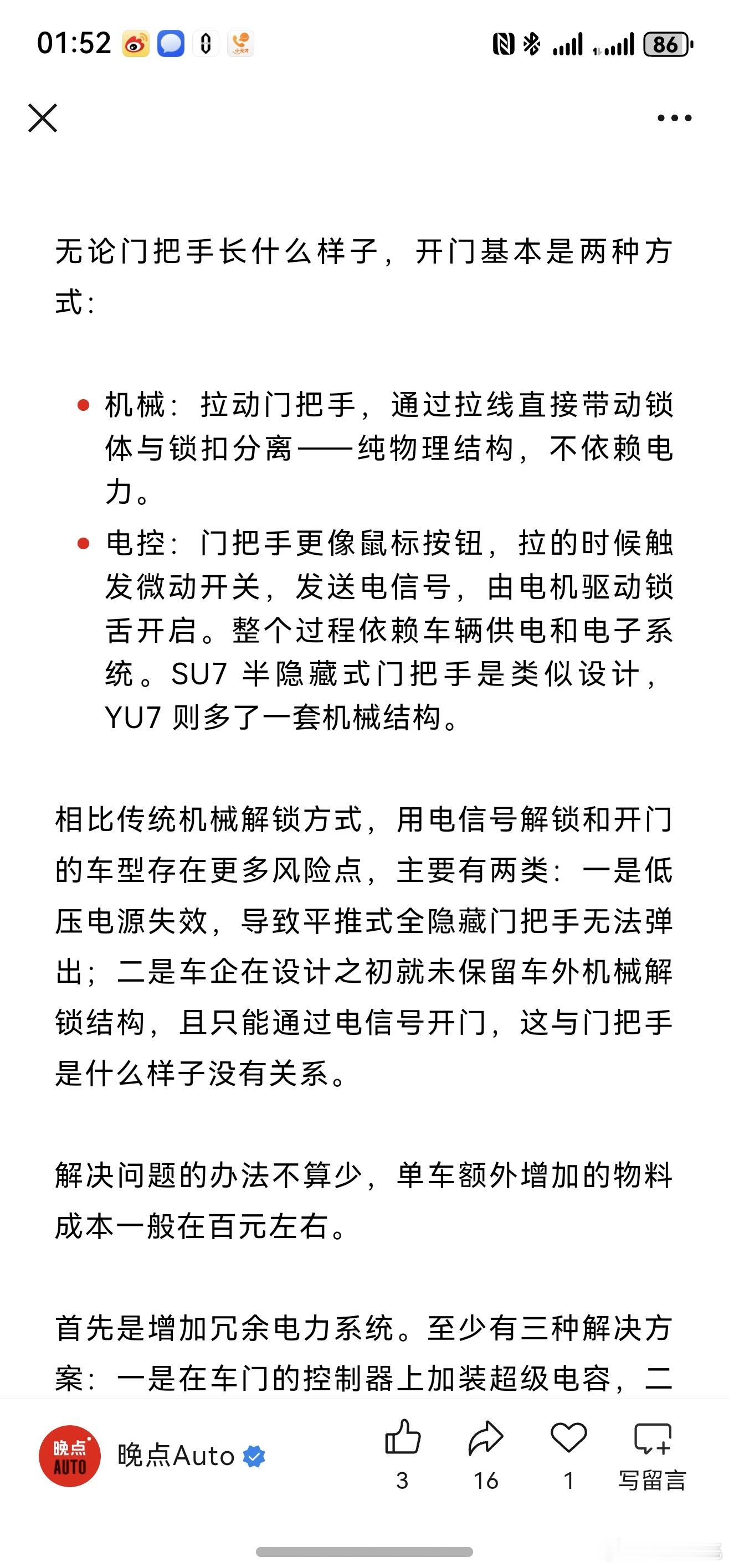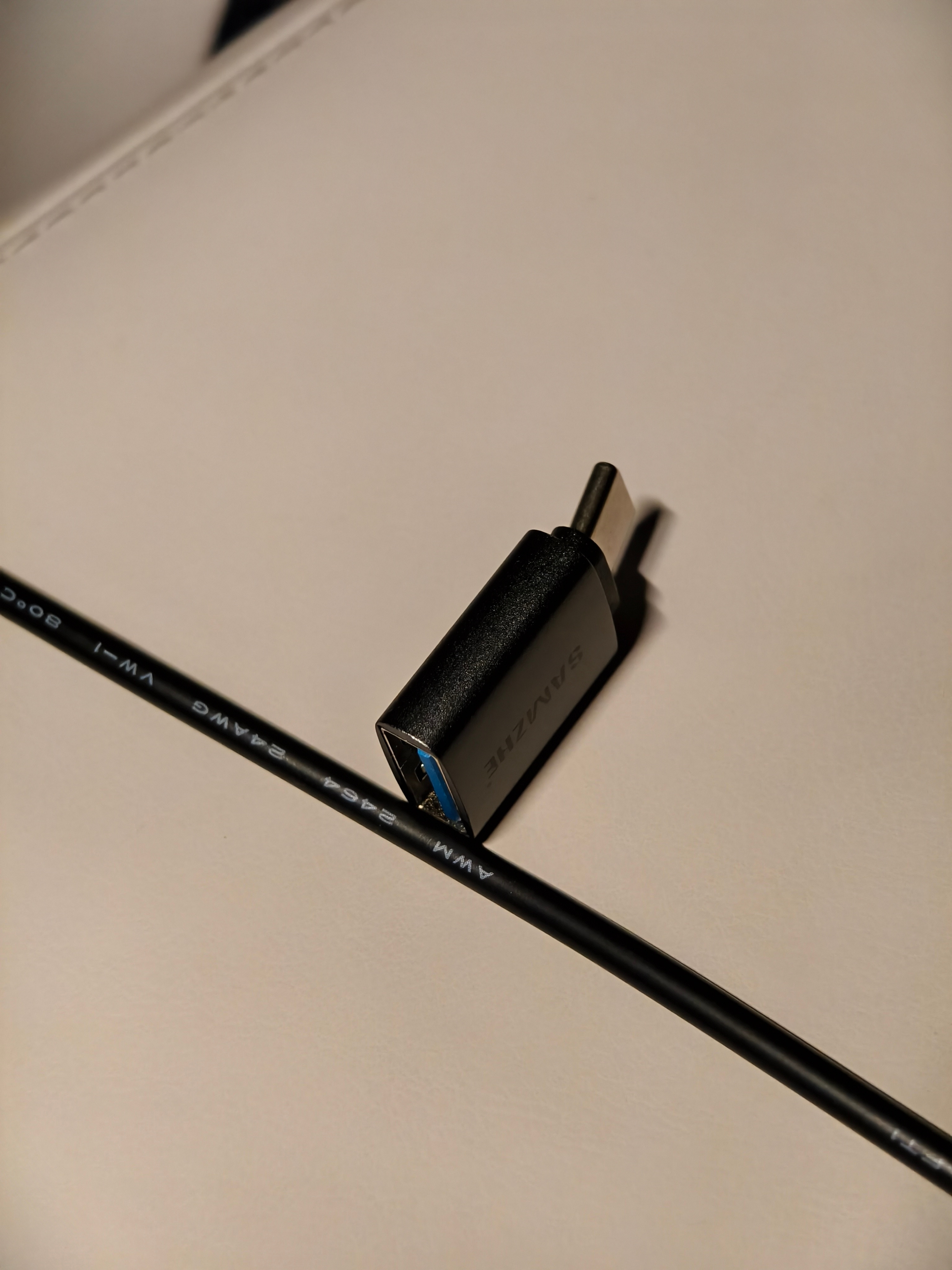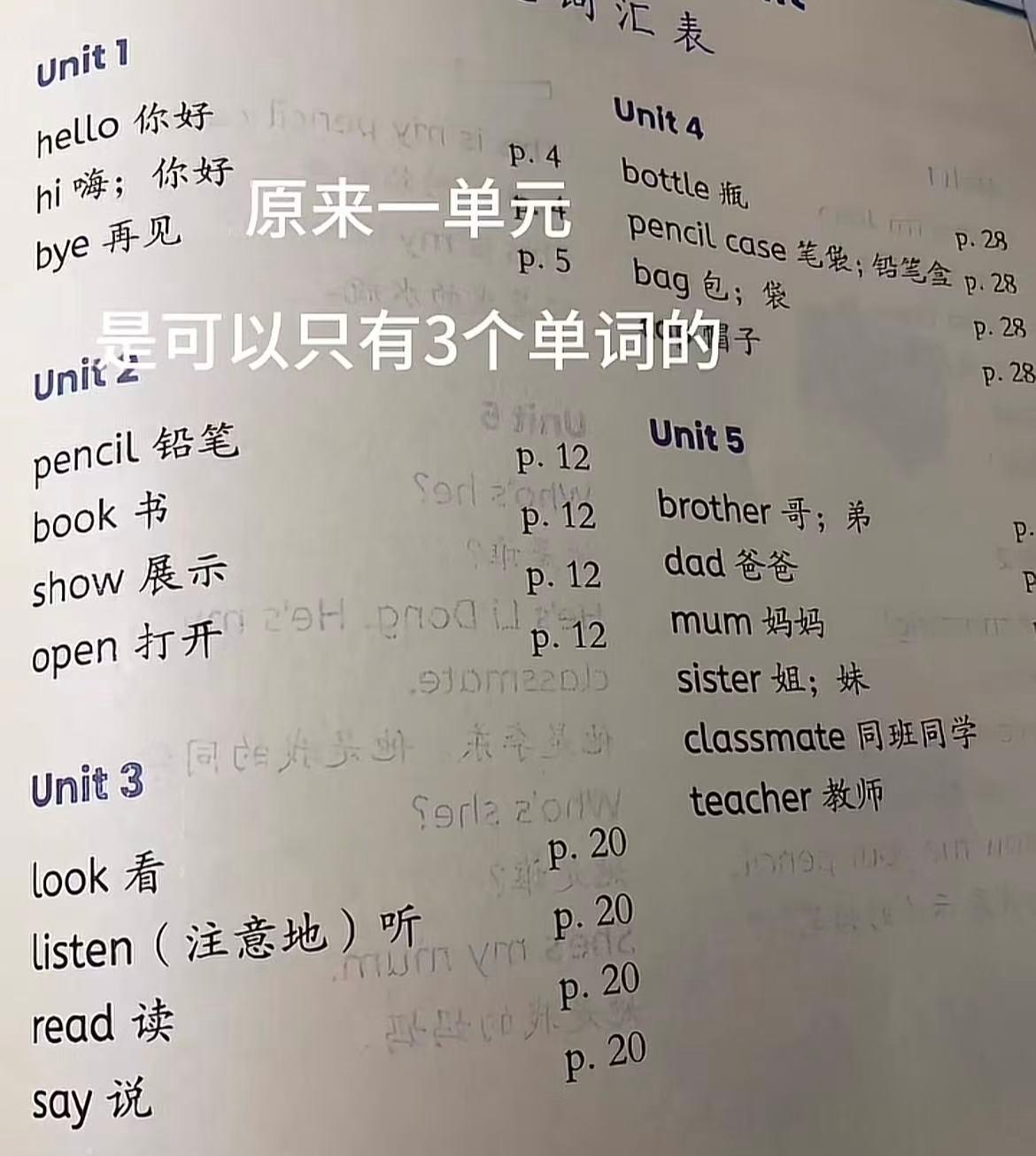十三岁的夏天没说出口的痛,凭什么要我用余生原谅? 下午三点的阳光本该暖得刚好,可微信语音里“妈妈”两个字跳出来时,我握着鼠标的手突然僵住——这个早就被我拉黑的号码,像附骨的蚊子,总在我以为安全的时候,猝不及防叮得人疼。 “淼淼,你姨病了,挺重的……”妈妈的声音裹着电流,软得像泡发的棉花,却往我心上压得慌。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设计稿,线条笔直,色块分明,这是我打拼多年才攒下的“秩序”——在这里,每一笔都由我掌控,没有意外,没有阴影。可“姨”这个字,偏像把生锈的钥匙,“咔嗒”一声,捅开了我以为早封死的那个房间。 房间里永远是十三岁的夏天,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后院烂在枝头的桃子散着酸腐味,混着姨夫喷蟑螂的杀虫剂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我记得那天姨妈说去巷口买酱油,让我在屋里等她。姨夫坐在沙发上,手指摩挲着一串钥匙,电视里演着喧闹的小品,他的眼神却没在屏幕上——那目光像黏糊糊的蛛网,缠在我身上,让我攥着衣角的手都在抖。 “怕什么?姨夫又不会吃了你。”他突然站起来,挡住了门,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我当时不懂的怪异。我想跑,脚却像灌了铅,直到他的手碰到我胳膊的那一刻,我才像疯了一样推开他,跌跌撞撞冲出门,凉鞋跑丢了一只都没敢回头。 我以为跑回家就安全了,哭着把事情告诉妈妈时,她却摸着我的头说:“小孩子别乱说话,你姨夫怎么会对你做那种事?是你想多了。”那一刻,我才知道,有些伤口不仅没人帮你包扎,还会被人说“是你自己矫情”。 从那以后,“姨妈家”成了我提都不敢提的禁地,夏天的桃子和杀虫剂味成了我的噩梦。我拼命学习,考去离家乡最远的大学,学设计时总爱画最直的线、最规整的图形——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觉得生活能被自己攥在手里,不会再突然冒出一个阴影,把我拽回那个夏天。 这些年,妈妈不是没劝过我“放下”,可她从来没问过我,那个十三岁的下午,我是怎么光着一只脚跑过整条街,怎么在夜里蒙着被子哭到喘不过气,怎么从此对所有男性长辈都保持着警惕。就像现在,她只说“她毕竟是你亲姨”,却没说过一句“当年是我们没保护好你”。 “我忙。”我把声音压得像设计稿上的线条,没有一丝温度。挂了语音,电脑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我盯着那些冷静的线条,突然鼻子一酸——我努力了这么多年,不过是想把那个夏天埋得深一点,可为什么总有人要把它挖出来,逼我“原谅”? 或许有人会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有些伤害不是时间能抹平的,就像一道疤,平时看着不显眼,一碰到还是会疼。我不想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可我也做不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笑着去看那个让我噩梦缠身的人。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是受害者,却总被人劝“大度”“放下”?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请求,会怎么选?评论区跟我说说吧,或许你的话,能给我一点力量。

![理解大人,成为大人[哭哭]](http://image.uczzd.cn/994123562056664233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