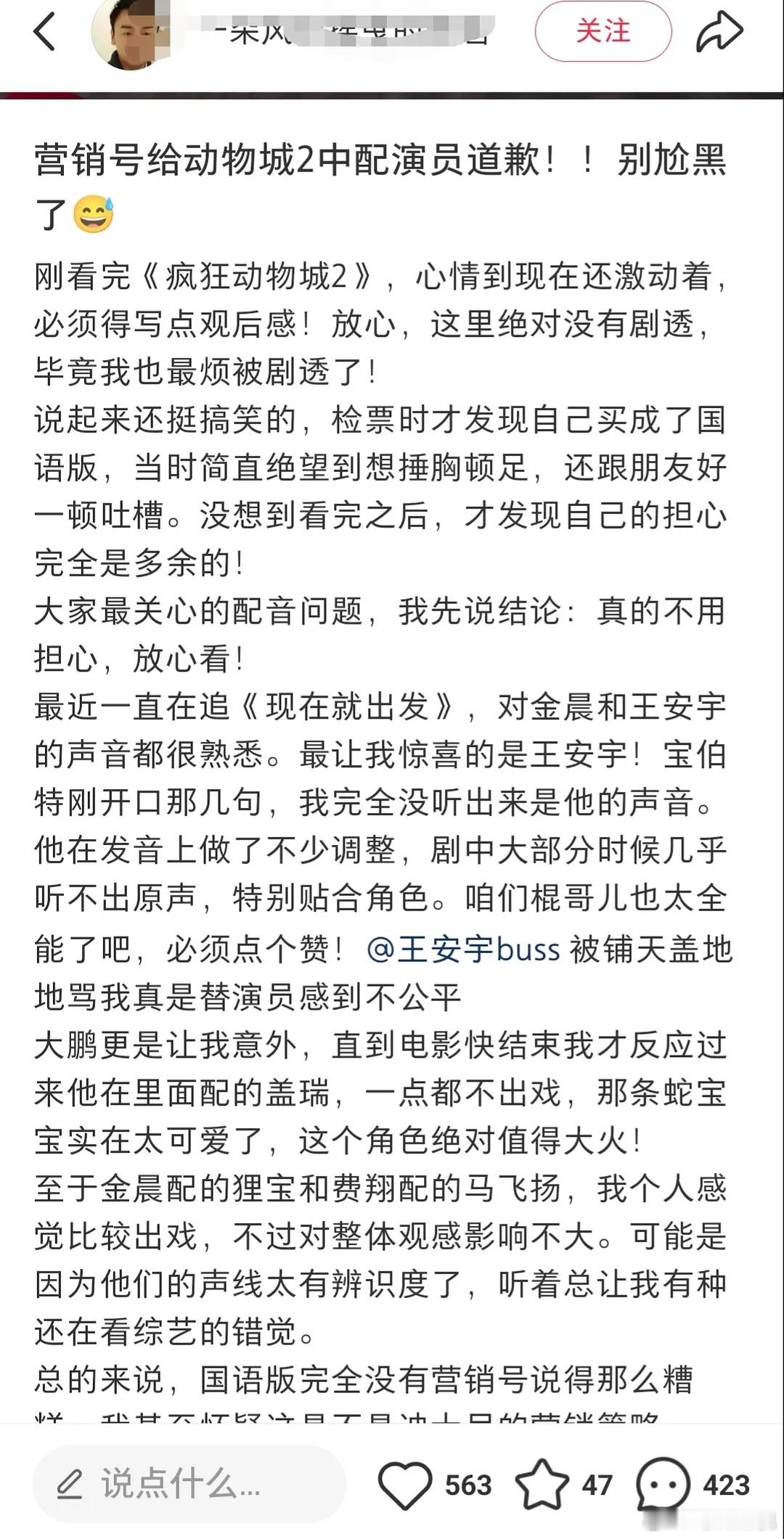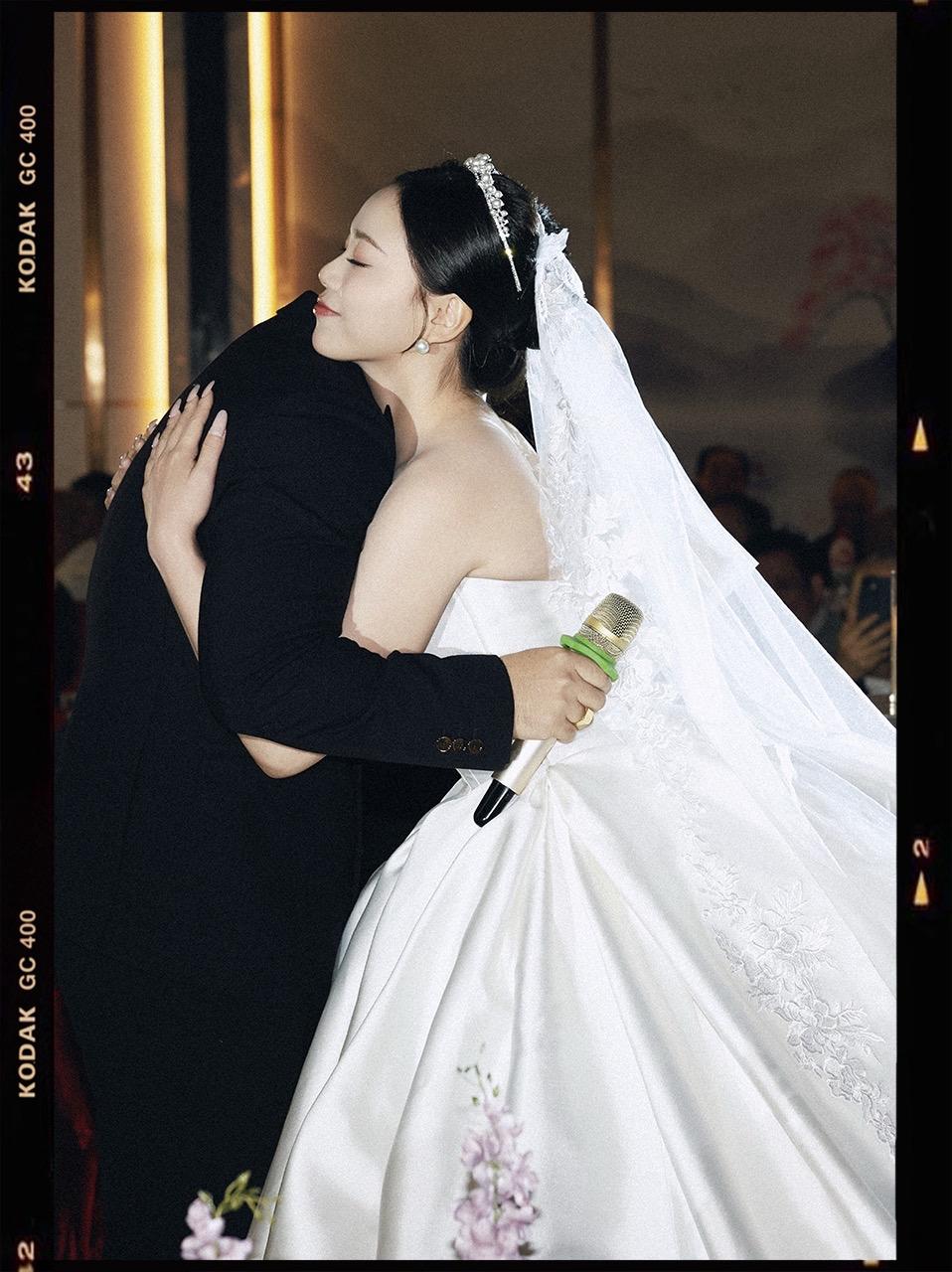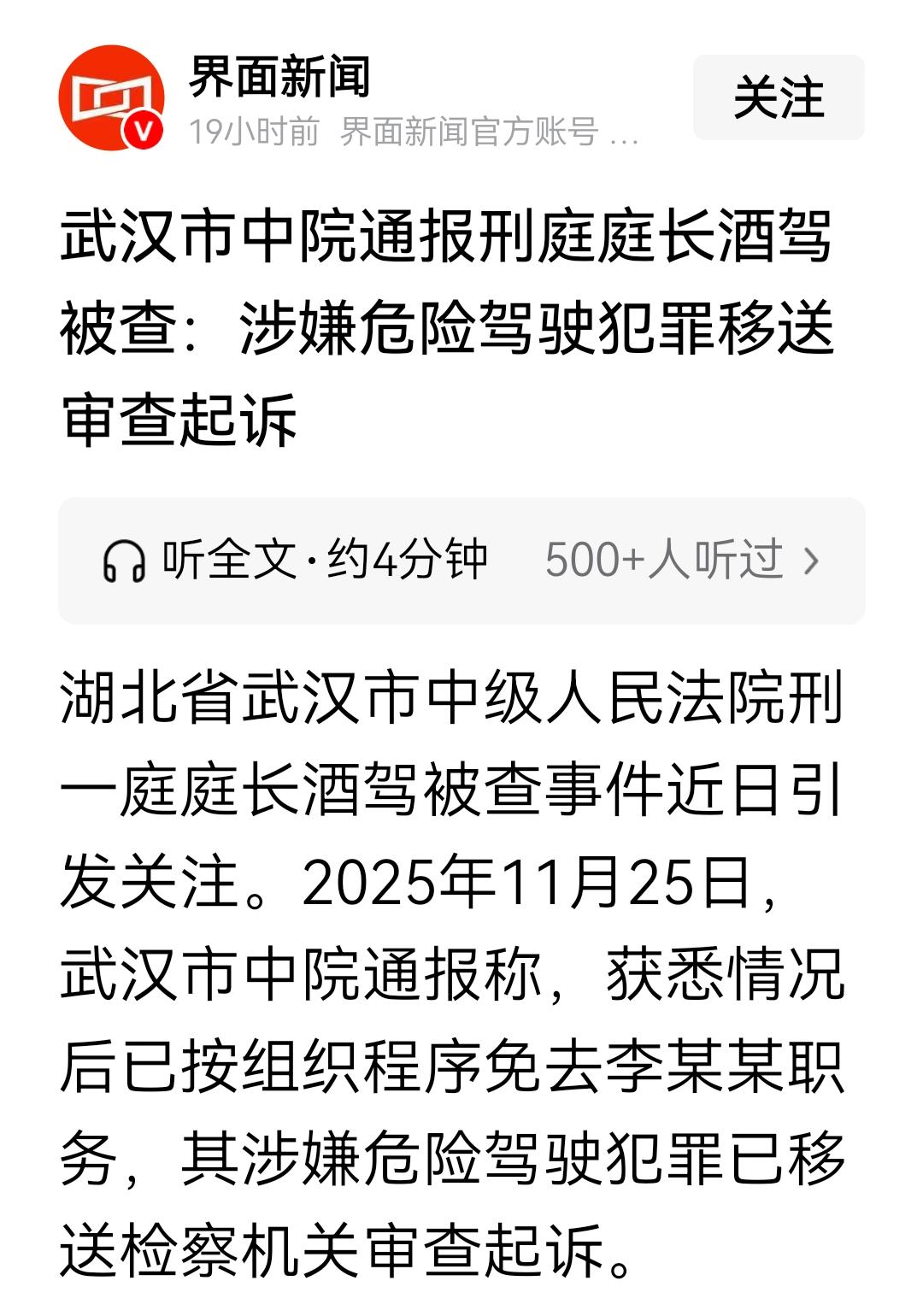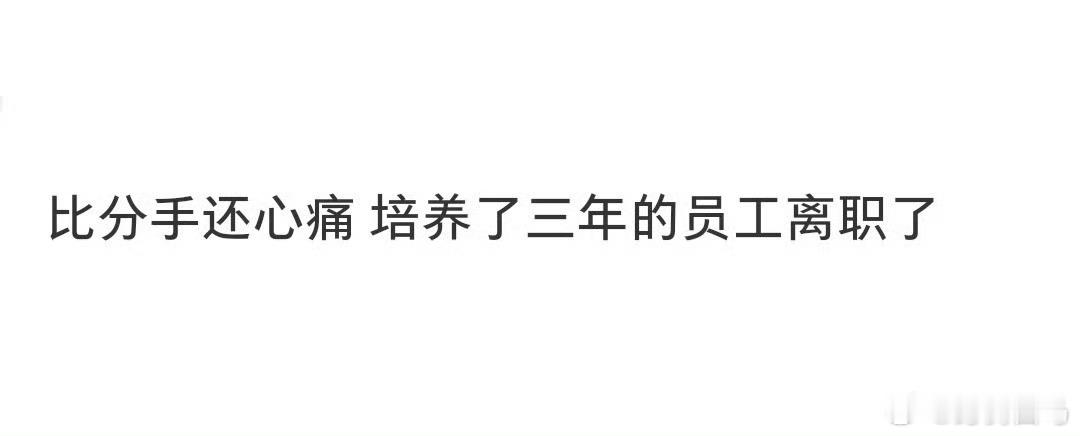她不上班,但每月拿九万三,比香港普通家庭多出两倍多。 不是25万,是媒体算错了账——牙科、学费,不能当月月开销。 梅艳芳走前怕她挥霍,留了信托,不是留了金库。 法院没让她一次拿走一个亿,反而多设了个百岁医疗户,算到她活到一百岁。 搬出跑马地豪宅,住进“梅寓”——不是免费,是信托内部调账,省下四万块。 钱没少给,但每一分,都卡在“别让她饿着,也别让她败光”这条线上。 她不是贪,是怕死。 怕没得花,怕没人管,怕女儿走了,自己就真成了孤老。 可信托不是提款机,是墓志铭—— 梅艳芳用钱,替她续了命,也锁了自由。 这每月九万三像把双刃剑,割破了亲情最后的体面。香港劏房里的打工族攥着血汗钱,望着这个住在“梅寓”的老太太。信托基金的条款写得明明白白,比墓碑上的刻字还要冰冷无情。 梅艳芳在生命尾声画下的这个圈,困住了母亲余生的脚步。那些数字游戏玩得漂亮,牙科费用单独列支,百岁医疗户头设得巧妙。这哪里是遗产分配,分明是场精心设计的财务囚笼。 九万三在香港能过什么日子?浅水湾一顿下午茶上千,中环理发也要八百。但对一个习惯挥霍的老人来说,这些钱就像漏水的勺子,永远舀不尽欲望的深井。 信托经理们坐在冷气十足的办公室里,拨算盘的声音比钢琴还清脆。他们不在乎老太太的哭闹,只忠实执行那个逝去明星的遗嘱。这出戏里每个人都是提线木偶,线头还握在已故之人手里。 老太太搬出跑马地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像极了梅艳芳出殡那天的天气。“梅寓”这个名字取得讽刺,哪里是故居,分明是座活人墓。四万块租金差价在账本上跳着数字芭蕾,却暖不了一颗苍老的心。 那些说老太太贪心的人不懂,人越老越像孩童。她吵着要钱的样子,多像孩子哭着要糖。可惜信托基金不是慈祥的祖父,而是最严厉的家庭教师。 梅艳芳或许早就看透,金钱既能延续生命,也能扼杀灵魂。她为母亲铺好的路,每块砖都刻着“控制”二字。这份来自黄泉的爱太过沉重,压得生者喘不过气。 香港的夜依旧璀璨,跑马地的灯火通明。“梅寓”窗前的影子日复一日地徘徊,数着日子,数着钱,数着女儿离开后的每一个晨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