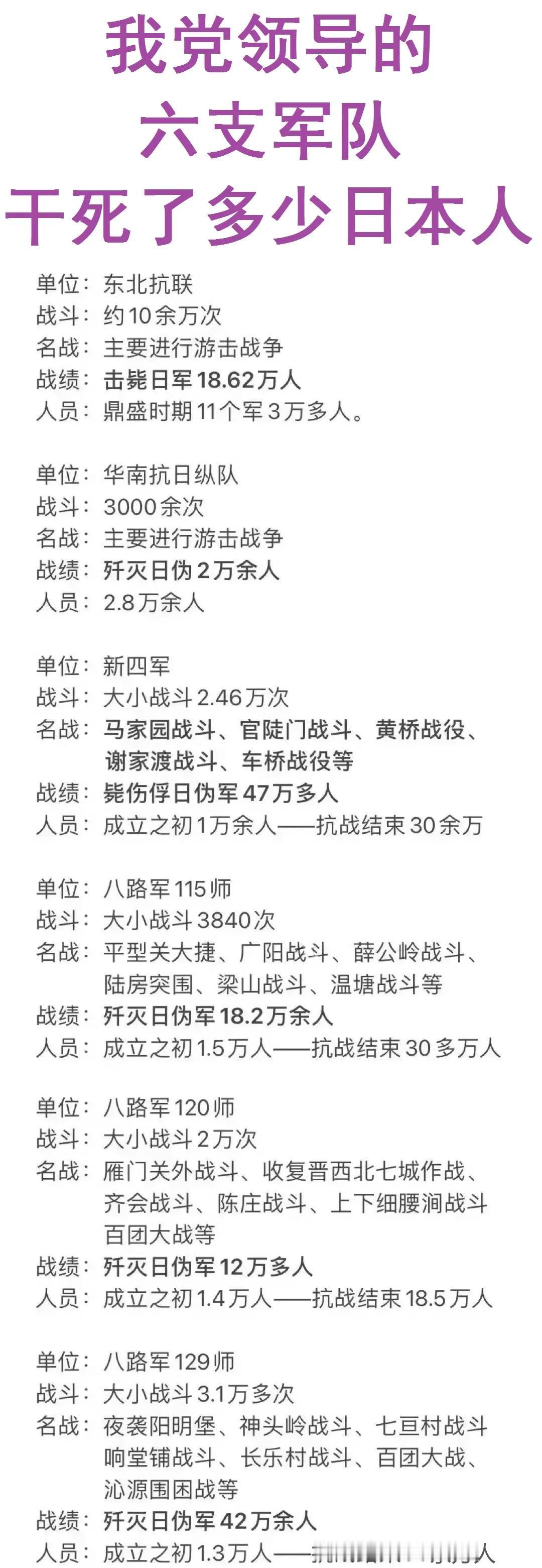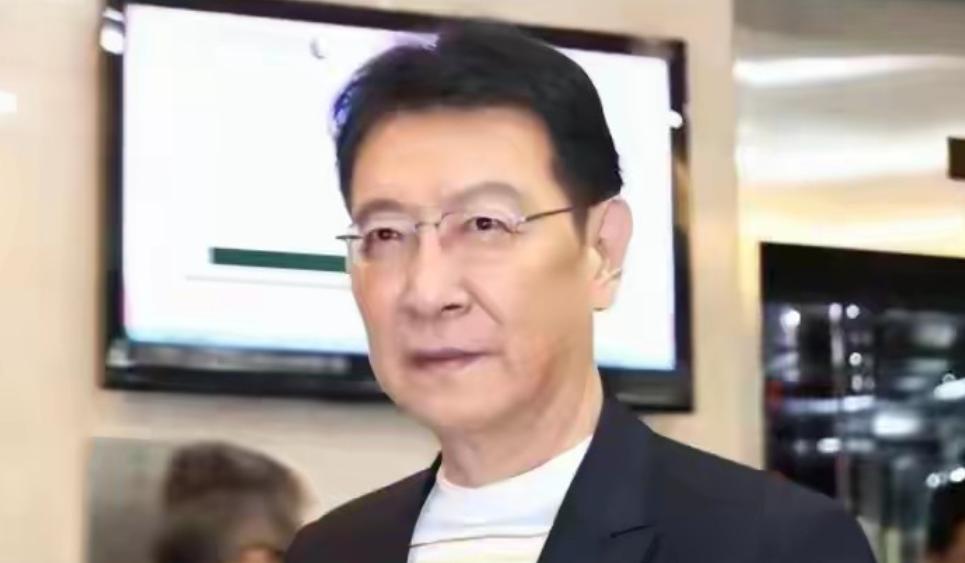[太阳]1964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 (参考资料:2016-07-1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慨然面对生死) 毛主席对生死的看法,藏着一对奇特的矛盾,他跟记者埃德加·斯诺聊起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坦言那纯粹是“偶然性”。 可转头又对护士长吴旭君强调,死亡是辩证法的必然,是新陈代谢,甚至是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 这种张力,远不是一句“英雄无畏”能概括的,它贯穿了一生。 死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延安,一颗炸弹下来,卫士当场被撕碎,温热的血溅到了他身上。 长征路上,飞机轰炸,警卫班长胡昌保为了掩护他而牺牲,这个1930年参军的江西吉安小伙子,让他流下了眼泪。 这些经历,让他对生命的脆弱有最直接的体感。 更早的时候,1927年秋收起义前,他还被地主民团逮住过,他揣着几十块钱想买通押送的士兵,普通士兵动了心,但小队长不干。 就在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他瞅准机会挣脱逃跑,躲进长满高草的水塘边,好几次搜捕的人就从身边走过。 那晚他光着脚走了一夜,最后靠着一个农民的帮助,用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买了鞋、伞和吃的。 正是这些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的经历,让他总结出几个听起来土得掉渣,却无比深刻的军事常识:“人要吃饭”,后勤是命脉。 “走路要用脚”,指挥不能脱离实际;还有最关键的一条,“子弹能打死人”,兵力是宝贵的,不能瞎消耗。 他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瞎指挥,就是因为那些人不懂这些。 但直面过无数次偶然的死亡威胁,他反而更透彻地思考着死亡的必然。 他甚至让护士长吴旭君去读《形式逻辑学》,然后第二天跟她玩起了三段论:“人都是要死的;我是人;所以我是会死的。”讲得冷静又清晰,像在讨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他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种新旧更替的自然法则,个体生命的终结,是为了给新事物让路,这在他看来,非但不是悲剧,反而是辩证法的胜利。 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识? 他对自己葬礼的设想更绝,他希望死后能开个庆祝会,大家要穿得鲜艳点,红的、花的都行,高高兴兴地来。 他还给吴旭君安排了发言稿,让她告诉大家:毛泽东死了是好事,要不然从古至今的人都活着,地球早装不下了。 晚年,他把这种豁达带到了国际舞台,他对基辛格说,自己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又跟福特开玩笑,说基辛格老是干涉他去见上帝。 他把衰老的身体比作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用幽默化解沉重。 这种超然的哲学思考,最终落实在了他对自己身后事的具体安排上。 他明确提出要火葬,而且希望把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他甚至想好了台词,要向鱼儿们“赔不是”:这辈子吃了不少鱼,现在让鱼吃我,你们长肥了,再为人民服务嘛,他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这个想法太超前了,吴旭君当场就拒绝,说自己不敢做。 但这并非他一时兴起,早在1956年,他就带头在一份《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件上签了名,后面跟着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长串名字,倡议书说得很明白,土葬占地费木材,火葬更合理。 然而,历史的走向充满了吊诡,他生前大力倡导火葬,反对个人崇拜的繁文缛节,但最终他的遗体却被保留下来,安放在纪念堂中。 很多年后,邓小平对法拉奇解释说,这是当时为了求得政治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其实违背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 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从“偶然”的幸存走向“必然”的物质循环,并试图为自己安排一场最彻底唯物主义告别的人,最终却以一个永恒政治符号的形式,留在了他曾想回归的物质世界里。 这或许是他那套辩证法里,最深刻也最无奈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