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3年,写下《浮生六记》的沈复,带着芸娘第一次去太湖。芸娘站在太湖边,忍不住说了一句:此即所谓太湖?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 沈复这人,说白了就是个古代版的“文艺青年”,还是个没啥编制的“合同工”。他给官府当幕僚,也就是师爷,工作不稳定,收入看天吃饭,一辈子没考取功名,最好的朋友都当上状元了,他还晃荡在苏州的巷子里。 可他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娶了芸娘。 芸娘是他表姐,从小没了爹,靠一手刺绣养家糊口。她不识几个大字,却能自己摸索着读诗写字,还写出过“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的句子。沈复十三岁第一次见她,就跟他妈说:“这辈子,非她不娶。” 你以为这是啥霸道总裁的戏码?其实就是两个有趣的灵魂,隔着二百多年的时光,给我们撒了一把最纯粹的狗粮。他们的婚后生活,没钱,但有情趣。 怎么个有情趣法?夏天太热,请不起人纳凉,芸娘就把荷叶当杯子,舀了井水,说这叫“荷盏”;家里来客人,菜不够,她能用几块豆腐干、几颗豆子,摆弄出精致的冷盘;沈复喜欢插花,她就研究花的姿态,说插花要疏密得当,像写文章一样讲究“起承转合”。 他们把别人眼里的穷酸,活成了独一份的雅致。 这种心态,放到今天,不就是咱们天天挂在嘴边的“生活美学”吗?不需要你买多少昂贵的“摆件”,只需要你有一颗愿意把日子过好的心。 芸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沈复一起游山玩水。可搁在那个年代,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人家,想出远门比登天还难。 公元1793年,沈复要去吴江吊唁朋友,他心里盘算着,终于有机会带芸娘出去看看了。他俩合计了一个“计策”:芸娘先借口回娘家,半路上再偷偷溜上沈复的船。这操作,跟现在年轻人为了旅游找借口请假,简直一模一样。 船行至太湖,那天的风不大,水面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芸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开阔的水域,之前她眼里的世界,不过是苏州城里那一方小小的天井。当她站在船头,看着远处的水天一色,帆影点点,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忍不住脱口而出: “此即所谓太湖?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这个读了无数遍的人,每次看到都眼眶发热。 想想咱们现在,出国游跟逛超市一样方便,朋友圈里的定位遍布全球。可有几个人,能在一片湖水面前,由衷地感叹“不虚此生”?我们见过的世面多了,心里的触动却少了。芸娘看到的是太湖,更是她被禁锢的生命里,第一次裂开的一道缝,那道缝里照进来的,是自由和天地的广阔。 那一刻的震撼,比我们打卡一百个网红景点,发一千张精修照片,都要来得深刻。 这就是沈复和芸娘教会我们的事:重要的不是你走了多远,而是你的心感受到了多宽。 真正的富养,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浮生六记》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真实。沈复和芸娘的爱情,不是完美的童话。他们后来因为家庭矛盾,被父亲赶出家门,颠沛流离,生活愈发困苦。芸娘最后因病早逝,沈复晚景凄凉,连唯一的儿子也夭折了。 听起来是个悲剧,对吧? 可为什么二百多年后,我们依然羡慕他们? 因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从未在精神上亏待过彼此。芸娘懂沈复的怀才不遇,沈复也敬芸娘的蕙质兰心。他们是物质上的贫民,却是精神上的贵族。 芸娘想女扮男装去逛庙会,沈复不但不觉得荒唐,还帮她张罗衣服;沈复的朋友来家里喝酒,她能落落大方地坐在一旁,跟大家谈诗论画。沈复说:“可惜你是个女的,不然咱俩就能一起访遍名山大川了。”芸娘笑着说:“这辈子不行,那就约来世吧。”沈复回她:“来世你当个男人,我做个女人,天天跟着你。” 这种灵魂上的平等和契合,是他们对抗生活所有苦难的底气。 回看今天,多少人把婚姻当成了一场交易。房子、车子、彩礼,样样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两个人在一起,谈的更多的是“条件”和“匹配”,很少有人去问:“我们的灵魂,在一个频道上吗?” 我们总说要“富养”孩子,给他们最好的物质条件。可张幼仪当年把已经生了四个孩子的儿媳张粹文送到美国留学,她说:“我受过的苦,你不能再受。” 她知道,真正的富养,是让一个女人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站稳脚跟的本事。这和沈复、芸娘的精神内核,其实是一样的。 沈复在书的开头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是啊,人生就像一场大梦,真正快乐的时光能有多少呢?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还是那些留在心底,谁也拿不走的温暖瞬间? 《浮生六记》给不了我们暴富的密码,也治愈不了生活的顽疾。但它就像一位老朋友,在你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 慢一点,再慢一点。去看看身边的人,去感受一阵风,一片湖。所谓“天地之宽”,有时候,就在你愿意停下来的那一瞬间。 或许,这才是那对清代夫妻,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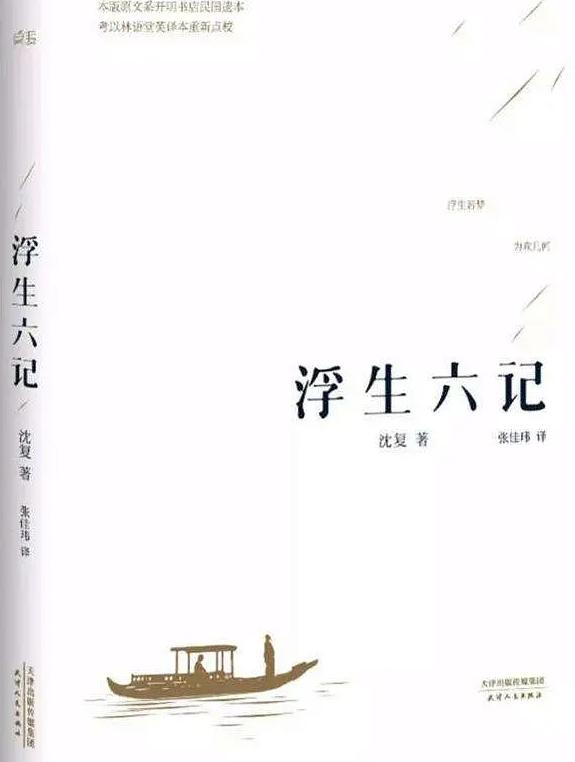

小老头
一个没志气,没毅力,没分寸,更没本事的人。只知玩乐,用现在的人叫啃老。游手好闲,不负责任的人。连儿女都不养的人,说是纨绔子弟还有点高抬,不成器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