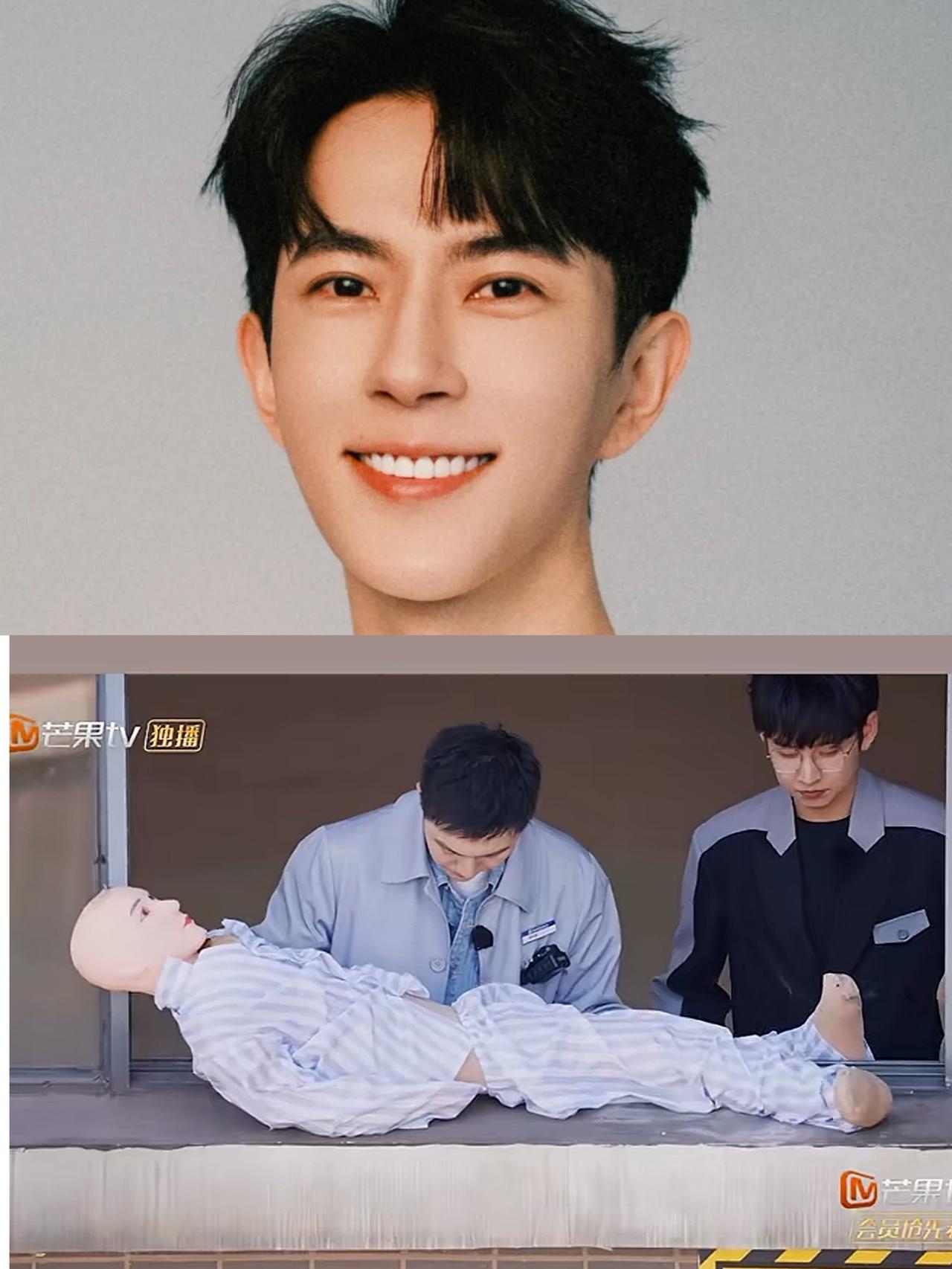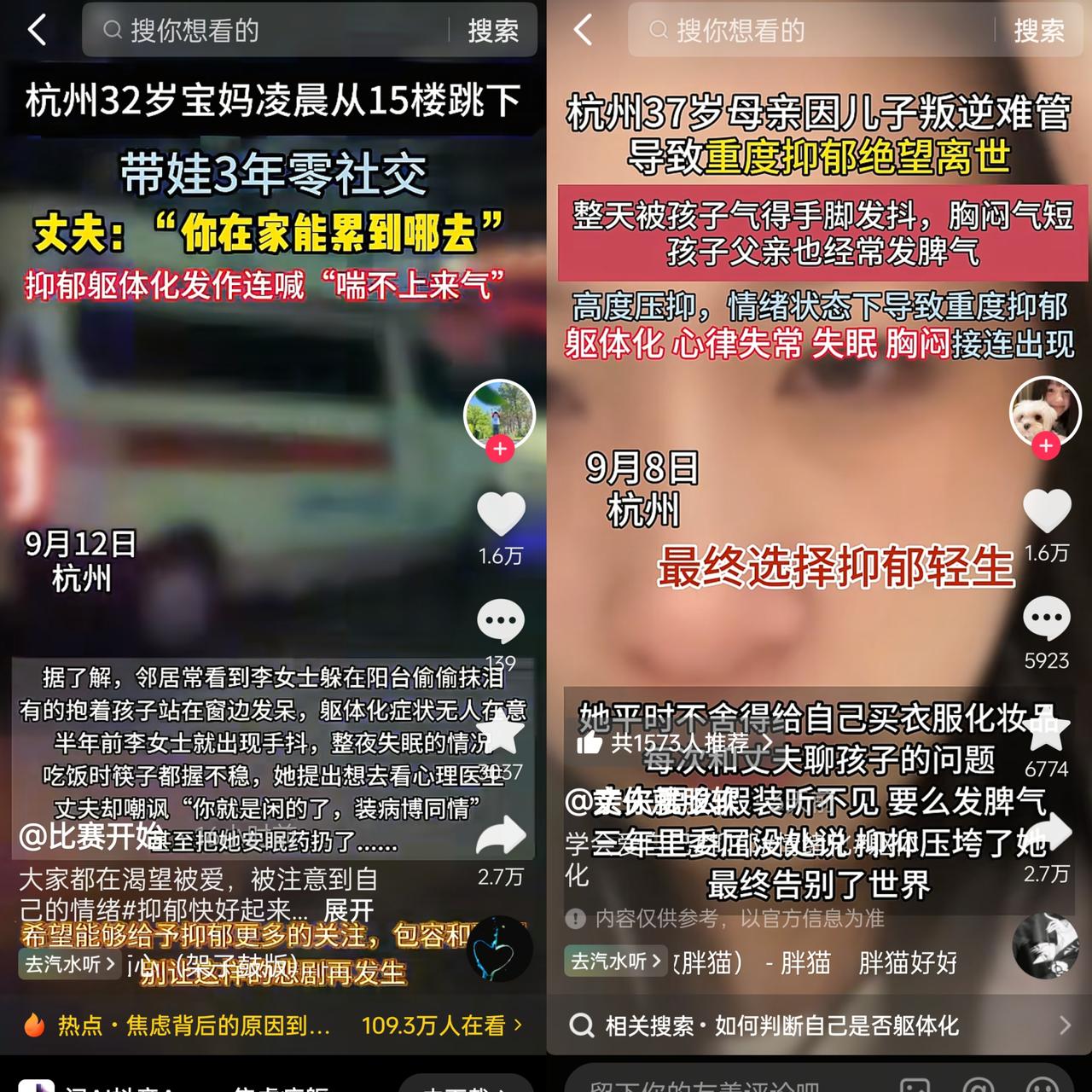徐学惠能进银行当值班员,在当时是全乡都羡慕的事。她老家在陇川边境的一个傣族村寨,父亲是村里的民兵队长,1956年在边境巡逻时因公负伤,落下了腿疾。 家里日子紧巴,她初中毕业就想着帮衬家里,听说银行招人的时候,揣着父亲攒的5块钱路费,走了两小时山路去县城考试。笔试考珠算和记账,她手指翻飞算得又快又准; 面试时考官问“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她攥着衣角说“公家的东西,绝不能让人拿走”——就凭这股轴劲,她成了所里最年轻的值班员。 那天凌晨,她刚把当天的流水账核对完,趴在桌上想眯一会儿。营业所的木门是老式的,没装防盗锁,只靠一根木栓顶着。 “哐当”一声巨响,木栓被踹断的瞬间,她猛地惊醒,就看见6个蒙着脸的男人冲进来,手里的长刀在煤油灯下发着冷光。为首的人一把揪住她的衣领,刀尖抵着她的下巴:“钱箱在哪?不说就捅死你!” 徐学惠的脑子“嗡”的一声,却下意识往桌下躲——钱箱就藏在桌底的铁柜子里,钥匙串在她的裤腰带上。她伸手去摸钥匙,想趁乱把柜子锁死,可歹徒眼疾手快,一把拽住她的胳膊,另一个人已经蹲下去把钱箱拖了出来。 那箱子有半人高,装着全乡农民卖粮的款、合作社的周转金,总共1.2万元。在1959年,这笔钱能买3000斤大米,够全乡人吃半个月,她怎么能让这些人把钱抢走? 她扑上去抱住钱箱,指甲死死抠着箱子的铁皮。为首的歹徒急了,挥刀就往她胳膊上砍,鲜血“唰”地喷出来,溅在钱箱的红漆上。 她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却没松手,反而把箱子抱得更紧,往墙角挪。歹徒们见她不撒手,开始用更狠的手段:有人用刀柄砸她的后背,有人拽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还有人踩着她的脚,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再犟就割你的喉咙”。 她的头被撞得昏昏沉沉,嘴里满是血腥味,可耳边总响着父亲说的话:“你守着银行,就是守着大家的活路。” 有个歹徒见硬的不行,想把钱箱从她怀里抢出来,两人拉扯间,她突然一口咬在对方的手腕上,那人疼得惨叫一声,挥刀就往她手上砍。 这一刀下去,她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瞬间就垂了下来,骨头都露在了外面。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是住在营业所隔壁的乡武装部干事老张,他晚上听见动静不对,骑着马去附近村寨叫人。歹徒们听见马蹄声,知道再拖下去会被围住,只能放弃钱箱,翻后墙跑了。 老张冲进营业所时,看见徐学惠瘫在地上,怀里还抱着钱箱,浑身是血,右手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泡,他赶紧脱下外套裹住她,喊着“坚持住,医生马上就来”。 送到县医院后,医生说她的右手神经被砍断,左臂有三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头部还有轻微脑震荡,就算治好,右手也很难再用劲了。 住院期间,县领导来看她,把一面“护财英雄”的锦旗递到她手里,她用没受伤的左手接过,眼泪掉在锦旗上:“我没让他们把钱抢走,没给所里丢脸。” 后来,徐学惠的事迹传遍了全国,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去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可很少有人知道,她出院后遇到的难处:右手基本废了,吃饭、穿衣都得靠左手慢慢练; 原本订好的婚事,男方家见她成了残疾人,主动退了亲;有人劝她跟单位申请调个轻松的岗位,她却摇摇头,回到营业所做了档案整理的工作,用左手一笔一划地登记账目,账本写得比以前还工整。 去年我去瑞丽采访,在陇川乡银行的陈列室里,还能看到当年那个红漆钱箱,箱子上的血迹已经发黑,却被擦得干干净净。讲解员说,每年新员工入职,都会来这里听徐学惠的故事。 现在的银行有监控、有防弹玻璃,再也不用靠人用身体护钱箱了,可那种“把公家的事当自家事”的劲头,还在一代代传下去。 徐学惠后来嫁了个退伍军人,生了两个孩子,退休后还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当年的事。她总说:“我不是英雄,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可正是这份“该做的事”,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在危难面前,也能迸发出撼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靠勇气撑着,是靠对责任的坚守,对他人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