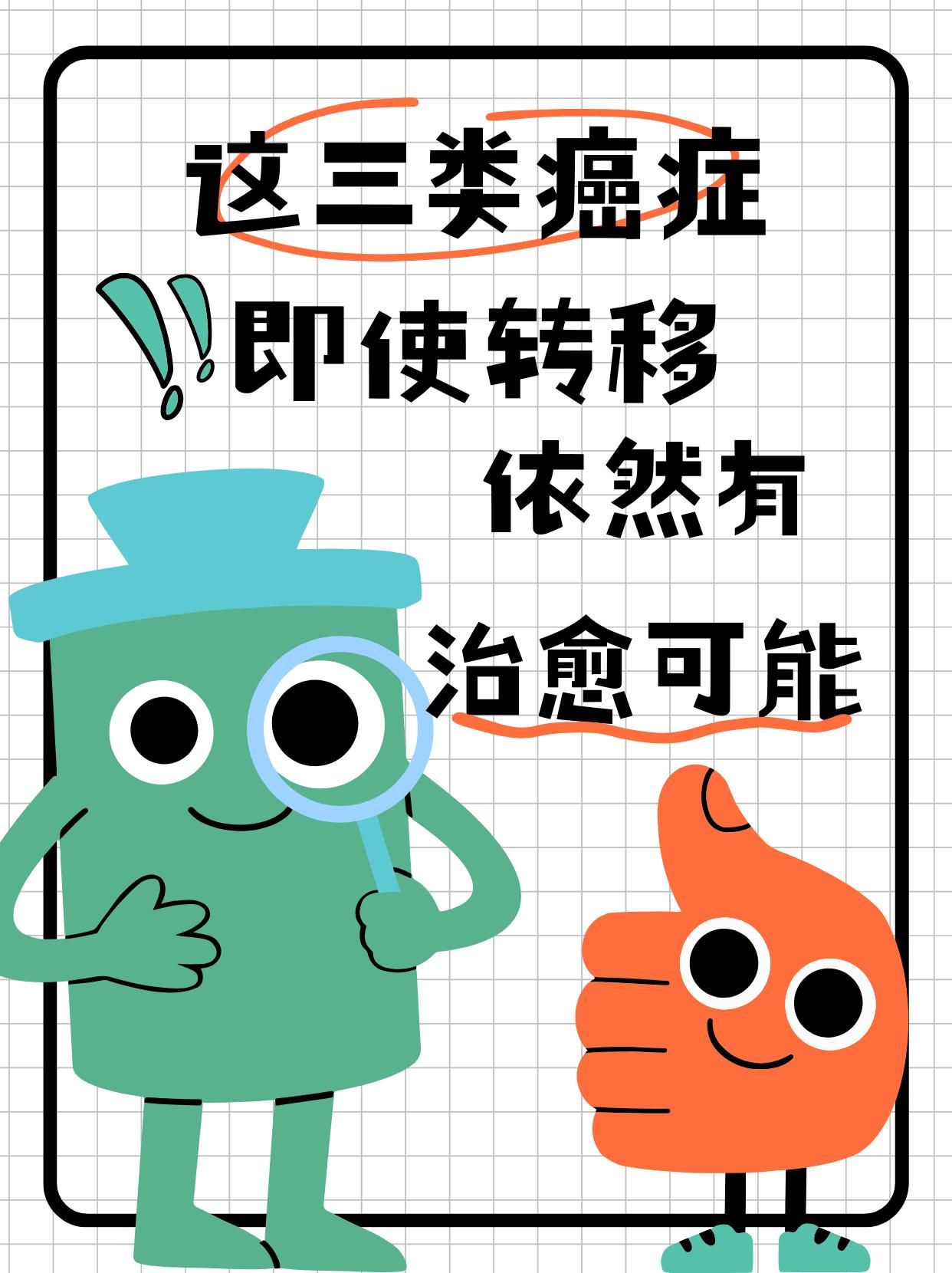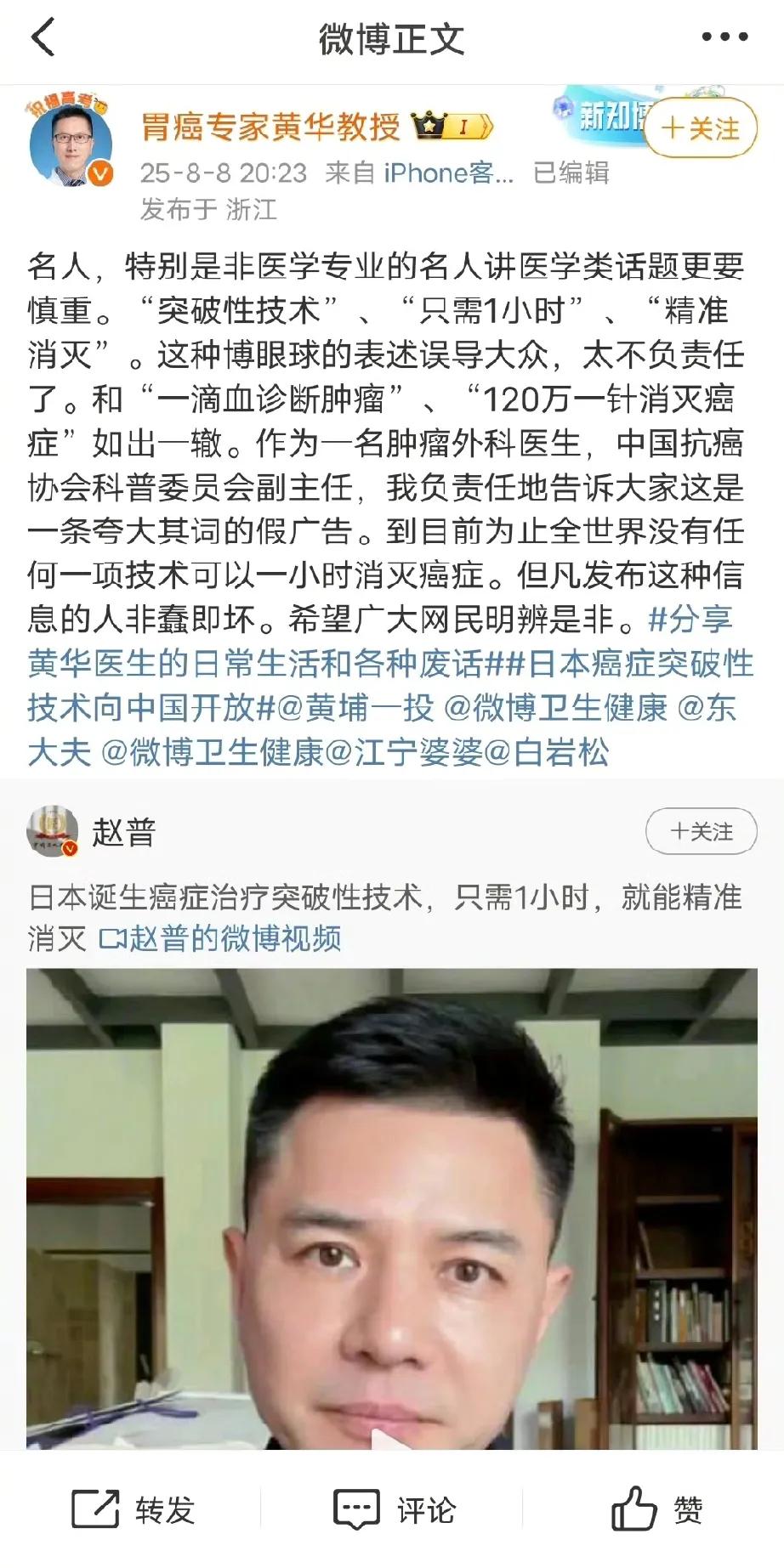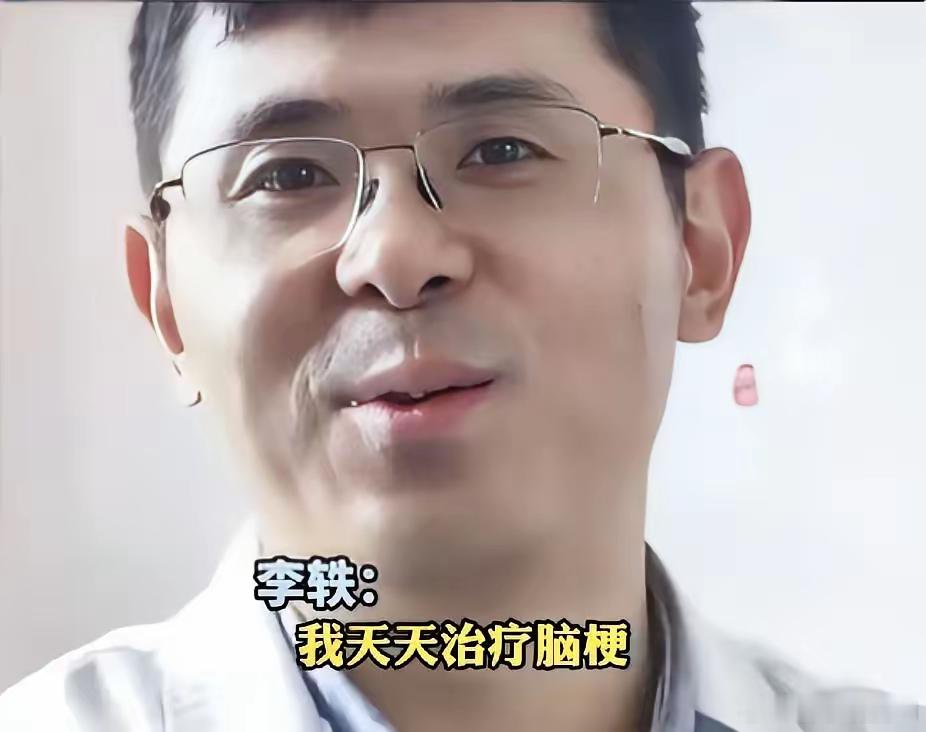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流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2年6月16日,北京医院的病理解剖室格外安静,白色的灯光下,医生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遵从罗健夫的遗愿,开始解剖这位年仅四十七岁就离开人世的科学家。 当手术刀划开胸腔的那一刻,场面震撼了所有人,一个直径超过心脏的巨大肿瘤赫然显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几乎没有一处是健康的组织。 有人低声抽泣,年长的医生红了眼眶,谁也无法想象,这样的身体,竟然支撑着中国最艰难的科研攻关整整十年。 罗健夫出生在战乱的年代,童年的经历让他早早萌生了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求学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十六岁参军入伍,在部队锤炼了坚韧的意志。 退役后,他考入西北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年轻学子,大学时期,他深受“科学要服务国家”的信念影响,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用知识与拼搏来守护家国,从西北大学毕业后,罗健夫本来从事的是核物理研究。 1969年,他被调去承担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研制中国自己的图形发生器,这是一种制造集成电路的核心设备,是航天、计算机、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工具。 当时国内几乎一片空白,国外又严密封锁技术,没有资料,没有设备,也缺乏专业人才,几乎处处都是障碍,面对这种困境,他没有退缩,反而把它看作国家需要时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为了跨过技术壁垒,他从零开始学习,白天在实验室反复试验,夜晚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把原本熟悉的核物理暂时放在一边,自学电子线路、光学系统、自动控制和精密机械,强迫自己成为跨学科的“全能战士”。 为了看懂外国的技术资料,他苦学俄语和英语,翻译成中文后再与团队一同钻研,每遇到难题,他都亲自去上海、北京等地请教专家,奔波在各大科研院所之间。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1972年,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终于研制成功,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让导弹制导和电子工业的精度提升了一个台阶。 那一刻,许多人欢呼雀跃,而罗健夫却只淡淡地说,这只是团队共同熬出来的结果,他把荣誉让给同事,把奖金用来买书送给年轻人,科研在他心里,从来不是个人的光环,而是国家的前进阶梯。 第一代设备问世后,他没有停歇,又带领团队投入第二代产品的研发,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意味着更多的难题,他常常在实验室连续十几个小时,吃点干粮就继续干活。 到了1975年,第二代图形发生器再次取得突破,科研的脚步并没有就此放缓,他开始着手第三代产品的设计,就在这时,病魔悄然袭来。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他就因为长期咳嗽吐血被迫住院,诊断书上赫然写着“淋巴肉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却只在病床上停留了半个月,就毅然回到研究所。 身体已经开始肿胀,手无法握笔,他便用绷带把笔绑在手上继续绘图,后来癌细胞扩散到腰背,疼痛让他无法坐直,他就跪在椅子上工作。 裤子磨破了,就垫上棉布继续坚持,那些止痛药瓶堆在实验室角落,成了一座小山,但他从不在同事面前喊疼,总是笑着说没什么大碍。 1981年底,他在工作中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是晚期癌症,医生告诉他最多还能活三个月,他最关心的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能不能完成第三代图形发生器的设计。 他拒绝使用强效止痛药,因为药物会让思维变得迟钝,他宁可清醒着忍受剧痛,也不愿在昏沉中停滞工作,病床上的他依然拿着图纸,修改参数,校正方案。 1982年春天,他终于完成了全部设计,那套图纸后来成为国内极为重要的技术资料,继续推动了航天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旧想着科研,临终前,他嘱托同事要接着完善设计图纸,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主动提出捐献遗体,用身体最后一次为医学研究做出贡献。 1982年6月16日,解剖现场让医生们无比震撼,癌瘤几乎遍布全身,那颗比心脏还大的肿瘤,是他以生命燃烧的见证。 罗健夫的一生,是短暂的四十七年,却浓缩了几代科学家的坚守与奉献,他没有留下华丽的头衔,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科研不是为了个人荣耀,而是为了国家前进的道路,解剖室里的泪水,不只是对一位科学家离去的哀悼,更是对那种精神的敬仰。 比心脏还大的肿瘤,是病魔残酷的标记,也是一座无声的丰碑,它记录着一个人怎样用生命与时间赛跑,把最后的清醒留给科研,把有限的生命化为通往未来的桥梁。 罗健夫离开了,但他的精神长存,他为国家点燃的火焰,仍在一代代科研人心中燃烧。 信源:人民网——罗健夫:心中有家国 淡泊且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