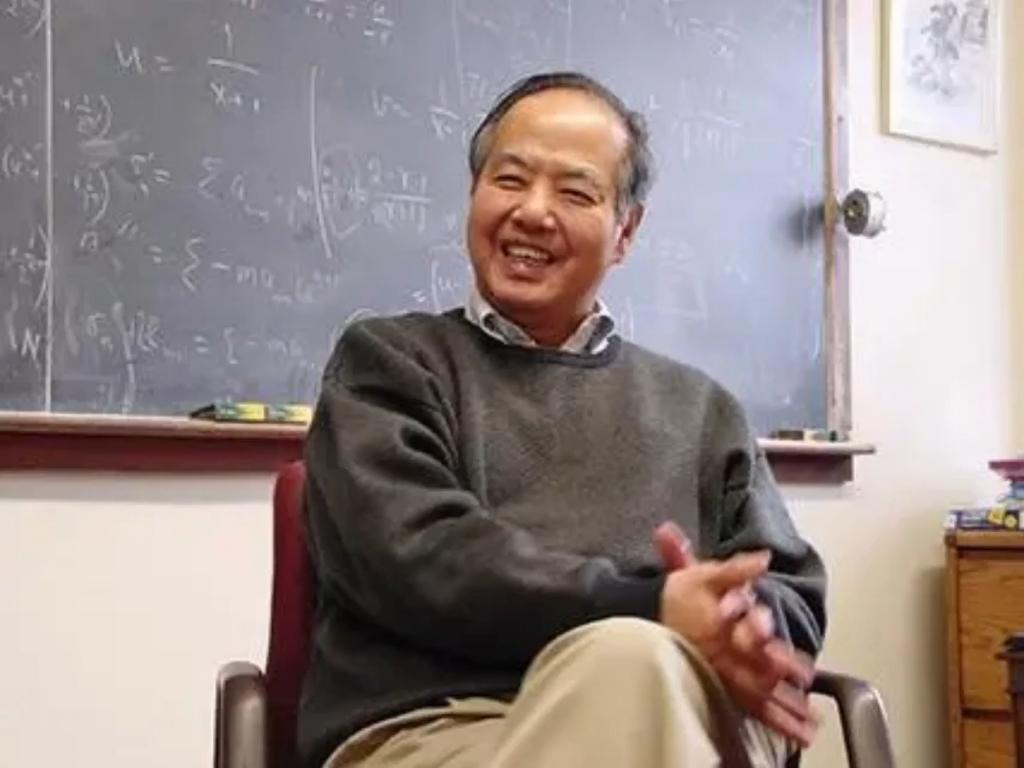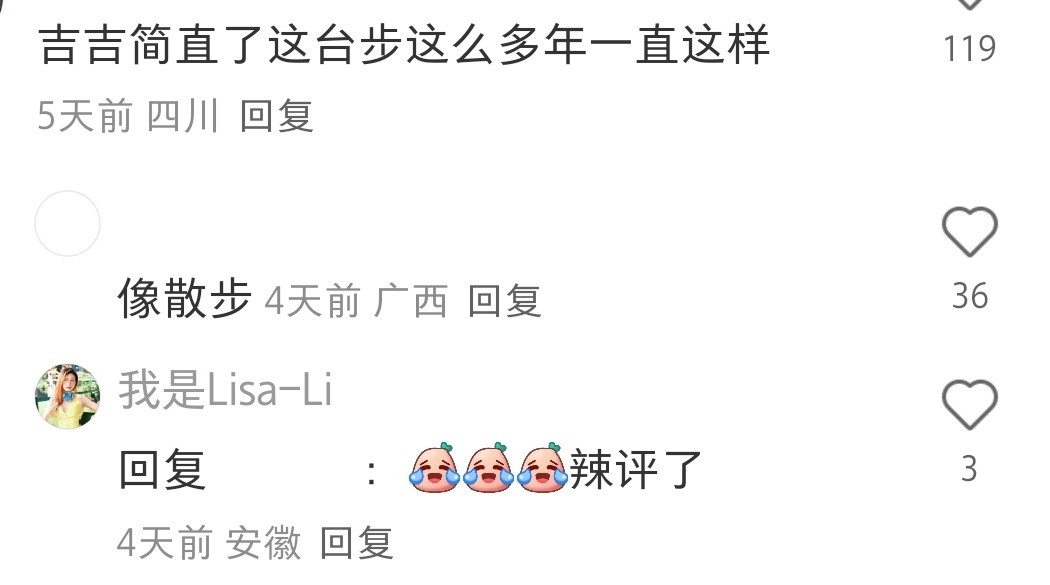1946年冬,谢汉光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以“林业专家”的身份从香港辗转赴台,加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工委)。临行前,他在潮汕老家的土屋里与新婚妻子曾梅玉许下誓言。 他将一把铜锁交给她,郑重地说:“锁在人在,我一定回来。”曾梅玉攥着锁,泪眼婆娑地点点头。那一刻,院子里刚栽下的苦楝树苗随风摇曳,像是见证了他们的约定。 台湾的生活却远比想象残酷。谢汉光潜伏在基隆,表面上是林业实验所的普通职员,暗地里为台工委传递情报,联络地下党员。 1947年,他登记入职台湾省农林厅,化名“叶依奎”,这份伪装的身份成了他日后活命的护身符。 然而,1950年的“基隆中学事件”如晴天霹雳,台工委遭国民党当局重创,上级张伯哲被捕牺牲,组织几乎全军覆没。谢汉光侥幸逃脱,却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逃亡生涯。 为了躲避白色恐怖的肃清,谢汉光逃进台东深山,伪装成林场工人。山林里没有灯火,他靠野菜和山泉果腹,营养不良让他患上了夜盲症。每到夜晚,他只能摸黑前行,跌跌撞撞,几次险些滚下山崖。 一次伐木事故,他被机器夺去了右手三根手指,鲜血染红了工服,但他咬牙包扎,继续干活,只为不露破绽。 在山中,他不敢与人深交,怕暴露身份。夜晚,他常坐在溪边,借着月光摩挲那把藏在怀里的铜锁,回忆曾梅玉为他梳头时发间的茶油香。 那是他唯一的念想,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档案记载,他曾在一封未寄出的家书中写道:“梅玉,苦楝树长高了吗?我还活着,等我。”但这封信,最终被他烧毁在山风中。 时间流转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两岸探亲。谢汉光在台东的林场听到了广播,愣了许久。他用“叶依奎”的身份提交了返乡申请,却因档案缺失被反复核查。 红十字会几经辗转,终于在汕头档案馆找到他的真实身份——谢汉光,饶平县浮滨镇人,中共地下党员。 1988年11月,他获批返乡,带着那把铜锁和一颗忐忑的心,登上了回大陆的船。 船行海上,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模糊的海岸线。42年了,妻子是否还在?她是否还记得那把锁的誓言?他的心像被海浪拍打,忐忑不安。没人知道,码头上是否还有人等着他。 汕头港的码头上,人群攒动,横幅“欢迎亲人回家”在风中微微褪色。谢汉光下船时,腿脚发软,几乎摔倒。一个身影从人群中挤出,穿着粗布衣裳,头发花白却依旧用茶油梳得整齐。 曾梅玉站在他面前,双手颤抖,摸向他缺了三指的右手,眼泪夺眶而出:“当年你说‘锁在人在’,我就知你会回来……” 谢汉光哽咽着掏出铜锁,递到她手中。两人相拥,茶油香气弥漫,仿佛时间倒流回1946年的新婚之夜。 回到浮滨镇的土屋,谢汉光看到院子里那棵苦楝树已合抱粗,树皮上刻的“光”字被岁月磨平,只剩浅浅凹痕。 屋檐下,曾梅玉晒芋丝干的竹匾已经蛀损,她却日复一日地修补,像是用竹篾编织着对丈夫的信念。 邻居回忆,曾梅玉从不提改嫁,靠刺绣养大养子谢锋,屋里始终挂着那块褪色的“光荣军属”牌。她说:“汉光为国做事,我得守好这个家。” 谢汉光的归来,不仅是夫妻重逢,更是台工委那段隐秘历史的缩影。台工委1800余名党员,至1987年仅30余人幸存返乡。 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张伯哲,早已长眠于白色恐怖的枪口下。谢汉光的42年潜伏,是无数地下党人用生命书写的忠诚。他们隐姓埋名,山林为家,却从未背弃信仰。 重逢后的谢汉光和曾梅玉在浮滨镇度过了余生。1990年,谢汉光在镇志编撰时留下一句话:“我这一生,欠梅玉太多,但国不负我。” 2001年,他因病去世,曾梅玉将那把铜锁与他一同下葬。她说:“锁在人在,他在,我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