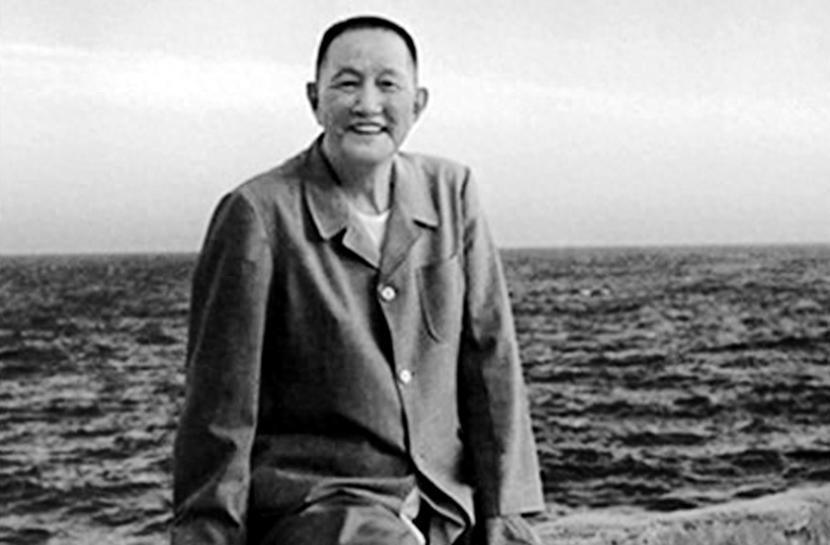1970年洪学智下放农场养猪,被猪气得大喝:我可是开国上将洪学智 “嗨!你们这些不听话的家伙,再跑,我可要记过了!”——1970年11月4日凌晨,猪圈边的洪学智忍不住吼出这句带着半分无奈半分火气的话。夜色还浓,泥地里却已经闹腾得像集市,一群小猪拱翻木桶,满地乱窜。听到这声呵斥,旁边的孙炎峰愣了愣:一个月前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个蹲在豁口里追猪的灰衣老头,是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指挥过数万人冲锋的开国上将。 清晨的薄雾散开,农场大院渐渐热闹起来。几名青年站在围栏外看热闹,小声议论:“真是洪副总参谋长?”“别瞎说,他现在可是我们粮库的小工。”说者语气带着狐疑,却也带着敬意。洪学智没理会,他们在哼哧喘气,他在琢磨战术——猪圈的门得加固,饲料得调配,最要紧的是先把猪哄进圈。对他来说,这跟当年在朝鲜布阵并无两样,只是对手换成一群饿得见风就跑的小畜生。 时间往回拨三十天。10月2日午后,风卷黄叶,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吉林金宝屯胜利农场。车门开处,两个年轻军人先跳下,随后搀下一位五十出头的老同志。没有欢迎仪式,只有豆腐坊里飘出的湿热蒸汽和黄豆香味。负责豆腐坊的“老穆头”听说来了个“老洪”,只抬眼瞄了一下:“干活儿的吧?先换工作服。”直到当晚农场接到省里通知,才知道这位“老洪”就是一年前还在重工业厅主持工作的洪学智。 职位骤转,气度不变。落脚第二天凌晨五点,洪学智就跟着磨豆,点卤、压块一气呵成,老穆头看得直咂舌:“行家里手,可惜了。”老洪笑笑,只留一句:“家里世代贫农,豆腐活计熟得很。”此话半真半假,他确实是贫苦出身,却从未真靠磨豆谋生,少年习武,青年从军,打到解放战争尾声时已是东北野战军的要员。 短暂的豆腐坊时光,农场青年很快发现这位老同志干活不要命。扛麻袋那天最能说明问题:200斤的粮包,一般年轻小伙两人抬他一人扛,跳板窄如尺,他稳得像装了陀螺。一个上午连趟十几趟,肩头勒出青印,也没吭一声。午饭时还有心情给大家讲战场趣事,惹得几个小工哈哈大笑,累意倒消了一半。 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农场领导把新开的养猪场交给他。交接那天,猪仔们正缺料,饿红了眼,到处啃庄稼。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洪学智却点头:“行,我试试。”头三天几乎是被猪“牵着鼻子走”,泥浆糊了一身。第四天夜里,他被猪气得拍栏杆,高声自嘲:“我可是开国上将洪学智,连你们都收拾不了?”一句玩笑,一身汗。 方法总比困难多。第五天拂晓,他挑着两担酒糟回来,掺谷糠煮透。酒糟香味一出,小猪们围着料槽打转,吃得肚圆,倒头就睡。趁这功夫,他补栏杆、装闸门、规划圈舍动线。几天后,猪仔再没闹过事。此后一个月,他坚持早晚各煮一锅酒糟杂粮,猪长得飞快。三个月,七十多头猪个个身壮体肥,农场账面上第一次出现肉食盈余。 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发明意外带动了地方酒厂。原本要倒掉的酒糟变成抢手货,厂里一个会计算了笔账:一年能多卖出近两万斤酒糟,折合现金足够添置一条灌装线。当地报纸登了短讯,没写出发明者姓名,只说“驻场技术员老洪”。消息传到省里,有人对号入座,轻轻叹息:“他还是那个洪副总参谋长,哪里像个下放干部?” 1971年初春,中央组织部门着手为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平反,洪学智也在名单里。4月16日,复查组派车来接他回省里。听到消息,农场职工拥到路边,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塞给他一双自家纳的千层底鞋,有人掂着两个咸鸭蛋硬往口袋里塞。洪学智把打包好的行李解了,又分出自己用惯的搪瓷缸、棉大衣给几个困难户。车发动时,他只说了一句:“我离开,但咱还在一个祖国,谁要是路过北京,来找我喝茶。”话不多,声音却沉稳。 半个世纪后,2003年夏,他再回金宝屯。八十四岁的他拄着拐杖,走到当年猪圈旧址,木栏早换成水泥围墙,墙根仍能闻到淡淡酒糟味。他笑着同陪同人员回忆:“那一年多,没上过战场,却天天打仗。对手是体重不足三十斤的小猪,却厉害得很。”在座的年轻职工听得直乐,不敢打断。 不得不说,洪学智在农场这段插曲,看似离奇,却与他一生行事风格连成一线:分到什么岗位,就在那儿做到最好;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就琢磨最简单有效的招。战时是敌军,和平年代可能只是饿急了的猪仔,本质没变——都是问题,都需要解决。 我个人一直认为,某种意义上,这一年多的下放比金星勋章还珍贵。它让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高级将领,重新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群众站在同一条生产线。磨豆、扛包、养猪,这些最基层的工作催生了那句他后来常说的话:“劳动锻炼人,哪怕当过将军,也得出汗。”他不是在展示高风亮节,只是在重复一种信念:真正的强大并非军功章,而是始终能把每件小事干到极致的那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