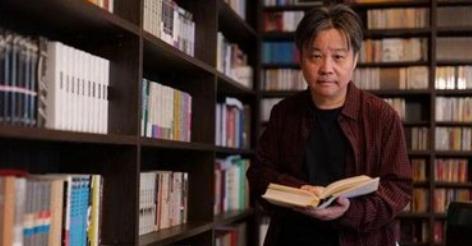1991年余华想去北京闯荡,妻子潘银春坚持反对,因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两人离婚,很快他就娶了一位性感的女诗人,凭借一本书赚到了1550万。 1991年的一个初夏午后,浙江海盐的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海腥味。余华伏案写作,窗外是蝉鸣与远处打铁的叮当声。 他的桌上堆着厚厚的稿纸和几本翻得卷边的书,《人民文学》杂志寄来的信静静躺在一旁。 信中说,他们诚挚邀请余华赴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笔会,届时会有许多知名作家到场,这对一个在文学道路上摸爬滚打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那天傍晚,余华握着那封信,走进了厨房。妻子潘银春正在煤油炉上煮着晚饭,米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余华有些激动地说:“银春,《人民文学》要我去北京参加笔会,我想借这个机会去闯一闯。” 潘银春抬头,眼神中闪过一丝迟疑。她放下勺子,擦了擦手,语气却很平静:“余华,你的写作我一直支持,可这些年下来,你真正写出了什么?我们家的日子有改善吗?北京的生活开销那么大,你去那边,不一定能立住脚啊。”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泼在余华心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嘴角抽动了一下,却没有反驳。那天晚上,两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坐了很久。 余华望着桌上的油灯,心里有一股难以言说的倔强与失落交织。他明白妻子是现实的,也是为了生活考虑,可他又觉得,如果不去闯一次,这辈子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这座小城里。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气氛越来越冷。潘银春不再提笔会的事,余华也不再开口争取。 终于,1991年8月的一天,两人默契地走进了民政局,没有争吵,也没有眼泪,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那一刻,余华心里有一种轻飘飘的空落感——像是一个人从熟悉的港湾松开缆绳,驶向未知的海面。 离婚后不久,余华只身去了北京。彼时的北京对他来说既陌生又令人心潮澎湃。灰蒙蒙的天空下,他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厚厚的手稿。 生活并不容易,稿费微薄,房租和吃饭都是问题。 就在这样的时候,他遇到了陈虹。陈虹是个性格开朗、笑起来有梨涡的姑娘。她知道余华是个作家,但也看得出他穷得叮当响。 两人渐渐熟识后,余华坦白:“我现在的生活很苦,甚至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北京坚持下去。” 陈虹笑了笑:“我又不是看你有没有钱才跟你在一起。我喜欢你写作时那股认真劲儿。” 1992年,两人结为夫妻。婚礼很简单,甚至没有婚纱照。他们在北京租下了一间只有9平米的小屋,屋子里除了一个小木床,就是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 冬天的时候,寒风能从窗缝里钻进来,夜里睡觉要穿着毛衣盖棉被。做饭的地方只是走廊尽头的一块空地,一口小煤炉就是全部的厨房设备。 有一次,北京下了大雪,屋顶漏水,雨雪夹着寒气滴在床边。余华拿着盆接水,陈虹则笑着递给他热茶:“再苦也没关系,反正咱们在一起。” 日子虽然清贫,但余华的写作越来越投入。每天早晨,他坐在桌前,手握钢笔,伏在稿纸上写到天黑,指尖常常被墨水染得发蓝。 陈虹不但不抱怨,还帮他整理稿子、誊写草稿,偶尔出去打些零工补贴家用。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出版。那是一个关于苦难、关于生命尊严的故事,也凝聚了他多年来的心血与生活体验。 《活着》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在文学界赢得赞誉,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凭借这本书,余华赚到了1550万。 拿到稿费的那一刻,余华久久地沉默。陈虹站在他旁边,笑着说:“怎么样?我当初说不嫌苦,是不是没说假话?” 余华看着她,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感。这一路的艰辛,寒风、漏水、煤烟、饥饿……都因为这个女人的陪伴而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在回忆里带着温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