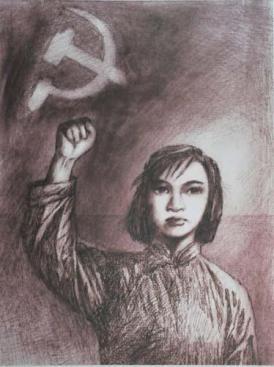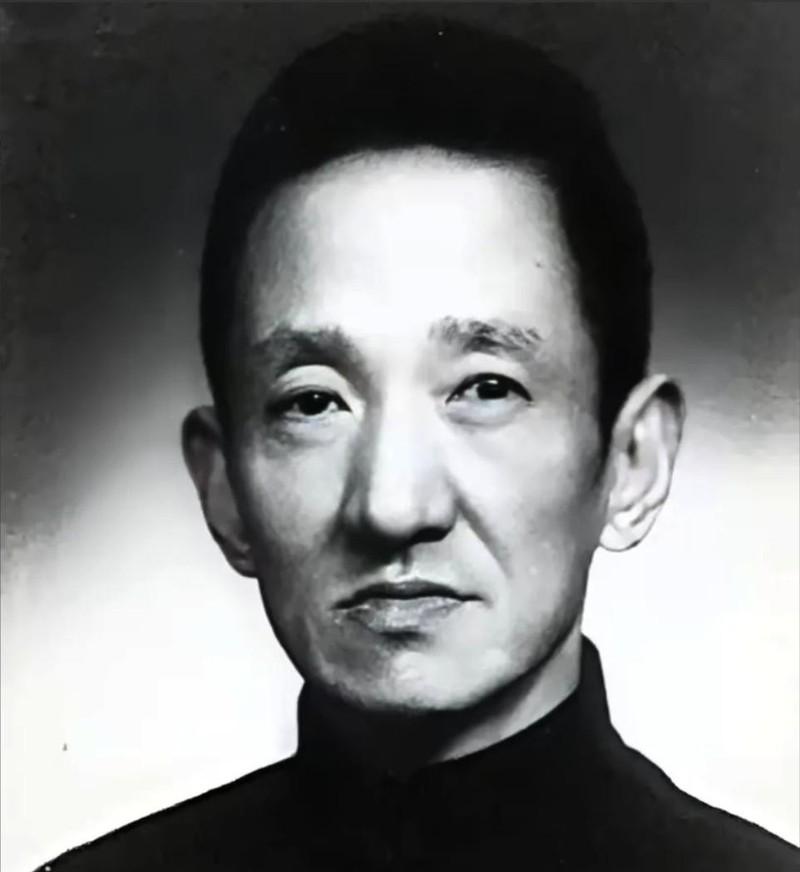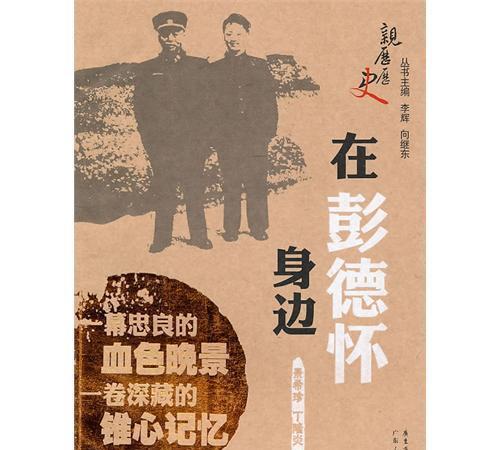王翠兰: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王翠兰是老王庄子东北街人。16岁那年,她加入了抗日妇女救国会,没多久就当上了村妇救国会主任。她有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王淑兰和王文兰,村里人叫她们“三兰”。 在战火连天的冀东平原,这三个小姑娘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缝军鞋、做军袜,喂伤员、端水喂饭,有时候还得替伤员擦洗伤口、换药。要知道,那时候不少伤口化脓流脓,气味呛人,可她们从来没嫌弃过。 在那个讲究“女子不外出”的年代,她们顶着流言蜚语,和男人一起站岗、传递情报。地主、汉奸造谣说她们“抛头露面”,甚至想借机破坏她们的名声。翠兰的父亲是个老实人,开始也担心女儿受牵连,想劝她回家少掺和,可她一门心思想的是前线和同志,拦也拦不住。 1944年5月3日,王翠兰光荣入党。她说过一句话:“干活多,干活快,心里才踏实。”入党后,她更是冲在最前面。 抗战胜利后,老王庄子开始土地改革。但地主势力仍在,本村有个地主父子,造谣、威胁、散布恐慌。翠兰看得很透:“不斗倒他们,咱的活干不下去。” 她带头搜集罪行证据,组织妇女在斗争大会上站在最前排。男人们受她带动,也站出来作证。最终,恶霸地主被斗倒,群众分到了地,心里也有了底。那一次,村里人对她的敬佩又深了一层。 真正的危险出现在1946年12月9日。逃跑的地主父子带着国民党军队和“伙会儿”杀回村里,想一网打尽区、村干部和物资。他们点名要抓“三兰”,还悬赏百元“现大洋”。 翠兰带着群众把公家和私人的粮食、布匹都藏好,才和大伙一起撤到苇泊里。那片苇泊足有十多华里,苇子高密,冬天结着冰,是天然的屏障。可是,敌人的“伙会儿”里有本地人,熟门熟路。组织上劝翠兰先转移,她摇头:“我不能丢下乡亲们。” 苇泊里的生活别提多苦了。腊月十五那天,鹅毛大雪下了两天两夜,雪深到膝盖,天寒地冻,很多人耳朵、脚趾都冻坏了。翠兰白天安抚群众,晚上替人站岗,还要向大家传达前线的好消息,鼓劲打气。 后来敌人用炮轰的办法轰苇泊,人们被迫分散。翠兰自己潜回村里,化名寄住在一位王姓大娘家,打算继续秘密活动。 真正的转折,来得很突然。 “伙会儿”用“现在不抓人了”的谎话骗翠兰的父亲回家,又让他劝翠兰回来。老人老实,以为真能平安,就劝女儿别在外头受苦。翠兰回到家,当晚就被捕。 12月25日,她被押到敌人的据点。敌人以为她是个年轻姑娘,吓一吓就能招供。但他们没想到,她早就把生死放下了。 “是不是共产党员?” “当然是,不然你们会到处抓我?” “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为了穷人翻身,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为了共产主义。” 敌人问干部在哪儿、物资在哪儿,她只说:“不知道。” 敌人用尽酷刑——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烙铁烫身;竹签钉进指缝;火烧头发……她昏过去,又被泼醒,嘴里还是那三个字:“不知道。” 他们把她父亲和奶奶抓来劝降,她强忍眼泪说:“回去吧,我不会给咱穷人丢脸。” 临刑前,敌人吊她在屋檐下示众,剥去衣服,用冰水泼。放下时,她已经冻得无法行走,耳朵和几根手指在摔落时掉在地上。 敌人问:“疼不疼?” 她笑了:“共产党员不怕疼。” 让她下跪,她说:“死不可怕,但绝不跪在土匪面前。”她还对同时被捕的四位同志喊:“咱们死得值,将来会有人报仇!” 走向刑场时,她昂着头,对乡亲们喊:“我什么也没说,我死得光荣,天下是咱们的!” 最后一刻,她高喊:“共产党万岁!”然后倒下。那一年,她才18岁。 王翠兰牺牲后,老王庄子的人久久不敢提她的名字——不是忘了,而是怕刺激到老人。可在村民心里,她永远是那面旗帜。 2004年,王翠兰烈士陵园被定为唐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0年,她被评为唐山百年十大女杰。每年三八节、清明节,当地都会有人去献花。 如果你去曹妃甸的滨海镇,可以在纪念碑前多站一会儿。碑下安眠的,是一个18岁的姑娘,她的青春早已化作那片土地上的风。 她的名字,值得被一遍一遍地念出来—— 王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