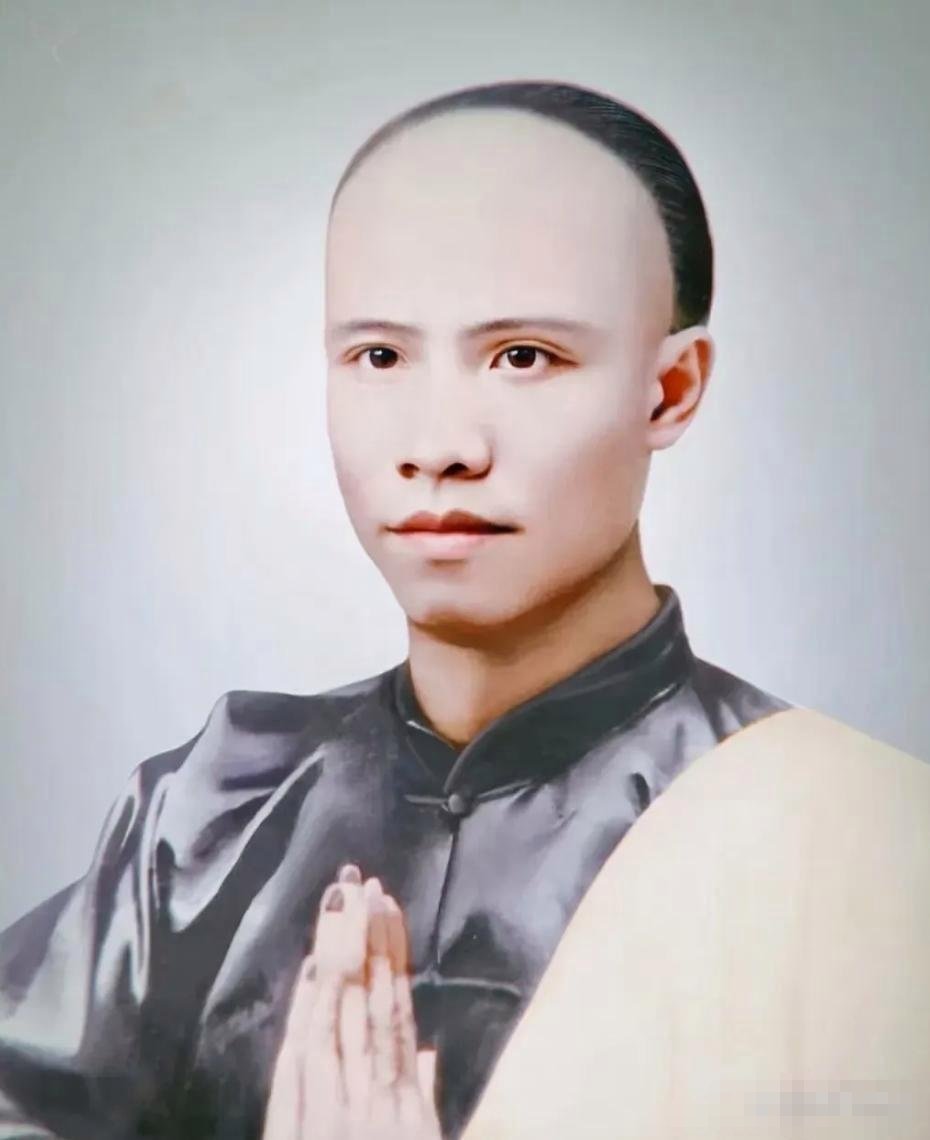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1385年,书生黄子澄上京赶考,会试、殿试都考了第一,眼看就要封状元了,朱元璋突然问道:“你多少岁了?”黄子澄回答:“学生34岁”。
朱元璋听闻,微微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黄子澄,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猜不透皇帝心里在想些什么。“34岁……”朱元璋缓缓开口,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朕看你才学确实出众,只是这年纪,略显稚嫩啊。”
老太监端着木盘的手微微发抖,盘子里本该放状元金花红袍的,这会儿却空荡荡的。黄子澄跪在青砖地上,额头贴着冰凉的砖缝,后背的官服早被冷汗浸透了。殿角铜鹤香炉里飘出龙涎香,混着新科进士们急促的呼吸,凝成一片令人窒息的雾。
屏风后头传来窸窣声,几个蓝袍小官缩着脖子咬耳朵。“三十四还嫌小?我考了二十年才中个同进士!”“嘘——你懂什么,听说前日工部那个贪墨案……”话音未落,御前侍卫的刀鞘已经磕在廊柱上,金銮殿里又死寂一片。
朱元璋站起身,十二章纹的龙袍扫过丹陛,腰间玉带上的金镶玉晃得人眼花。“来人,把前日八百里加急的折子拿来。”老太监捧着黄绸包袱过来时,黄子澄的膝盖已经跪得发麻,他盯着皇帝靴尖的云纹,听见折页哗啦响动的声音。
“浙江道御史弹劾两淮盐运使私贩官盐,你怎么看?”朱元璋突然把折子往地上一扔,黄纸黑字正落在黄子澄眼前。新科进士们倒抽冷气,谁不知道盐政是皇上的逆鳞,去年才剥了三个四品官的皮。
黄子澄的指尖触到冰凉的笏板,掌心汗湿了竹纹。他想起进京时在扬州渡口看见的盐船,桅杆上挂着官灯笼,舱底却压着私盐。“回陛下,学生以为当查官仓存盐数目。”他咽了口唾沫,青砖缝里渗出的寒意顺着膝盖往上爬,“官盐出库要盖三道戳,若数目对不上,必是戳印出了问题。”
龙案上的宣德炉"当啷"晃了下,朱元璋扶着桌角往前倾身:“接着说。”
“私盐贩子能打通关节,无非钱财开路。可官印在谁手里?必是仓场大使、主事、监运三人中有人私刻印章。”黄子澄额角青筋直跳,他闻到折子上沾着的朱砂味,“学生斗胆,请陛下着人查验盐引存根,真印朱色透纸背,假印浮于表面。”
丹墀下有人"咚"地栽倒了,两个锦衣卫架着个绯袍官员往外拖,乌纱帽滚到黄子澄脚边。朱元璋忽然大笑,震得梁上灰尘簌簌往下落:“好个查印不看人!朕倒要看看,你这双眼能不能辨忠奸。”
三天后,快马从扬州带回三枚铜印。黄子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真印浸在朱砂泥里按下去,纸背透出鲜红的"淮"字。假印按的文书,红印子只浮在纸面上,像抹了层胭脂膏子。
朱元璋摩挲着真印章上的缺口——那是他当年亲自用刀刻的记号。“黄子澄,知道朕为何嫌你年轻吗?”他甩开龙袖站起来,十二旒冕上的玉珠晃成一片,“三十四岁就能看透这些把戏,等你五十四岁,岂不是要把朕的龙椅都看穿了?”
黄子澄刚要跪,却被老太监托住胳膊。“着黄子澄任翰林院修撰,赐探花及第。”圣旨念完,金花红袍终于端了上来,只是状元冠换成了银簪花。后来有人听说,那天退朝后皇帝单独留下黄子澄,扔给他一摞空白的盐引:“把这些都填满,错一个数,朕送你回老家种田。”
二十年后的应天府,已经成为帝师的黄子澄站在奉天殿前。朱允炆追着问他:“先生当年真不怕死?”他摸着官袍补子上的孔雀纹,想起那晚宫灯下填盐引时手抖洒了的朱砂——红得就像第一次面圣时,金銮殿里的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