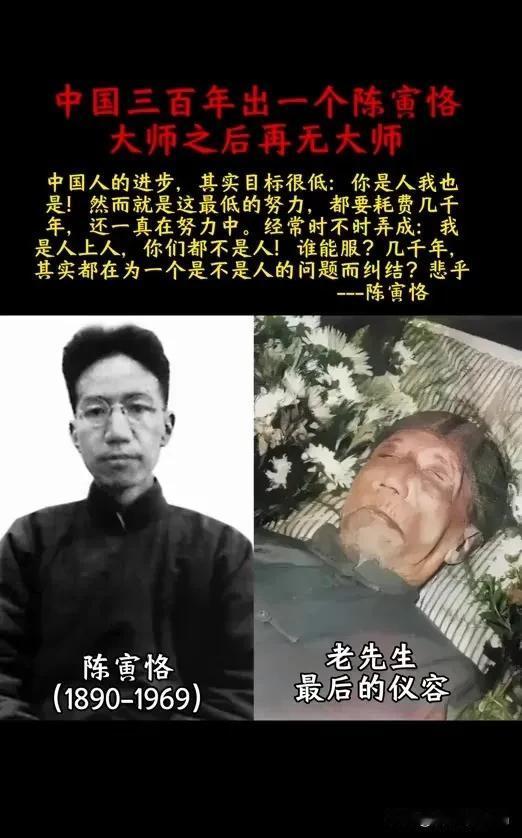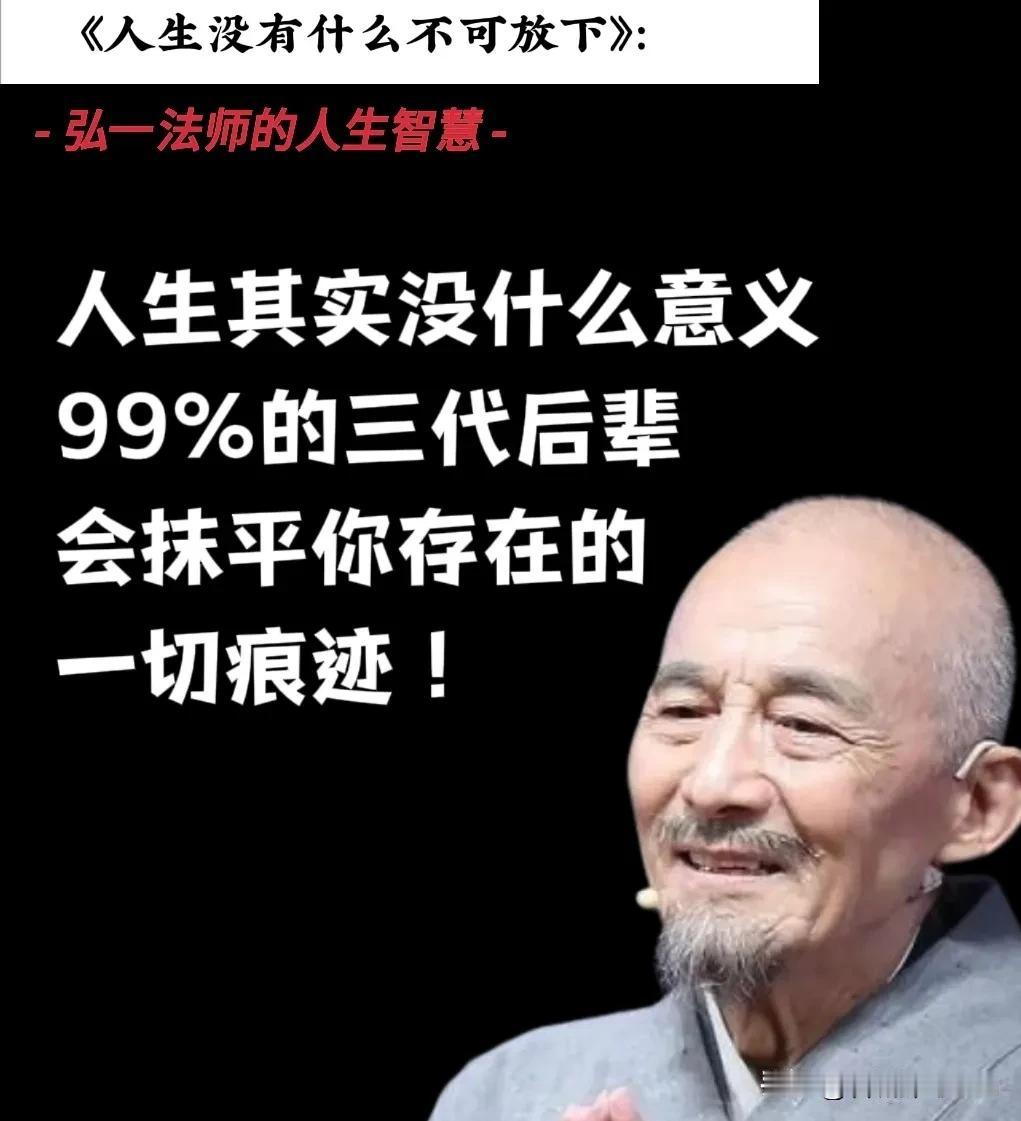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就是钱穆,江苏无锡人,打20岁站上小学讲台起,这辈子就没离开过“中国历史”这四个字。 青年时在无锡中学教书,课间总被学生围着问“古人为什么要修长城”“唐宋的百姓怎么过日子”,他从不拿课本照念,而是带着学生在当地的古桥、旧宅里找历史痕迹,说“历史不是纸面上的字,是活在土里的魂”。 40岁那年,他辗转到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物资匮乏,他在云南蒙自的破庙里,就着一盏油灯写《国史大纲》,手稿改了七遍,扉页上那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后来成了无数史学人治学的初心。 1950年,钱穆从香港辗转到台湾,彼时他的《中国通史》已在学界传开,蒋介石听闻后,特意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拨给他居住、治学。这一住就是四十年,素书楼的庭院里种着他亲手栽的桂树,每到秋天满院飘香; 书房的书架从地面堆到天花板,每本书的天头地脚都写满批注,有的是补充史料,有的是随手记下的感悟,连《论语》的空白处都贴着他剪的报纸片段——那是他看到的两岸民生新闻,想日后若有机会,能补进自己的研究里。 谁也没料到,1990年春,台湾“教育部”突然发了封函,说素书楼是“公有财产”,要求他一个月内搬离。当时钱穆已95岁,眼睛半盲,耳朵也背,日常靠学生读报、念史料给他听。 接到通知那天,他没发火,也没抱怨,只是让学生扶着自己走到书架前,枯瘦的指尖慢慢划过《国史大纲》的封面,声音发颤:“我在这里写了一辈子中国史,怎么就成了占公家的地方?”学生们要帮他申诉,他却摆了摆手,说“治学的人,不跟人争房子”,语气里满是无奈。 最终他还是搬了,搬到台北市区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出租屋。墙皮斑驳脱落,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以前在素书楼能摆下四张书桌的空间,现在连他的砚台都只能放在窗台上。 他再也没力气像从前那样清晨打太极,每天就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偶尔会突然问学生:“无锡的梅花开了吗?” 他离开故乡时,家门口的老梅树每年腊月都开满白花,母亲总说“梅花落了,你就该回家了”,这个念想,他揣了四十多年。 他很少在人前提乡愁,却在晚年的日记里写“夜梦江南,晨起泪湿枕巾”。大陆的亲人曾想托人带些故乡的泥土给他,让他闻闻熟悉的味道,可当时两岸往来不便,东西辗转几次,最后还是没送到他手上。 他最常跟学生说的,是年轻时在无锡古运河边看书的日子,“河水清得能看见鱼,岸边的茶馆飘着茶香,偶尔有船划过,船夫唱的调子跟史书里写的吴歌一样”,说这些话时,他浑浊的眼睛里会泛起光,像看到了远方的故乡。 搬去出租屋的第二个月,钱穆的身体就垮了。先是感冒引发肺炎,吃了药也不见好,后来连说话都没了力气。 弥留之际,他拉着学生的手,声音轻得像气音,反复念叨“把书收好,把中国史传下去”,从头到尾没提一句被赶出素书楼的委屈,也没说一句对谁的不满,只在最后问了句“能把我葬在能看见大陆的地方吗”。 1990年8月30日,他在睡梦中去世,床头还放着一本翻开的《论语》,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无锡老地图,地图上他老家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又圈。 人们总说钱穆是“史学大家”,却常忽略他骨子里的“中国人”底色。他治史不是为了钻考据的牛角尖,而是想让后人明白,中国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年代和事件,而是一代代人对家国的牵挂、对文化的坚守。 95岁被赶出住所的窘迫,至死没能回故乡的遗憾,都没能磨灭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一个学者的个人遭遇,而是那个时代两岸分隔的缩影——再深的学识,再高的声望,也抵不过对故土的牵挂,抵不过“想回家”的念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