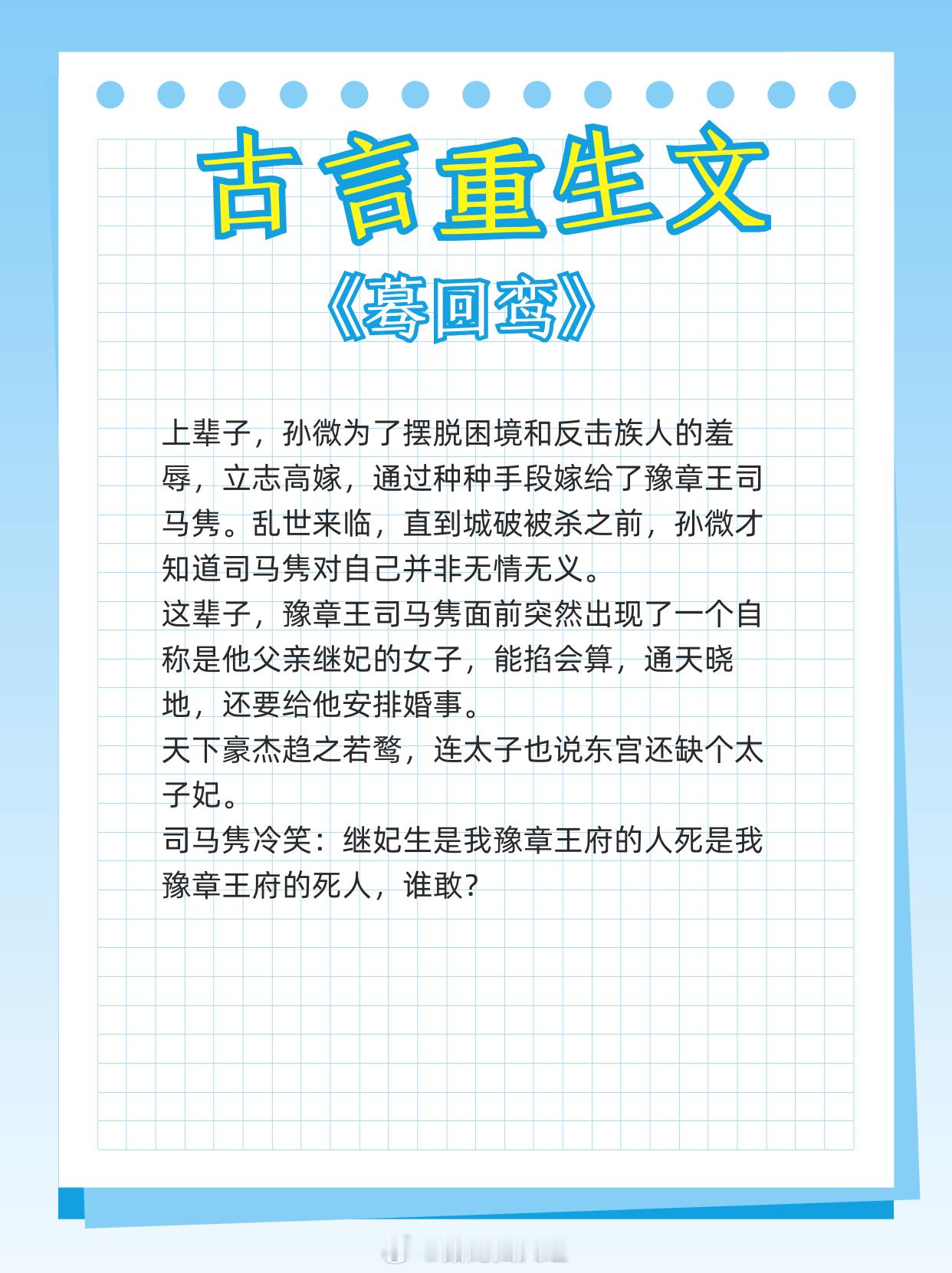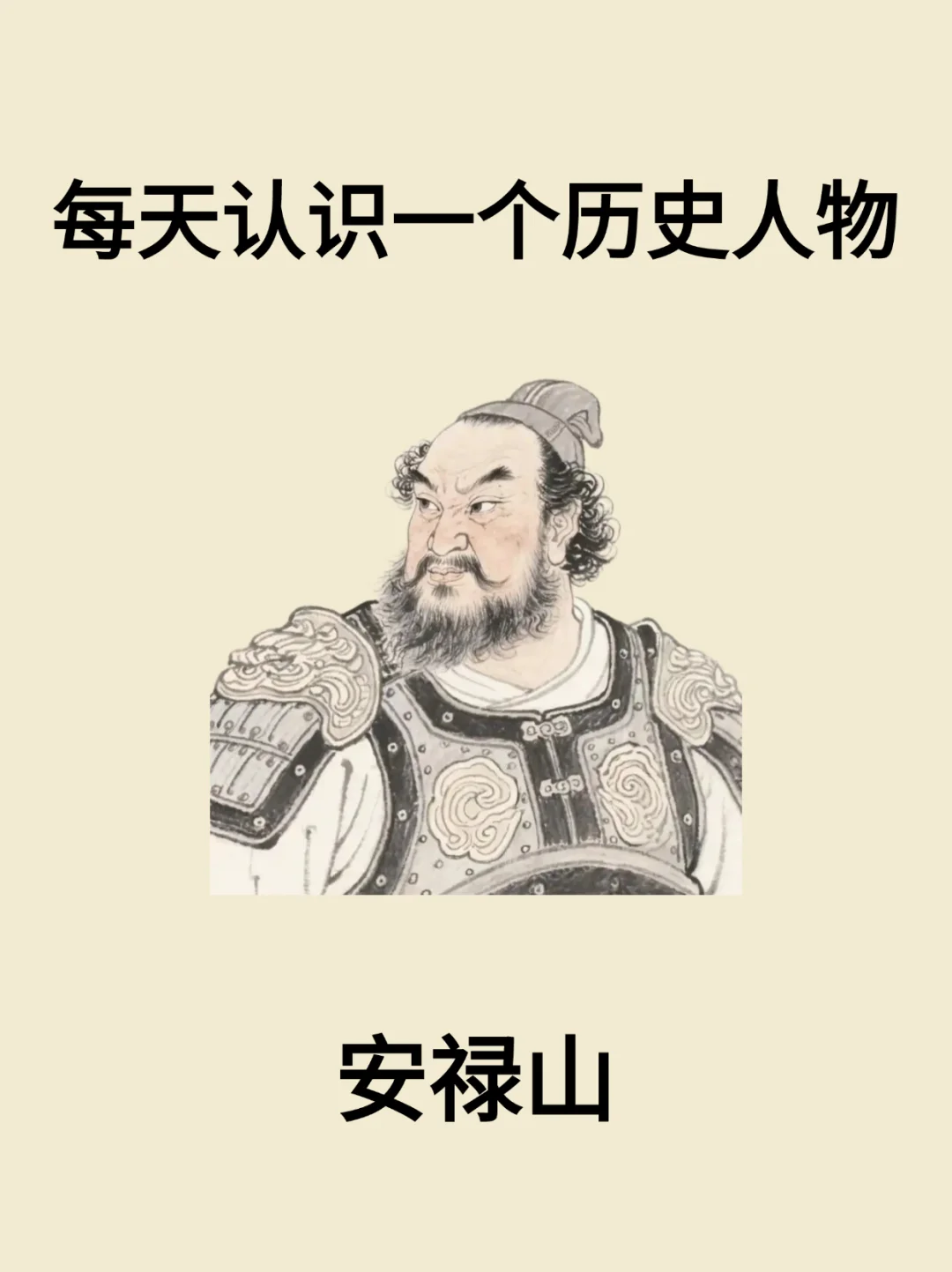“再生女儿我就纳妾!”这话一出口,朱环佩肚子都紧了半分。可老天像是故意捉弄她,孩子还真是个女娃。她刚落泪,婆婆却说:“别哭,我有办法。” 1900年,福建一个叫毛家的大宅子里,朱环佩第三次临盆。 产房外头,丈夫毛华东的脸比锅底还黑。 他不是等孩子,他是在等答案,到底是个儿子,还是个“赔钱货”。 朱环佩不是没给毛家生过男孩。 早在两年前,她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取名都取好了,可惜活不过周岁,没了。 从那以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毛华东的脸色也一天天冷下去,连个正眼都不肯给她。 “要是再生个女的,我就纳妾!”毛华东把话撂得清清楚楚,话音一落,朱环佩心里就凉透了。 那一年朱环佩才26岁,出身书香门第,嫁来毛家时是风风光光的少奶奶。 可惜毛家早就不是当年的毛家,生意垮了,地也卖得七七八八,靠着几亩薄田和祖宅撑门面,连过年都要借米。 偏偏这个时候,孩子来了。 产婆出门那一刻,毛华东眼都红了,“男的还是女的?”他不问母子平安,他只问这个。 “一个女孩。”产婆声音不大,但字字扎心。 朱环佩抱着孩子,眼泪止不住。她知道,自己这辈子的日子算是到头了。 可这时候,婆婆悄悄进了产房,手里还抱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眉头紧皱:“环佩,别哭了,这事我来解决。” 那一晚,毛家对外放出消息,喜得一对龙凤胎,男孩取名毛承恩,女孩则被“送去亲戚家养”,说是“命硬”。 谁都没多问,只有朱环佩知道,那个女孩是她亲生的第三个女儿,而所谓的“儿子”,是婆婆从乡下一个穷亲戚手里“换”来的。 她不敢拒绝。 不是因为没骨气,是她知道,只要这个“男孩”在,她就还有个位置。 毛家的香火不断,她才不会被扫地出门,连个名分都保不住。 可问题来了,孩子太弱了。 毛承恩从出生起就体虚多病,三天两头发热咳嗽。 朱环佩日夜照顾,药汤一碗接一碗地熬,可孩子还是没熬过第一个冬天。 那一天,毛家守灵堂,毛华东眼圈发红,却一句话没说。 三天后,他带回了一个年轻女人,叫阿香,说是“亲戚家的姑娘,来帮忙照顾家务”。 不到半年,阿香挺着肚子住进了正房。 朱环佩彻底明白了,男人说纳妾,从来都不是吓唬人的。 她身子一天天虚,心也凉了。 阿香生的是个儿子,毛华东像变了个人,整天围着孩子团团转。 朱环佩的两个女儿,一个送去了外地亲戚家,说是“养着”,另一个干脆没人提起。 冬天到了,朱环佩一个人睡在西厢房,炭火也不给烧,连个下人都没人伺候。 她不吵不闹,只是夜夜梦见那个被送走的小女儿,哭着喊她“娘”。 她熬了下来,只为了那两个还活着的女儿。 大女儿毛彦文最聪明,从小读书识字,笔下生花。 朱环佩省吃俭用,偷偷卖了嫁妆给她换来学费。 她从私塾考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来还出国留学。 再往后,她成了民国女子教育的旗手,写文章、演讲、办学,为了让更多女孩读书识字,拼尽全力。 女儿回来时已是民国初年,穿着西式长裙,头发剪得利落,一进门就把母亲接走了。 “娘,跟我走吧,咱不在这儿受这没来由的气。” 朱环佩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终于有人能护着她了。 毛家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毛华东的儿子早早病死,阿香带着另一个孩子改嫁去了南方。 朱环佩的晚年,是靠着毛彦文照料过的。 她住在北平一间阳光很好的屋子里,身边摆着女儿送的钢笔和书,她不识字,但她摸着那些东西,总觉得心里暖。 有人说她命苦,可她不这么看。 “我养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儿,这日子,不亏。” 故事讲到这,你可能觉得心里堵得慌。可那时候的女人,哪一个不是在夹缝中求生? 朱环佩的悲剧,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女人的缩影。 可也正因为有女人像她一样撑下来,咬牙把女儿养大,才有后来毛彦文那样的人,敢站出来说:“女子也能顶半边天。” 这不是反转,这是传承。 她没能为自己争口气,但她教会了女儿如何为母亲争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