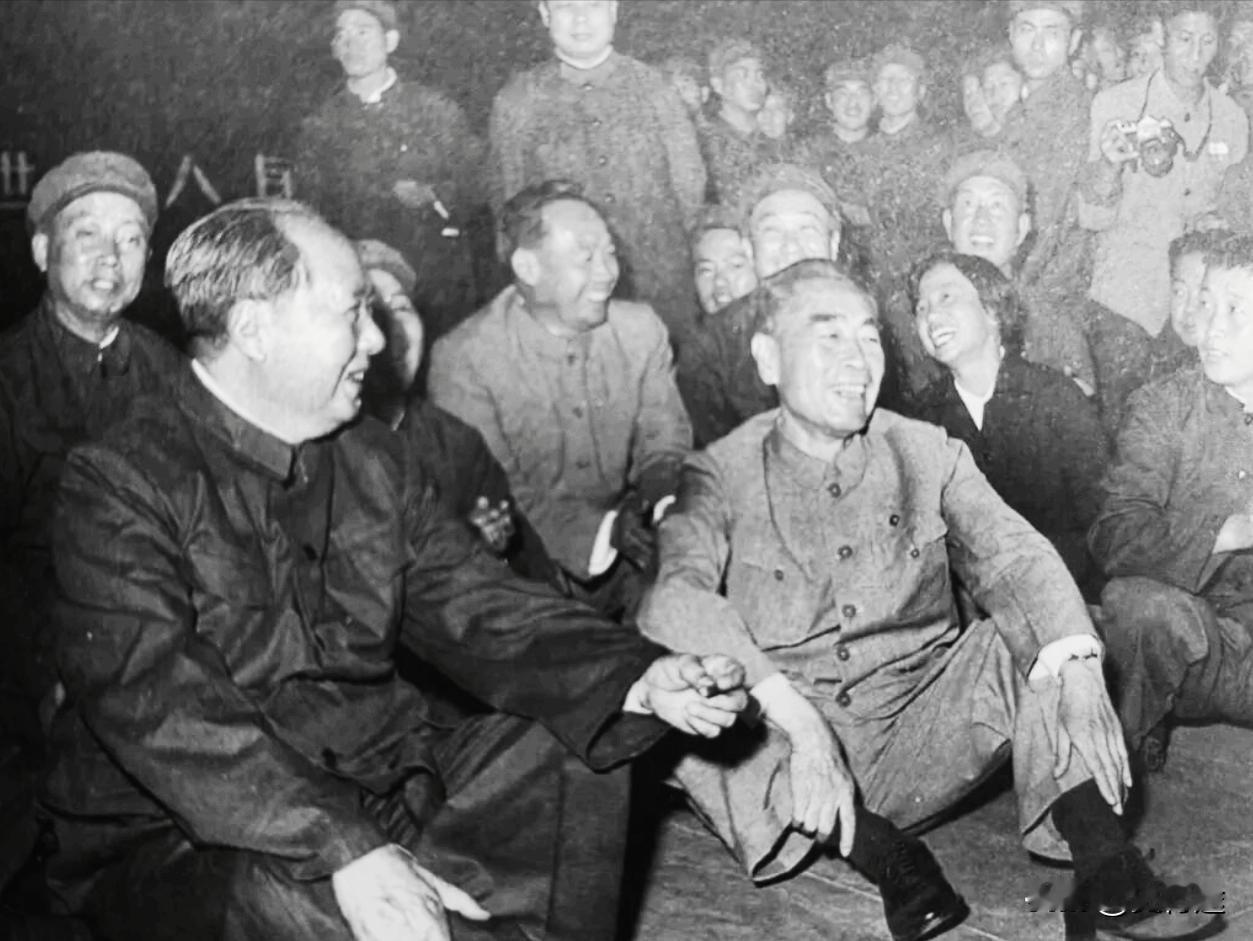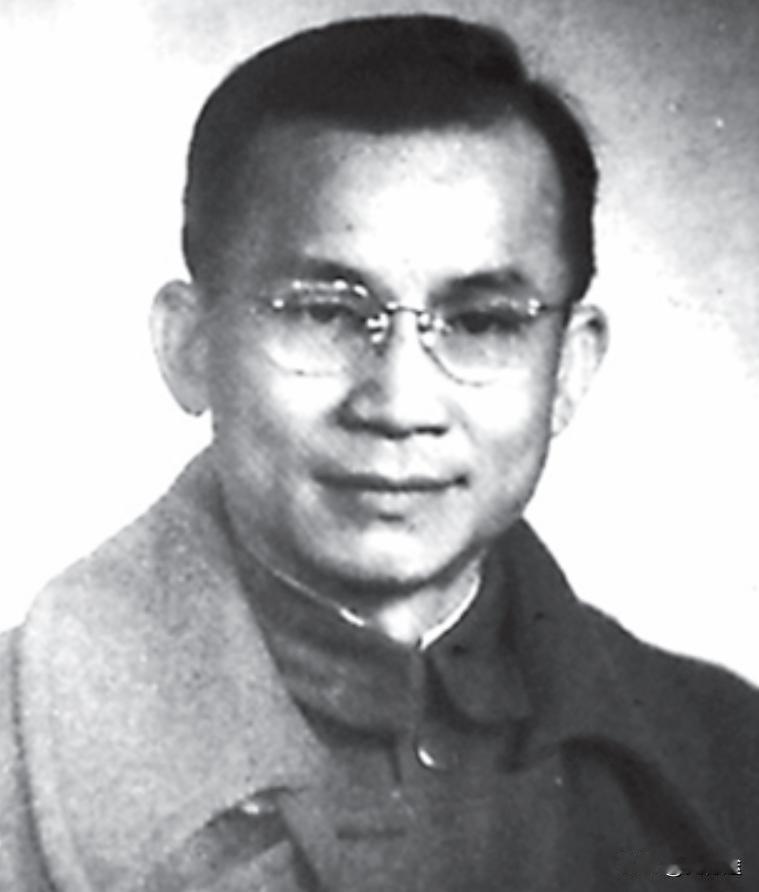中国穷人,与世界穷人,都要感谢毛主席,中国现在的太平盛世也要感谢毛主席所立的威! 韶山那地方,不大,就是几个山头绕着几口水塘,一年四季湿漉漉的。 早晨鸡还没叫,人就起了,田边路上踩出一道道水痕。毛泽东小时候,就长在这样一块地方。 他家不算穷,可也富不到哪儿去,家里种田,也做些小买卖,日子要精打细算。 他母亲常管不住手,老是从米缸里抓米给隔壁的穷人送去,送完回家还得挨父亲一通骂。可她就是改不了这毛病。 他小时候干活不比别人少六七岁就喂猪、放牛、拾粪,十多岁那几年,天天下田,犁耙样样来。 他跟家里请来的长工干活,有时还抢着干。 不是争气,是习惯了。他看惯了山里人一辈子窝在土地上,靠天吃饭,靠力气换口饭吃,哪天人一倒,整个家就跟着垮。 他对穷人的苦,不是听来的,是看多了、碰多了。 十四岁那年,邻居李南华家租了他家两亩田,一年到头收成不好,粮不够吃。 他爹让他去收租,他进了李家,没张口,转身回了家,回头又从家里仓里抓了一把谷,假装是李家交上来的。 他爸问谷子怎么这么多,他没回,只说:“交了。” 那会儿人讲面子,不问太细,事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次,他家买了头猪,跟人讲好价,收了定金。没几天猪价涨了,卖猪的人又想悔约。 那农民说得也实在:“你家不差这几个钱,我家差。”他就回家跟爹说不买了,把猪退回去了。那时候没人教他“同情弱者”,也没人喊“人民立场”,就是看不下去,觉得不合适。 他小时候见过不少事,最扎心的,是长沙那次饥荒。 人饿得上街求粮,衙门不开口,倒是开了枪。人死在街头,头挂在城门。那年他十七,事发生后,好几天不说话。 那之后,他开始琢磨:人要活,得靠自己。 后来读书,也不是奔着当官去的。 他读《新青年》《民报》,也写文章,但写得不空,写的都是人,苦人,老实人,倒霉人。 他嘴上不说什么主义,可做的事,早就有了方向。 1927年他做农民调查,带着几本小册子,跑村串巷。农民说话他听,地主说话他也听,最后写了一大本。他不讲道理,只说你看,地是谁的,粮是谁种的,税谁交的?你不让人翻身,人家迟早反你。 那年他写报告,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候很多人不爱听,说他话冲。但村里人听得明白。他说话不转弯,也不绕。他知道,老百姓不怕穷,就怕没盼头。 后来到了瑞金,开苏区大会。别人讲国家、讲世界,他讲盐、讲米、讲衣服、讲路。他讲得细,有人觉得没劲。可他就是要讲这些。他说你不讲这些,革命谁跟你干?人是要吃饭的,不是听报告的。 抗战时期,他在延安,山里冷得厉害。那时候物资紧,公粮重,老百姓日子难。有一天,边区征粮的事让人骂上了天。有人说:毛泽东咋还不被雷劈。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警卫紧张得要命。他却说:“不查,得听。”第二天就开会,减租、减负、精兵简政。他说:“说空话没用,得让人真过得去。” 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听人说话。谁都行:农民、杂役、炊事员、修桥的、打铁的。他坐下来,一边听一边问。他常说:“我是学生。”人家笑他装,他就笑回去,说:“不听人话,怎么懂人事?” 1945年夏天,黄炎培来延安,问他:“中国怎么才能不走老路?朝代更替,亡来兴去。”他听完没急着答。想了一会儿,说:“我们找了条新路——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这话,他是掂量着说的。他知道政府怕的是民心散,不是敌人凶。 建国之后,他没变。还爱写信,爱问事。给家乡亲戚的信,一封封,问得细:“田种得怎样?学校开了吗?路修了没?”这不是作秀。真有人给他回信,说这说那,他也回。他说,老百姓的话才是真。 有一年春节,他去延安乡政府拜年,落座之后不说别的,只说:“今天我给你们拜年,你们给我提意见。”一开始没人敢说,他便笑,说:“不说,我们可没法改。”于是有人开口,说盐贵、衣难、娃读书难。他听完,点头,说:“记下来,看看能不能办。” 他和农民杨步浩的交情,几十年。杨帮中央种地,他知道后特地接见,两人一见面,聊得投机。后来杨生日,他托人送东西。毛泽东不讲这些场面事,但人情他记得住。谁帮过他,他都不忘。 他对毛岸英要求也严。孩子从苏联回来,他让他下乡,干农活。干到手上出血泡,他说:“你还没毕业。”不讲道理,只讲“去干”。 他常讲安泰,说:“共产党人像安泰,贴着地才有劲,离了地,就完。”这话说得不文气,但是真。他不靠理论过活,他靠人。他说:“穷人就是力量。” 老了,他还是一样。有人劝他多休息,他说:“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这不是演讲,是他真心话。他知道,穷人一哭,不是哭自己,是哭这日子没指望了。 他这一辈子,说到底就认一件事: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谁就能站住脚。 别的都是虚的。制度也好,路线也罢,说得好听,做不到,百姓一走,全塌。 他的办公室,桌上常放着一张纸,写着“为人民服务”。字写得不漂亮,也不规整,但能看出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