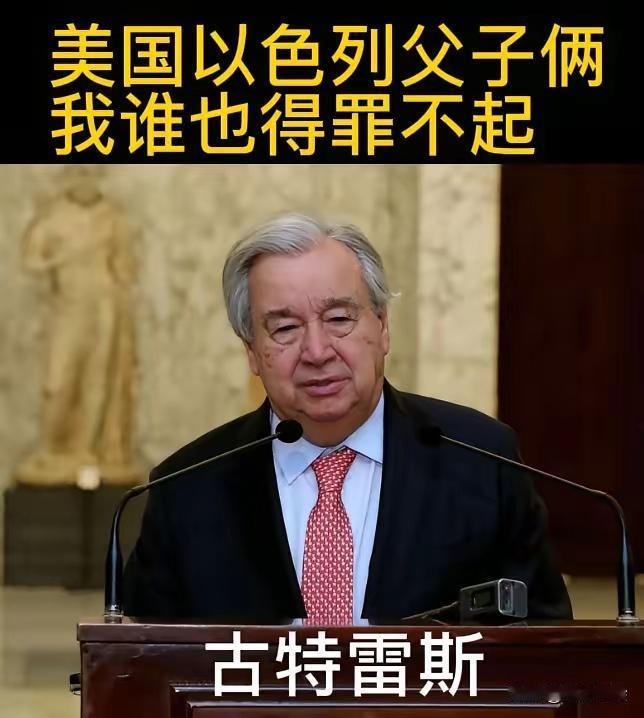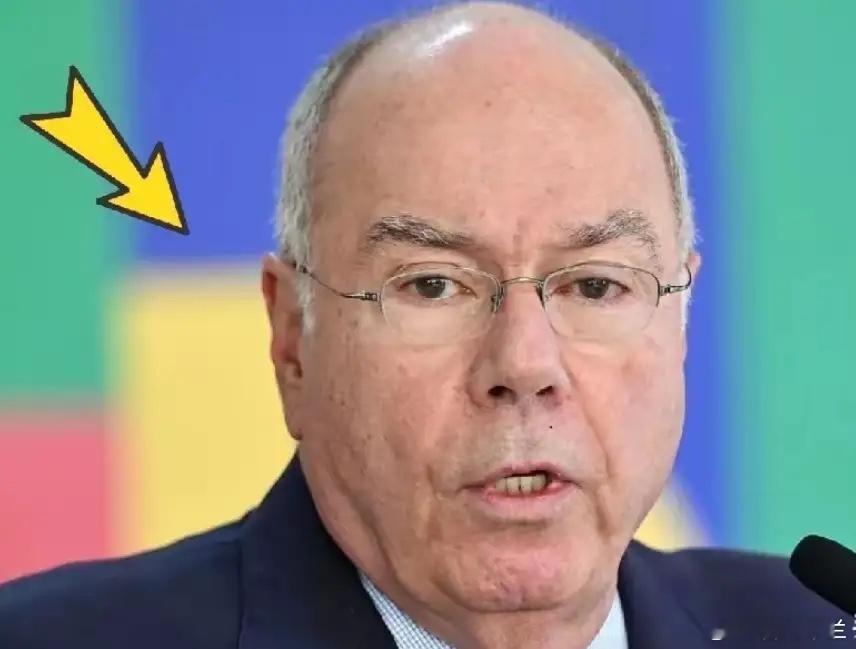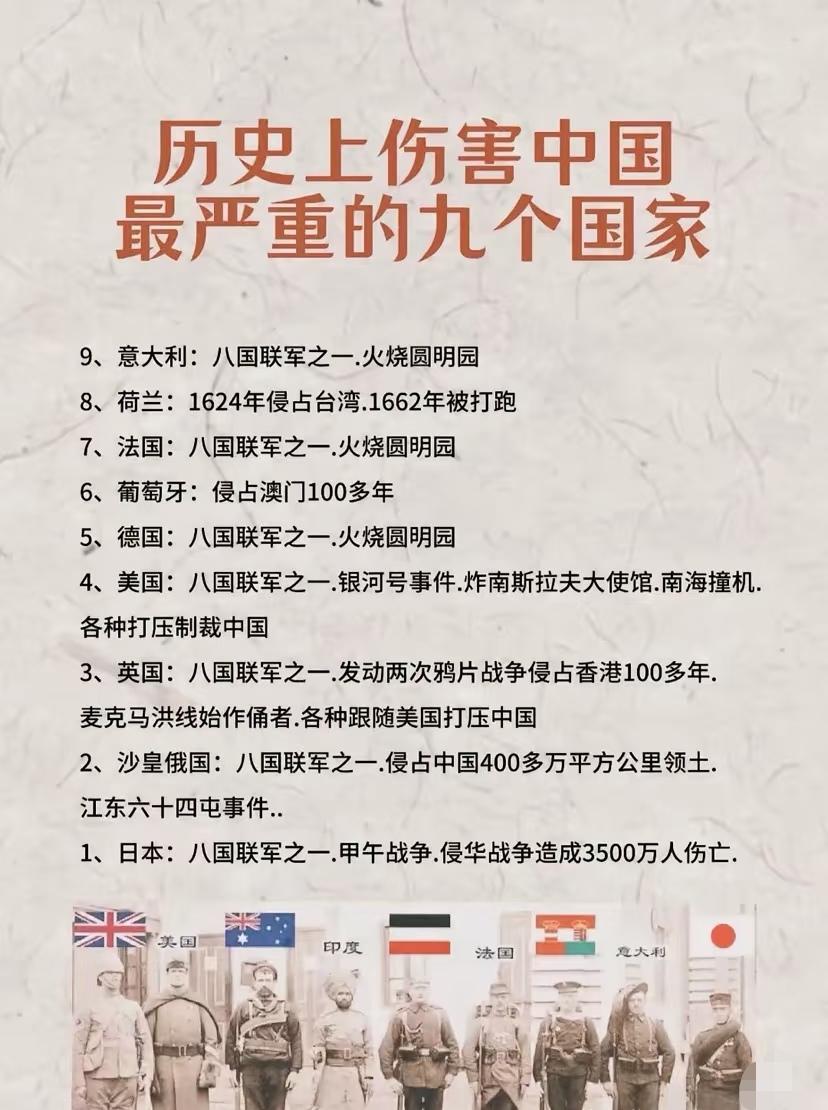联合国改革挥刀五常,取消否决权服从多数,中美罕见意见一致。在联合国即将迎来成立8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秘书长古特雷斯突然公开呼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 他指出,当今安理会的组成结构仍停留在1945年,与现代世界格局严重脱节。这不仅损害了其合法性,也在不断削弱其全球治理效能。因此,他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而在这些计划中,最具突破性的一点,就是对五常的一票否决权施加限制。他希望五常能放弃一票否决权。而在这个问题上,中美罕见地达成共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历史节点提出安理会改革方案,尤其针对五常否决权的限制倡议,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罕见的“共识”更显得耐人寻味。 然而,这场看似推进全球民主化的改革,实则暴露了国际秩序转型中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否决权制度的设计初衷并非为了特权固化,而是为了避免大国间的直接对抗升级为战争。 1945年雅尔塔体系下的“大国一致”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妥协:通过赋予五常特殊权力,换取其对国际秩序的责任担当。 这一机制在冷战期间客观上避免了美苏冲突演变为核战争,但其代价是许多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被政治博弈所绑架。 如今否决权遭遇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源于全球权力结构的演变。 五常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945年的50%以上降至如今的26%,经济总量占比也从60%下降至45%左右。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实与二战遗产制度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这种代表性危机使得安理会决议的道德权威持续流失。 中美在限制否决权问题上看似一致的立场,掩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考量。 对美国而言,支持改革意在通过“多数决”机制强化西方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其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人权等议题上推动“价值观联盟”的尝试正是此种逻辑的延伸。 而中国则更关注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这种共识的脆弱性在于:美国设想的“多数决”可能演变为新型集团政治,而中国主张的协商民主则需要克服效率低下的难题。 两国本质上都在试图塑造有利于自身理念的国际制度框架,这种深层目标的分歧注定会使改革进程充满变数。 安理会改革面临的根本矛盾在于:既要保持决策效率,又要体现代表公平;既要维护大国责任,又要防止权力滥用。 历史表明,单纯扩大安理会规模可能导致决策效率降低(如国联的教训),而完全取消否决权则可能促使大国另起炉灶(如1919年凡尔赛体系的崩溃)。 更具建设性的思路或许是建立“分级多数决”机制: 对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化等特定议题设置否决权激活门槛;同时建立区域代表轮值制度,使更多国家参与核心决策过程。 这种渐进式改革既尊重现有权力结构,又能逐步注入新的民主元素。 联合国改革本质上是全球治理范式转型的缩影。 在传统主权国家体系与新兴非国家行为体共存的背景下,单纯围绕否决权的争论可能忽略了更深层的变革需求。 数字治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正在产生超越传统安理会职权范围的全球公域治理需求。 这意味着联合国改革需要跳出“权力再分配”的旧框架,转向构建多层级、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体系。 安理会或许应该专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职能,而将发展、环境等议题交由经过改革的联大及其他专门机构处理,形成功能互补的制度生态系统。 古特雷斯的改革倡议揭示了一个深刻悖论:既要破除大国特权,又需要大国承担特殊责任; 既要体现国家平等,又要承认权力差异的现实。 这种二元对立如何调和,将决定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安理会真的取消否决权,是否会导致大国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或小多边机制解决问题? 联合国是否可能因此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若维持现状,日益激化的代表性危机是否会最终侵蚀整个国际秩序的合法性? 这些悬念不仅关乎制度设计,更关乎人类能否在21世纪构建真正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 在霸权更替与全球挑战叠加的历史转折点上,联合国改革正在成为检验人类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公开权威信源深度分析,坚持客观立场,旨在促进理性讨论。原创内容结合AI辅助完成仅供交流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或决策建议。信源、图片均来自网络,若存在争议、图片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作者,将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