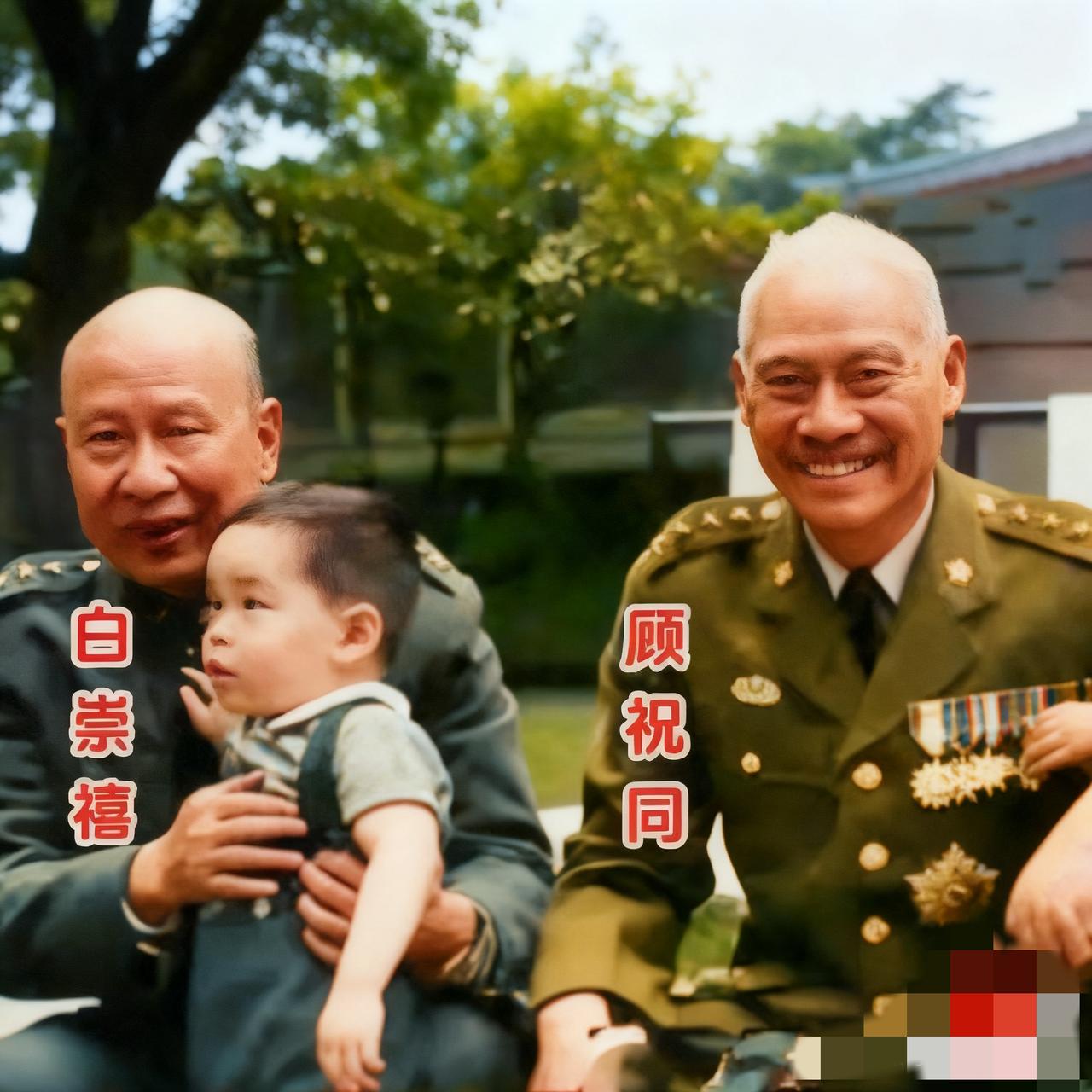1980年,开国上将陈士榘与妻子范淑琴经法院调解离婚,为这段始于1941年的革命婚姻画上句号。 2010 年范淑琴临终前,手指反复摩挲那张泛黄合影,将照片贴在胸口。 照片里 1941 年的她扎着麻花辫,陈士榘穿着军装,窑洞烛火映着两人的脸;而 1980 年离婚协议上,两人的签名隔着几厘米,却像隔了半生的疏离。 谁能想到,这段始于《黄河大合唱》的革命爱情,终在岁月里磨出了遗憾的棱角。 1938 年冬,晋察冀边区文工团演出,16 岁的范淑琴站在土台上开口。 《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刚起,台下画图的陈士榘就抬起了头,眼神定在她身上。 演出结束后,他主动找文工团负责人:“这姑娘嗓子好,能不能让她多参与宣传?”那时的他 32 岁,是历经长征的军级干部,却在听到清亮歌声时,漏画了工事图纸的一笔。 范淑琴后来听人说 “陈司令夸你”,脸一红,心里悄悄记下了这个名字。 1940 年春,范淑琴调到军区机关学电台,刚好分到陈士榘所在的部门。 第一次见面,他递来一本笔记:“这是我整理的通讯要点,你先看着。” 笔记里夹着张纸条,写着 “多穿点,边区风大”,范淑琴攥着纸条,手心发暖。 有次她值夜班发烧,陈士榘冒着风雪送来退烧药,坐在床边守到她退烧才走。 同事打趣 “陈司令对你上心”,她嘴上否认,心里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1941 年秋,组织找范淑琴谈结婚的事,她第一反应是 “我还没跟他说过几句话”。 可当陈士榘站在她面前,说 “革命需要稳定的家,我会对你好” 时,她点了头。 窑洞婚礼简单得只有几根蜡烛,对着毛主席像鞠躬时,他悄悄握了握她的手。 婚后第三天他就上了前线,临走前塞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是件新做的棉衣。 范淑琴抱着棉衣哭了,不是委屈,是知道这份感情要跟着战争颠沛流离。 1943 年,范淑琴怀孕,陈士榘难得回来一次,却只待了两天。 他坐在炕边,笨拙地给她削苹果,说 “等打完仗,我陪你看黄河”;她摸着肚子笑,说 “孩子出生了,你得教他画画”,两人的话里满是憧憬。 可第一个女儿出生后,赶上日军 “扫荡”,孩子在转移中夭折,范淑琴抱着空襁褓哭。 陈士榘赶回来时,只看到她红肿的眼睛,他没说话,只是把她搂进怀里,肩膀在抖。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两人终于有了安稳的家,陈士榘却成了 “不回家的人”。 他忙着当工程兵司令,修铁路、建导弹基地,经常几个月不沾家。 范淑琴把家打理好,还参与两弹基地建设,拿到勋章时,她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他。 可等他回来,只匆匆看了眼勋章,说 “好好保存,我明天还要去工地”。 她准备好的话堵在喉咙里,看着他疲惫的背影,把委屈咽了回去。 1955 年陈士榘授上将军衔,典礼结束后,他牵着范淑琴的手拍照。 照片里她穿着旗袍,他穿着礼服,笑容里满是骄傲,这是两人唯一一张正式合影。 那天晚上,他难得没谈工作,跟她聊起当年边区的日子,说 “还是现在好”。 范淑琴以为,安稳日子能让两人的感情更浓,可没过多久,他又扎进了工程里。 她偶尔会翻出那张合影,对着照片叹气,觉得两人离得越来越远。 1966 年夏,范淑琴被关进秦城监狱,每天最盼的就是听到陈士榘的消息。 有次狱友说 “你丈夫没来看你”,她摇头说 “他忙,他会来的”,心里却没了底。 直到有天,她听到看守议论 “陈司令跟她划清界限了”,她靠在墙上,眼泪无声地流。 1976 年范淑琴平反回家,推开门看到陈士榘,第一句是 “你为啥不救我”。 他坐在沙发上,头埋在手里:“我没办法,那时我自身难保。” “没办法” 三个字,成了两人之间的一道坎,之后的日子里,争吵成了常态。 有次儿女劝和,范淑琴哭着说 “我在牢里想他想了那么久,他却不管我”;陈士榘看着她,眼里满是无奈,却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进了书房。 1980 年 4 月,法院调解室里,陈士榘拿出 3000 块钱:“这是我全部积蓄,你拿着。” 范淑琴看着钱,又看了看他,签字时手在抖,却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走出法院,他想送她回家,她摇头说 “不用了”,两人朝着不同的方向走。 离婚后,陈士榘偶尔会问儿女 “你妈过得好不好”,却从没主动联系她;范淑琴把合影锁在抽屉里,只有过年时才拿出来,看一眼就放回原处。 如今,陈士榘的事迹被写进史料,他建的导弹基地仍在发光;范淑琴的故事,被儿女讲给孙辈听,说起那段始于歌声的爱情,满是唏嘘。 这段革命年代的婚姻,有过温暖的瞬间,也有过无法弥补的遗憾,终究成了岁月里的一段印记。 主要信源:(江苏文明网——跃马扬刀战倭寇——滨海抗战中的陈士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