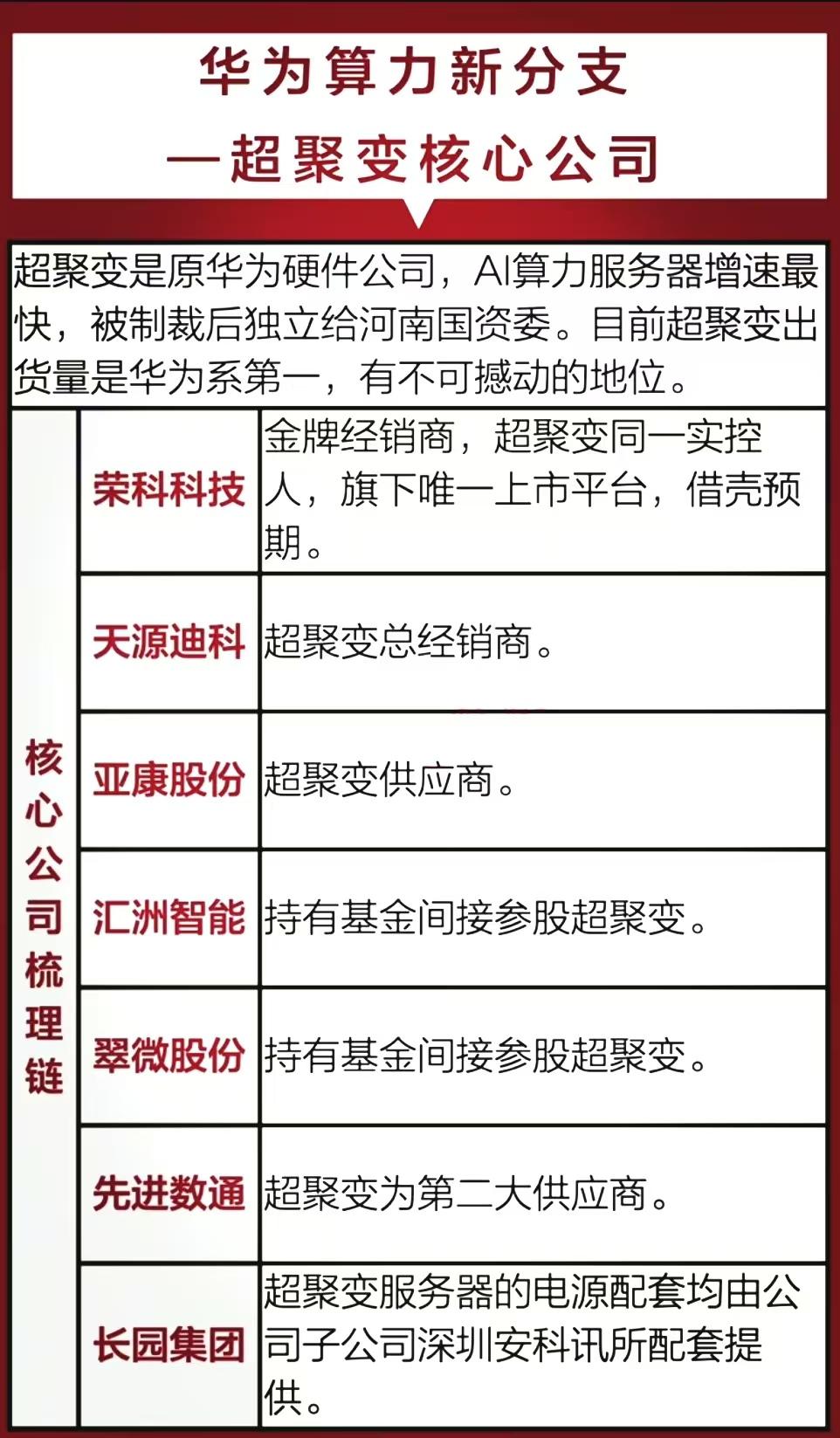或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沉默的荣耀。我是朱枫。在此之前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出身名门,千金,却选择为信仰赴汤蹈火,临危受命,孤身赴台,最后却事故无存。那一湾浅浅的海峡,隔开的不仅是我与故乡的牵挂,更是万千中华儿女归家统一的夙愿。一九零五年,我生在宁波镇海的大于殇家庭,母亲总说,喃喃是喊着金汤匙出生的。本以为我这一生就是富家小姐的普通轨迹。可一九二五年五卅那天,宁波女子师范的操场上,学生们喊着,还我同胞的声音震得我心口发颤。那刻突然觉得,比起当交小姐,我更想为那些受难的人做点什么。后来去上海学书法。沙孟海先生说,我字里藏着任气,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任气会陪我闯过多少难关。二十二岁远嫁去奉天,丈夫是炮兵工厂的技师。看起来,我本该将柴米油盐的安稳日子过下去。可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炮声炸响,我攥着给孩子新秀的虎头鞋突然清醒,我要是碎了,在安稳的家也护不住。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把裴家的金镯银簪全当了,换成钱给新知书店买纸印书。有人说我疯了,放着福,不想要去沾革命的,便可看着那些印着抗日救亡的小册子传出去。我心里比传绫罗还踏实。三十八岁那年,去重庆珠江食品店工作,表面是做生意,实则给组织当联络点。一九四四年转去上海,同风行,没几个月就被抓进监狱。日本人的鞭子抽在背上,烙铁烫的皮肤冒烟。问我书店同志的下落,我咬着牙没松口,一旦我松口,不仅我自身难保,同志们也会被一网打尽。后来组织想办法把我救出来,我便随即入了党。一九四八年调去香港和众贸易公司。看着窗外的渔船,总想起震撼老家的海。此时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一九四九年夏天,组织找我,要派我去台湾当交通员,加入东海小组,对接吴石先生。情报关乎统一,我没犹豫就应了。临走前偷偷去学校看孩子,他们在操场跑着笑,我没敢上前,只把模样刻进心里,就像吴石将军说的,这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到了台湾,我改明朱晨芝每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终于四年大年初二,我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在舟山接到撤退指令,此时距离家乡镇海就只有六十公里了。可特务突然冲进来手铐铐住手腕时,我只可惜差一步就差一步。我就可以回家了。原来是蔡孝乾叛变了,他把我们整个东海小组都招了出来,已经关制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吴什,还有陈宝仓、聂曦全部被捕在台北监狱,他们对我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可我要是嵩口多少同志要掉脑袋,后来趁看守不注意,我吞了藏在衣领里的金块。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家了。既然如此,那么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可是不久,我就被他们抢救回来了。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他们压我们四人去马场厅行场,阳光很暖,像震海的太阳。枪决之前,我拒绝蒙眼睛,我要看着祖国的方向。枪响时,我笑着心里想着女儿朱晓峰和儿子朱明,别怪妈妈,妈妈是为了让你们和更多孩子能安稳过日子。牺牲后,我的尸骨无人认领,想来也不会有人敢领吧。我的儿女无法跨越海峡,无法认领我的骨灰,便在南京明孝陵宝顶山给我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无悲无目无名字。而此时,我的骨灰早已经被丢进阴暗潮湿的那古塔编号两百三十三,名字写成朱占文。短期出现在二零零零年,山东话报出版社登了我零星的照片,穿碎花旗袍,攥着拳头,目光坚定。而你们看到这张照片,想要寻找母亲遗害的心情,再次点燃二零零三年照片的发布者、台湾学者徐宗懋表示,愿意帮着四处找线索,可是一直没进展。直到二零零九年,两岸早已通伤上海老人潘臻赴台寻父,在殡仪馆名册上看到,朱占文,觉得是朱成之的误解。半年后,殡仪馆工作人员在纳古塔里从六百多个无主骨灰罐中找到了二百三十三号。朱占文。经过台湾方面核查后确认,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的股会被迎回北京八宝山。二零一一年七月,国安部的专机把我送回宁波镇海安葬,我的遗像停留在四十五岁,可是儿女都已经白发苍苍。这段仅仅六十公里的路,我却以这种形式走了六十一年。从富家千金到身中六枪英勇就义。我从不后悔,所谓信仰,就是明知前面是刀山火海,也愿意燃尽自己。所谓英雄,不过是普通人。在该站出来时没退后半步,因为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统一的方向。
或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沉默的荣耀。我是朱枫。在此之前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
听露评娱乐
2025-10-31 21:48:32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