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意识形态问题
诺贝尔的和平奖和文学奖,历来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争端。北边的俄国就是个例子,在苏联时代,有好几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有审查制度,俄罗斯没有,按说在审查时期能顶着审查获得诺贝尔奖,等到了没有审查的好时代,更加容易获奖才是这片充满文艺的土地该有的样子。
结果到了解体后,俄国硬是没有一个获奖的人,难道是俄罗斯没有苏联黑暗吗?解体后几年民不聊生,内乱频发,死亡率大幅上升,直到普京上台才好了起来,但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结果竟然没有一个获奖的。 这不可能是现实不黑暗,更不可能是俄罗斯没有好作品了。而是获奖的几位得主有问题。
第一个获奖的蒲宁,公然敌视十月革命,天天骂苏联,自然有这样的态度应该给个文学奖。第二个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小说批判苏联的体制,又得了一个奖。 索尔仁尼琴也得过一次诺贝尔奖,这位作家的工作也是反苏。 这就叫批判的对象只要正确,就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的文学大家乔治奥威尔,写书批判英国,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畅销度,小说的深刻程度都比帕斯捷尔纳克高十万八千里,但是就是得不到诺贝尔奖。
谁叫他批判英国呢?批判西方民主国家,那就不可能获得文学奖,这就导致美国这个批判文学搞得非常好的地方,竟然只有几个人获奖了。 无他,因为这些人批判的真的是美国,海明威都不知道怎么最后没有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三体人带着纯纯的文学视角在思考地球文学,评奖委员会不是在真空中的,而是深受自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立场的影响,最后出来评奖的。
科技领域的进步奖我们搞得不多,那是技不如人,比如说数学,我们在这些领域搞得确实很一般,阿贝尔奖是近年的,很多办法给了之前其他奖项的老得主,菲尔茨奖四年一次,确实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联数学家和俄罗斯数学家屡次三番得奖。 百年之间就颁奖20次,这个可以认,但是文学奖领域说能出什么人才,和平奖领域要出什么大恩大德的人物,那就是天方夜谭。
归根结底,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和平奖的这种倾向,就是在通过设立并垄断世界级文学成就的定义权和颁奖权,让所谓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得以维持一种道德优越感。 他们的手段就是通过表彰特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让颁奖机构将自己置于自由世界的裁判席上,赋予自身道德制高点。
但是西方这一套也不行了,上来一个特朗普,出了一堆极右翼,诺贝尔文学奖越是想要引导叙事方向,越是鼓励和表彰的是符合西方利益和世界观的作品,对于非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失落的人群,这越意味着一种隐形的歧视。 要么你的批判不触及西方的根本利益,要么你批判的对象是西方所指定的敌人,否则便难以进入这个最高殿堂。
但是西方有人觉得敌人就在内部,这就不好办了,委员会就必须想办法掩盖自身的复杂性了。 那就是找到一条路,去证明西方制度虽不完美但仍是最终归宿的叙事是真的。找不到的时候,就找个喜欢岁月静好的作家,拿出来表彰一番,把头埋起来,继续做鸵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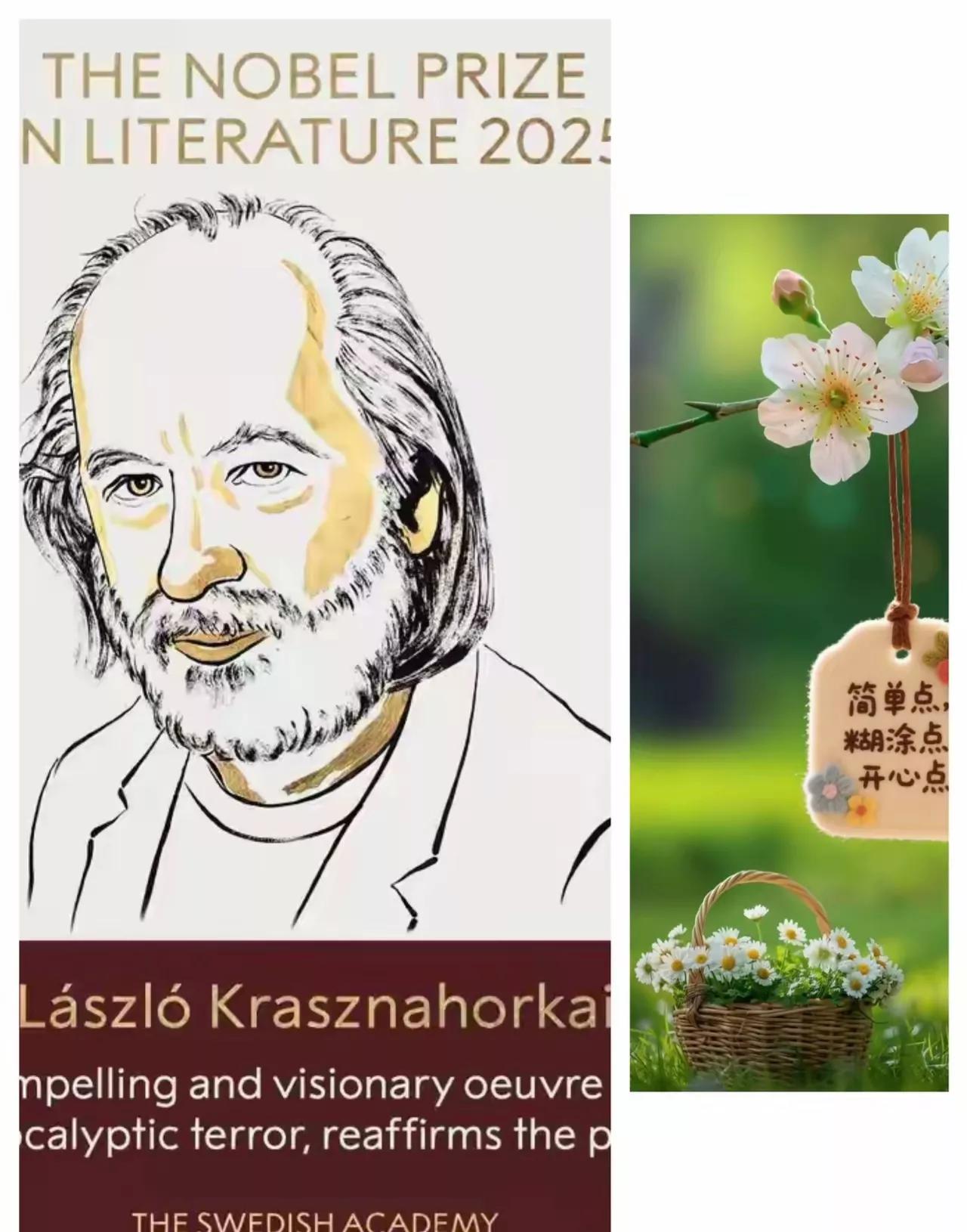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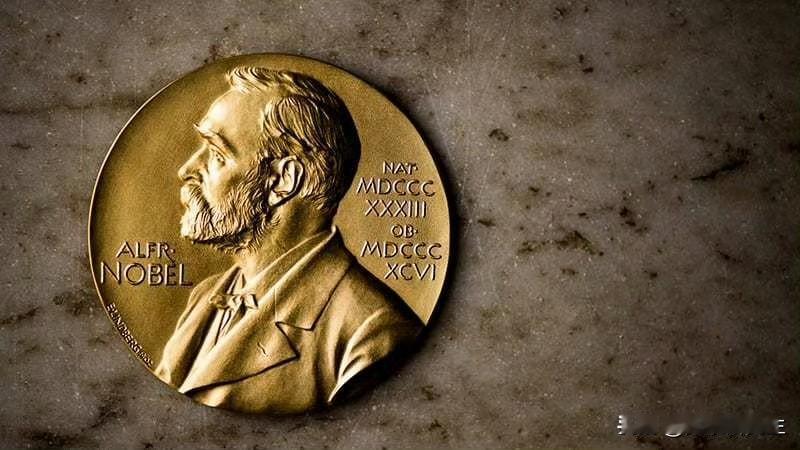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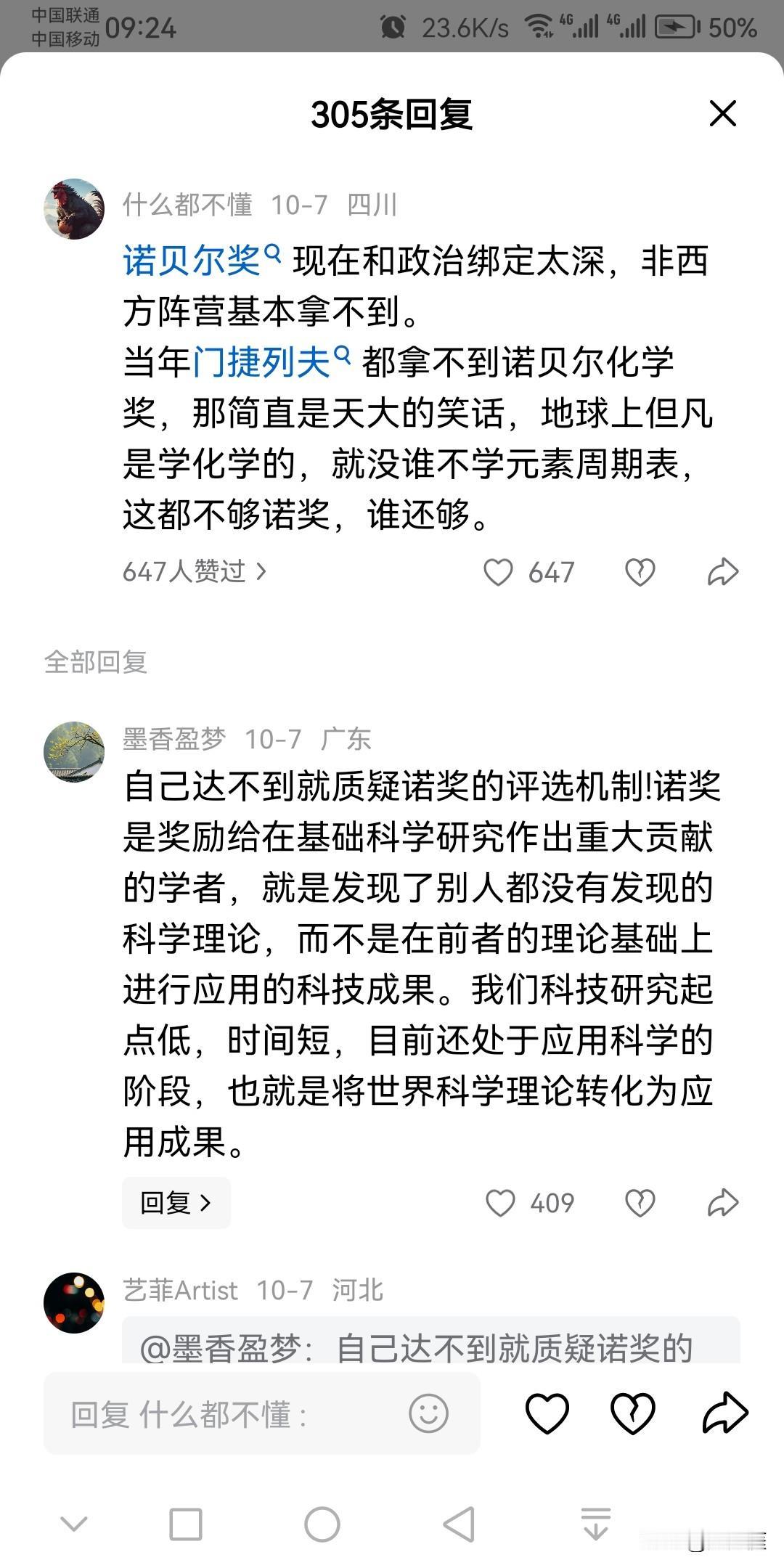


![瞬时电流50A这么窄的线径也能抗住那诺贝尔给你颁奖你也受得啊[doge]](http://image.uczzd.cn/14464498555581729231.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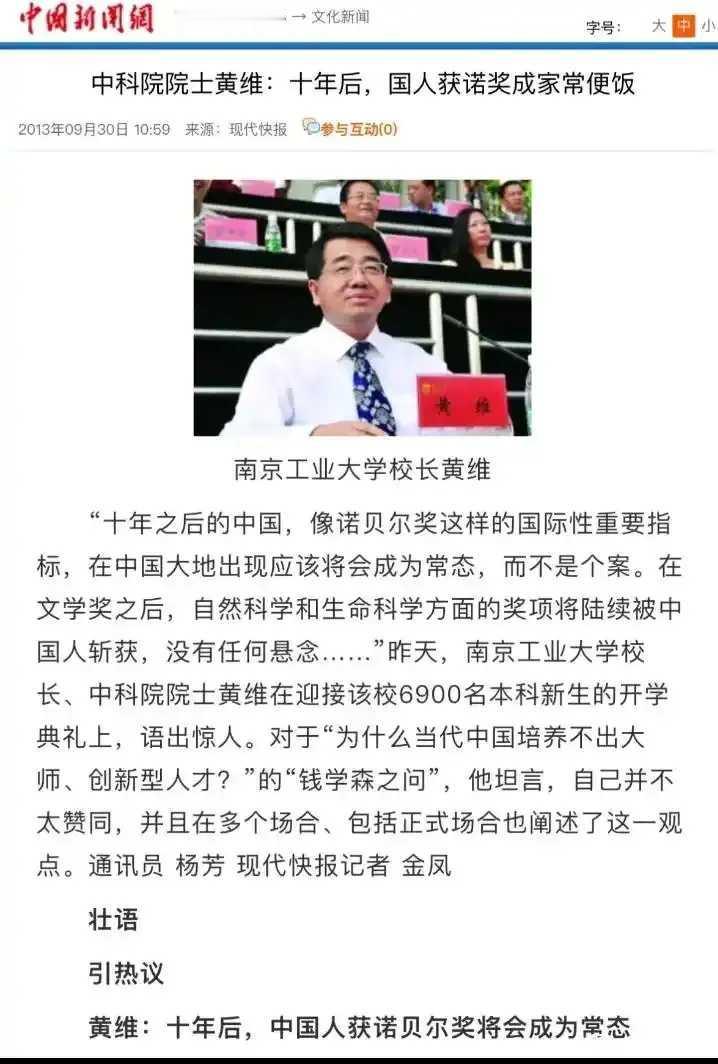

曾经的你
《尤里的复仇》
大牛
诱人叛国瞎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