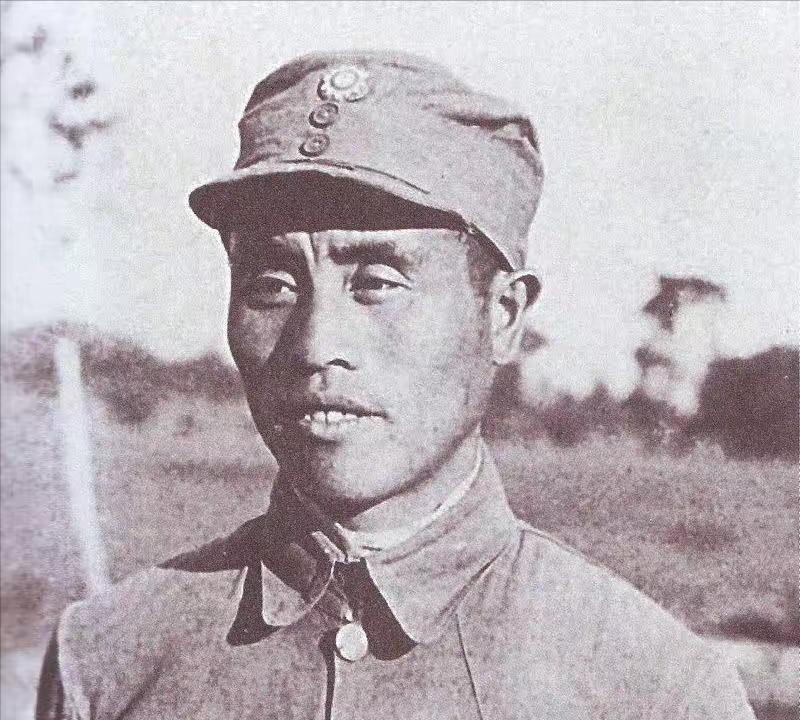1979年,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单位开会结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9年4月的那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张子石刚开完会,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电话铃响起时,他随手接起,以为又是哪个部门的例行汇报。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平静,就几句话,说中央已经决定撤销他的所有职务,他握着话筒的手停在半空,窗外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那一刻,六十三年的人生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 没有预兆,没有征兆,甚至连个心理准备的时间都没有,这就是权力世界的真实面目,你以为自己站得稳稳当当,其实只是站在别人搭建的台子上,台子一撤,摔得有多狠全看运气。 张子石放下电话,看着办公桌上那些还没批完的文件,突然觉得有些荒诞,昨天还在讨论教育改革方案,今天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 他父亲康生去世快四年了,当年葬礼办得很隆重,花圈摆满了八宝山,那时候张子石站在灵堂里,看着络绎不绝来吊唁的人群,心里其实有种说不清的预感。 政治这个东西,生前的风光和死后的评价从来都不是一回事,父亲活着的时候位高权重,可那些往事迟早要有人翻旧账,只是他没想到,这笔账会算得这么快,连带着把他也算进去了。 其实张子石跟父亲并不亲近,他从小跟着母亲长大,父亲常年在外,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后来他考上山东大学读化学,毕业后当老师,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 如果不是1948年那次机缘巧合进了解放区,也许他这辈子就是个普通的中学校长,教教书,带带学生,平平淡淡过一生,可血缘关系这东西,不是你想撇清就能撇清的,别人看你,永远会先看到你父亲的影子。 在青岛教育局当局长那些年,张子石做过不少实事,他主张让学生多动手做实验,多读课外书,不要死记硬背,有些老师觉得他的想法太新潮,但学生们都喜欢他这一套,那时候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跑学校、搞调研、开会讨论,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1975年调到杭州后,工作压力更大了,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事事要操心,但他依然觉得充实,觉得自己还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收拾了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没有跟任何人告别,独自走出了那栋他工作多年的大楼,街上人来人往,没人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突然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啊,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雪地上走一遭吗?脚印留下了,可雪化了,什么都不会剩下。 他做了一个决定,既然北京不能待,杭州也没有意义,那就回老家吧,他去了八宝山,把父亲的骨灰取出来,一个人坐火车回了山东,火车穿过华北平原,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村庄。 他想起小时候在胶县的日子,那时候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母亲总能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也许生活本来就该是简单的,是后来那些年把一切都搞复杂了。 回到老家后,张子石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他在祖宅旁边开了块菜地,每天早上提着水桶去浇水,下午就在屋里写写字、画画画。 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从外地回来的老张,没人知道他曾经的身份,他也不主动提,有人问起就笑笑说自己退休了,他重新捡起年轻时喜欢的书法和绘画,手头紧的时候就拿几幅作品去集市上卖,换点生活费。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十年,没有了权力的光环,也没有了身份的束缚,他反而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每当夜深人静,他会拿出那些泛黄的老照片,看看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自己,看看那些已经模糊的面孔。 那些曾经以为重要无比的东西,现在想来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陪伴他走到最后的,是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是每天升起的太阳和落下的夕阳。 2017年,张子石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享年101岁,邻居们这才知道,这个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原来有着那样不平凡的过去。 但对张子石来说,也许那些才是他人生最真实的部分,不是权力,不是地位,而是那些在菜地里挥洒汗水的清晨,和在书桌前静心读书的夜晚。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道客巴巴——康生儿子张子石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