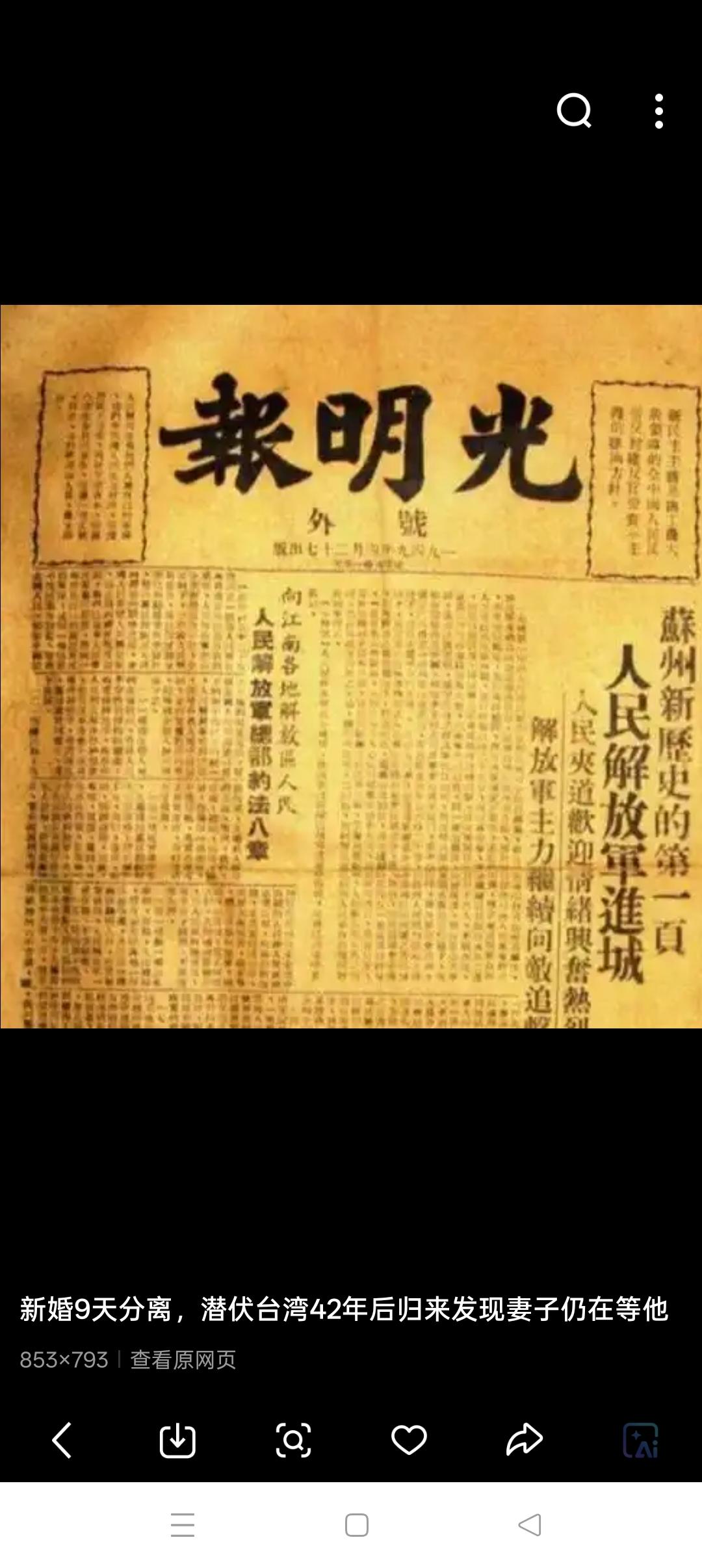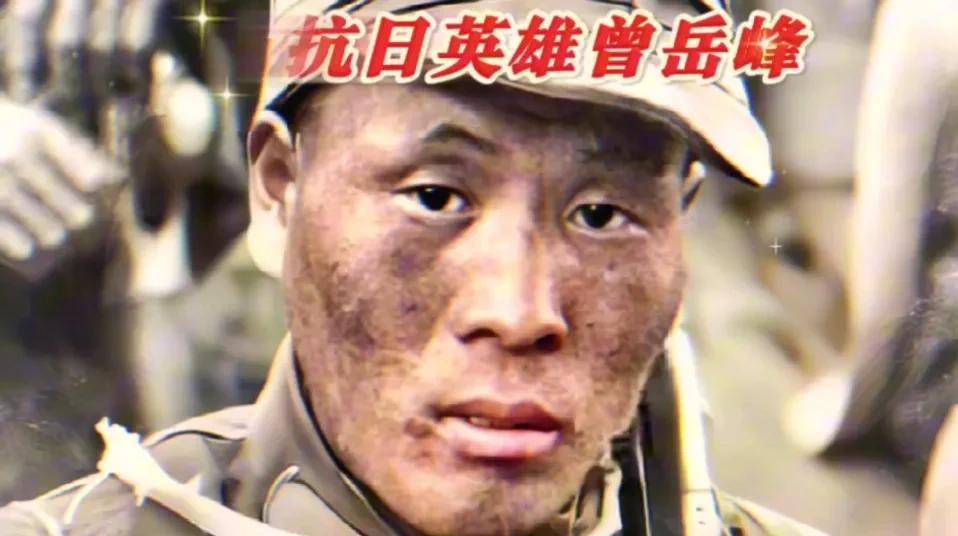1961年,26岁李敖穷困潦倒,面临辍学的风险时,给胡适写信道:“胡先生,我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 1961年,李敖二十六岁。那一年他生活困顿,身上没几件像样的衣服,连裤子都被送进当铺。他在信里写得直白:“胡先生,我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这不是夸张,而是他那时的窘境。他一边为学业发愁,一边还要维持读书和写作的习惯。支撑他的,不是钱包里的钱,而是书桌上那一摞和胡适有关的资料。 李敖年轻时对胡适几乎是痴迷的。他能背出胡适的文章,知道他写过的每个观点,甚至连胡适自己都说过一句:“李敖比胡适更懂胡适。”这种评价有点戏谑,但也能看出两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个在台北苦苦支撑,一个在台大讲坛上传播思想,看似隔着海峡,其实有种精神上的连接。 把时钟拨回到1917年,北京大学。蔡元培刚到任,希望能把北大变成中国思想的新阵地。他找来陈独秀、鲁迅、刘半农,很快又把胡适请了进来。当时的胡适只有二十六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带着一股新鲜劲。他上课不用八股文,而是让学生用白话写作。白话文在课堂上被认可,这在当时就是一场革命。胡适说过:“要有话才说话,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简单得很,却打破了文言的旧框子。 文学革命带来的影响很快显现。过去只能用在民间的“俗文学”被搬上大雅之堂,成了正宗的“国语文学”。鲁迅、周作人写白话小说,学生们模仿,校园里充满新的活力。胡适并不是孤军作战,但他确实是最早提倡用白话讲真话的人。 五四运动发生时,北大学生走上街头,举着横幅喊口号。胡适并没有冲到人群里,他仍旧坚持学术的立场。他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这句话后来常被人引用。有人说他迂腐,不敢正面迎战;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冷静的提醒。在那个满街都是“主义”的年代,胡适像是逆流而行,唱着不讨好的曲子。 他的理性态度贯穿一生。到了三十年代,世界流行独裁思潮,墨索里尼、希特勒声势浩大。连一些中国学者也说中国需要强人政治。胡适坚决反对。他说民主就像孩子学写字,歪歪扭扭也要学,不会一蹴而就。独裁看似效率高,可对一个没基础的国家来说,后果更糟。他甚至写过:“学民主像刻鹄子,刻不像也许还像只鸽子,妄学独裁反而变成狗。”这样的比喻让人记得住。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投身公共讨论,创办《独立评论》,和朋友们大谈政治。他强调宪政,坚持言论自由。那个年代,很多人主张激进,他却不断劝说要走“演进的路”,靠一点点改革来积累。有人骂他是乌鸦,天天说丧气话。他自己也承认过,说宁愿写学术文章,也不爱写社论,可他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 抗战期间,他去了美国,当上驻美大使。公开演讲时,他一口带湖南味的英文说:中国不会投降,会一直打到赢得体面的和平。听众并不觉得滑稽,反而觉得坚定。那几年,他的声音让西方社会重新注意到中国。 战后到台湾,胡适担任大学校长,又主持中央研究院。他讲“容忍与自由”,提出要有十年的学术计划,希望集中资源,把几所大学建成研究中心。钱很少,环境也差,但他还是坚持。他在会议上说:“这只是个起点,但能证明科学开始被重视。”这种笨拙的坚持,是胡适一贯的风格。 李敖看在眼里,心里复杂。他钦佩胡适的远见,但也觉得他太保守,太沉迷考据。李敖说胡适喜欢“打鬼”,浪费时间在古籍辨伪上,没有把力气用在社会的大问题上。在李敖看来,这是一种错位。他希望的是彻底的思想革命,而胡适走的是渐进的改良之路。 两人之间有时像是隔着代沟的争论。一个急,一个稳。李敖着急社会要变,胡适则相信变化得靠积累。李敖不耐烦,说胡适拖拖拉拉。可胡适觉得,真正的进步只能慢慢来。 胡适的性格里还有另一面。他听说学生生活困难,会寄钱相助。课堂上,看到冷风灌进来,会亲自下去关窗。有人追求他,他却在扇子上写下“爱情的代价是痛苦”。他不是冷漠的人,只是感情上自律得近乎苛刻。 他的一生中,批评声和赞美声从未停过。有人说他是“学阀”,有人说他是“现代中国的贤者”。他讲的“个人主义”,其实很简单:独立思考,自己负责。他常说:“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句话今天听来,仍旧能敲人心。 1961年的李敖,寄出那封裤子进当铺的信时,大概不会想到胡适也正在为科学计划奔走。两个不同年纪的学者,一个困在现实的贫穷里,一个困在社会的偏见里,却都在为同样的事焦灼:怎样让知识有尊严。 胡适晚年,独自去市场买菜,自己煮茶叶蛋。这样的小事让人觉得心酸。曾经的学术旗手,风光无限,到头来过着普通老人的日子。他笑得很自然,但身边其实很寂寞。 北大旧校门旁的槐树依旧,每到深夜影子被灯光拉长。有人说,仿佛还能看见一个清瘦的身影走得很慢,身后是那个被时代推着走的长长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