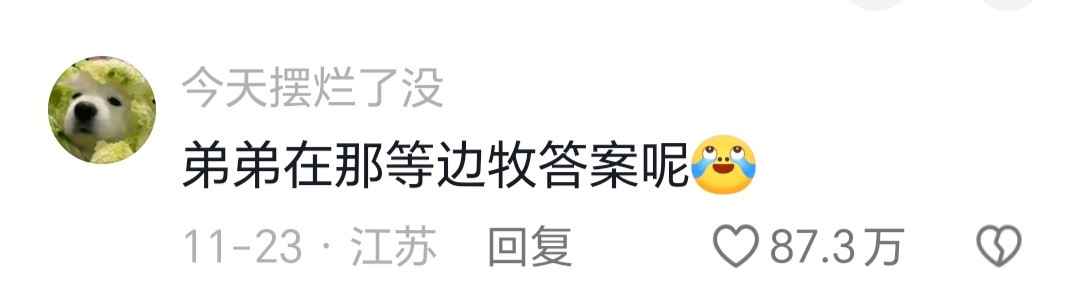昨天我还说我婆婆病了,我老公整日不回来,没想到啊,昨天晚上他居然回来了,回来送了一包成人纸尿裤,也没问老妈病怎么样了,也没搭理我,更没搭理孩子,就在家扭了一圈儿又出门了,再次回来我看了看手机,已经是凌晨12点半了。 昨天还跟邻居念叨,婆婆退烧后总说腿软,下床都费劲,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跑前跑后,老公的拖鞋在鞋柜里摆了三天,鞋尖落了层薄灰。 厨房飘着熬了一下午的小米粥味,孩子趴在沙发上画恐龙,蜡笔在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点,像我心里堵着的那些话。 门锁咔嗒响的时候,我正给婆婆换毛巾,手一抖,温水洒在床单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白色包装上“成人纸尿裤”几个字刺得我眼睛疼;没问妈今天吃了多少饭,没摸孩子的头说句“乖”,甚至没看我一眼——就像进了别人家的门。 他在客厅转了半圈,脚步在婆婆房门口顿了顿,又径直走向玄关,换鞋的声音比平时重,“砰”地关上门,楼道声控灯亮了又暗。 我盯着茶几上那包纸尿裤,包装边角被捏得发皱,想起上周他说公司接了新项目,天天加班到深夜,手机里的工作群消息比我的微信多十倍——可再忙,问一句“妈好点没”很难吗? 他总说“男人养家不容易”,可家不是只靠钱撑着的;那包纸尿裤放在茶几上,像个不会说话的证人,证明他记得妈需要这个,却忘了家人等的不是物件,是一句“我回来了”。 凌晨十二点半,他回来时我还没睡,客厅的小夜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拖鞋还是摆在老位置,灰没了,可鞋跟蹭着地板的声音,比落灰时还让人心慌。 婆婆翻了个身,嘟囔着“水”,我起身时,听见他在沙发上叹气,声音轻得像怕惊到谁,又像根本不在乎谁听见。 明天早上,或许该把那包纸尿裤收进妈房间,再问他一句“今天能早点回来陪妈说说话吗”——哪怕答案还是沉默。 小米粥的味早就散了,蜡笔画还在沙发上,恐龙的眼睛被孩子涂成了黑色,直勾勾盯着门口;他的呼吸声和婆婆的咳嗽声混在一起,在凌晨的安静里,一下下撞着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