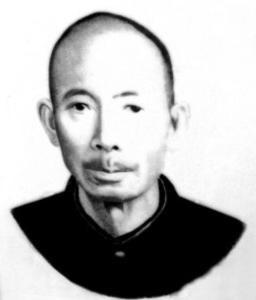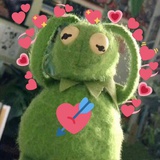我发现经常去寺庙烧香的基本上都是这两种人:一种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每日靠出卖体力赚着生活费,总是为明天的生活而焦虑,看不到未来。 王大叔就是这类人里的一个,今年五十出头,在城郊的建材市场扛水泥,一天下来能赚两百块,前提是得有活儿干。他住的出租屋就在市场旁边的老旧民房里,十平米的小单间,摆下一张床和一个煤炉就没多少空间。老婆早几年因病走了,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学费和生活费压得他喘不过气。儿子最近总说头晕,去医院查了说是贫血,医生让加强营养,可王大叔每天的饭都是两个馒头就着咸菜,偶尔买份炒青菜都觉得奢侈。他第一次去寺庙是听工友说的,说后山的观音庙很灵,求健康求平安都管用。那天收工后,他揣着皱巴巴的五十块钱,买了最便宜的香,在观音像前磕了三个头,嘴里反复念叨着让儿子身体好起来,自己能多揽点活儿。从那以后,只要每月能攒下点余钱,他就会去一次寺庙,香还是最便宜的,但磕头时的劲儿一次比一次足。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只是觉得跪在神像前的那一刻,心里的焦虑能少一点,好像有了点盼头。 寺庙里的另一类人,和王大叔完全是两个世界。张姐今年四十多岁,开着一家不小的服装店,家底厚实,穿的用的都是牌子货。她来寺庙的频率比王大叔还高,每周至少来一次,每次都买最贵的香烛,还会给寺庙捐不少香火钱。别人都以为她是来求生意兴隆,其实她是来求心里踏实。张姐的丈夫常年在外做生意,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早就淡了,去年她发现丈夫外面有人,闹了一场后,丈夫虽断了联系,但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儿子在国外读书,一年到头见不了一次面,打电话也总是说不了几句就挂了。她的服装店生意不错,可每天守着空荡荡的店铺,回到装修豪华却没人说话的家,心里就空落落的。有次朋友带她来寺庙散心,她看着香烟缭绕的大殿,听着僧人念经的声音,突然觉得心里静了下来。从那以后,她就成了寺庙的常客,每次来都要在大殿里坐半个小时,对着神像不说太多话,就只是坐着。她不求赚更多钱,也不求丈夫回心转意,就求自己能少点失眠,少点胡思乱想。 王大叔和张姐在寺庙里见过好几次,有时会在香炉旁边遇上。王大叔穿着沾满水泥灰的工装,张姐穿着得体的连衣裙,两人看着彼此,都能从对方眼里看到一丝疲惫。有一次下雨,两人都在寺庙的屋檐下躲雨,张姐递了一瓶矿泉水给王大叔,王大叔连忙道谢,拧开瓶盖喝了一口。“你也是来求平安的?” 张姐先开了口。王大叔点点头:“求我儿子身体好,能多干点活儿。” 张姐轻轻 “嗯” 了一声:“我就想来坐坐。” 那天他们没多说什么,就那样并肩站着看雨,雨水打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王大叔后来还是每天扛水泥,只是儿子的贫血慢慢好了,学习成绩也稳定了些,他去寺庙的次数没变,但脸上的愁容少了点。张姐依旧每周来寺庙,只是后来她开始跟着寺庙里的僧人学抄经,抄经的时候能完全静下心来,不再想那些糟心事。她还把店里的部分衣服捐给了山区的孩子,收到孩子们寄来的感谢信时,她心里第一次有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寺庙里的香火每天都很旺,来的还是那两类人,一类为生计奔波,求的是柴米油盐的安稳;一类衣食无忧,求的是内心的安宁。他们身份不同,境遇各异,却都在这座古旧的寺庙里,在袅袅香烟中,寻找着各自的寄托。或许生活本就如此,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需要一个地方安放心里的焦虑和期盼,而寺庙,就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落
我发现经常去寺庙烧香的基本上都是这两种人:一种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每日
白莲钢琴
2025-11-29 02:26:28
0
阅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