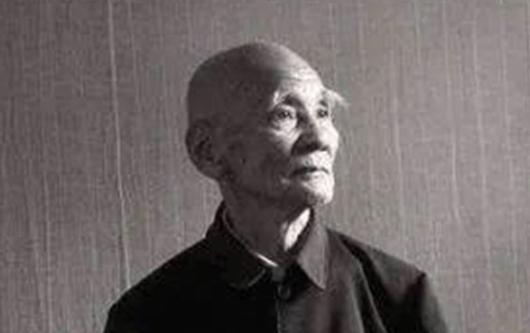[微风]1964年,沈醉说:当年徐远举刑讯江姐时,要扒掉江姐的衣裤,沈醉目睹了江姐怒骂徐远举,免遭侮辱的全过程。罗广斌说:江姐的机智、勇敢没写进小说,太可惜。 那天的渣滓洞,徐远举作为从《红岩》里的“徐鹏飞”走进现实的原型人物,早就对此刻的僵局失去了耐心。 那个叫江竹筠的女人,已经被折磨得没人样了,十根手指被竹签摧残,肿胀得像是紫红色的萝卜,连站立都需要两边的特务死死架住。 可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是不开口,徐远举在这个行当里混油了,深知肉体疼痛有时不如心理防线崩得快,他那双靴子踩灭了烟头,下了一道在军统内部看来并不新鲜的命令:把她的衣裤全部扒光。 在他那扭曲的想法里对一个旧时代的女人,甚至对任何人来说,光着身子比烙铁还让人羞耻,只要这层布一脱,人的尊严也就没了,徐远举等着看好戏,旁边的特务都伸出手,以为这次又能像之前十次里的八次那样成功。 没想到,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女人,那一刻爆发出的力量就像一声炸雷,江姐猛地抬起头,那双已经被打得肿成一条缝的眼睛里,射出来的光比刑具还冷。 她并没有像只待宰的羔羊那样求饶,也没有因为恐惧而蜷缩,而是直接用那双还在滴血的手死死护住那层破烂的囚服,声音劈头盖脸地砸向了徐远举:“徐远举,你是女人养大的,你母亲是女人,你老婆女儿也是女人。你今天扒我的衣服,就是在扒她们的衣服!” 站在门口原本打算只是来“观摩”的沈醉,在那一瞬间感到后背发凉,很多年后他在回忆录《我这三十年》里提到这个细节时,笔尖依然颤抖。 他意识到,这间屋子里的攻守态势瞬间倒转了,原本掌生杀大权的是他们,可江姐这一骂,把“羞耻”这两个字像钉子一样,原封不动地钉回了施暴者的脸上,她是在告诉眼前这群衣冠楚楚的禽兽:此时此刻,脏的不是那个受刑的人,而是这群掌握着权力却丢失了人性的特务。 沈醉记得那个场面尬住了,特务的手悬在半空,没人敢真的再进一步,徐远举那张脸涨成了猪肝色,他也没想到会被一个阶下囚拿伦理纲常给将了一军。 屋子里静得吓人,只有血滴在地上的声音,沈醉见状,在旁边不得不踢了徐远举一脚,小声嘀咕让他换个招。这时候徐远举才像是找了个台阶,气急败坏地吼着上竹签,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肉体折磨的轨道上。 这场没见光的交锋,最终没能进那本畅销小说,罗广斌听完后直拍大腿说可惜,但在那个当下,这股子硬气并非凭空而来。 如果回顾江竹筠的一生,会发现这个女人的一生早就把“苦”吃得像盐一样平常,从四川自贡的江家湾出来,她10岁就在重庆的织袜厂当童工,那双手早就磨出了茧子。 20多岁时做剖宫产甚至还得顺带做绝育手术,丈夫彭咏梧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在城门示众时,她也没有倒下,而是擦干眼泪去接替那条只有她熟悉的地下交通线,一个连死和断头都不怕的人,怎么会被这点下作手段吓倒?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铁,也活成了一面镜子。 后世的人们,大多习惯了从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看到英雄的形象:光环万丈,就义的场景伴随着慢镜头和激昂的配乐,但抛开这些艺术加工的元素,真正的革命斗争往往就发生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角落。 当年的特务们,总是把自己的恶行归咎于“执行命令”,把自己的良知推给“党国”,认为只要是上级交代的任务,再肮脏的事情做起来也心安理得,而江姐的那一番怒斥,恰恰撕开了他们的这层遮羞布,让他们明白:作恶就是作恶,没有任何借口可言。 沈醉晚年的时候,常常会在梦里梦到审讯室里的灯泡和江姐那双锐利的眼睛,大概就是因为那一次的经历,让他清楚地意识到,在真正有人性、有骨气的人面前,自己的灵魂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微。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青春绛烟锦江畔——革命烈士江姐的故事.2022.02.06 央视新闻.傲骨红梅 千秋不朽!在七封家书中重温血肉丰满、可亲可敬的江姐.2022.08.2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永远的人民代表 永远的江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