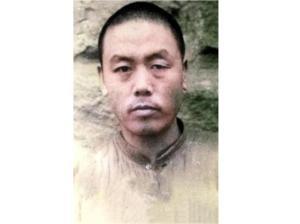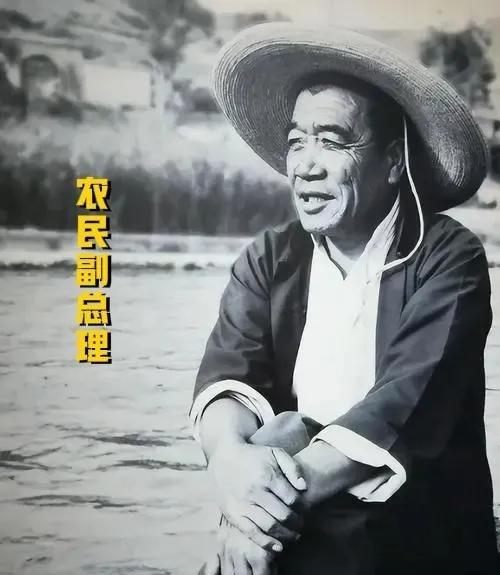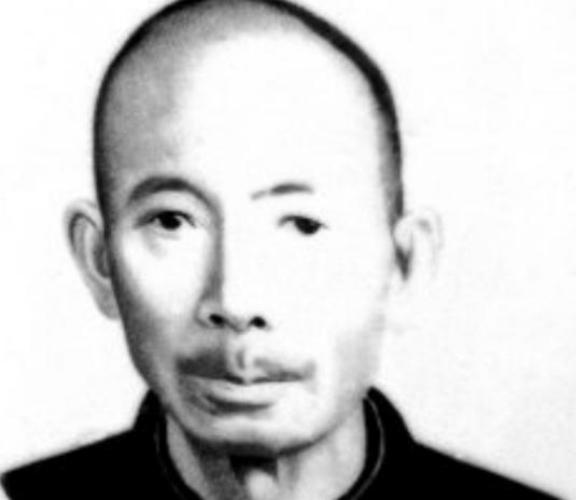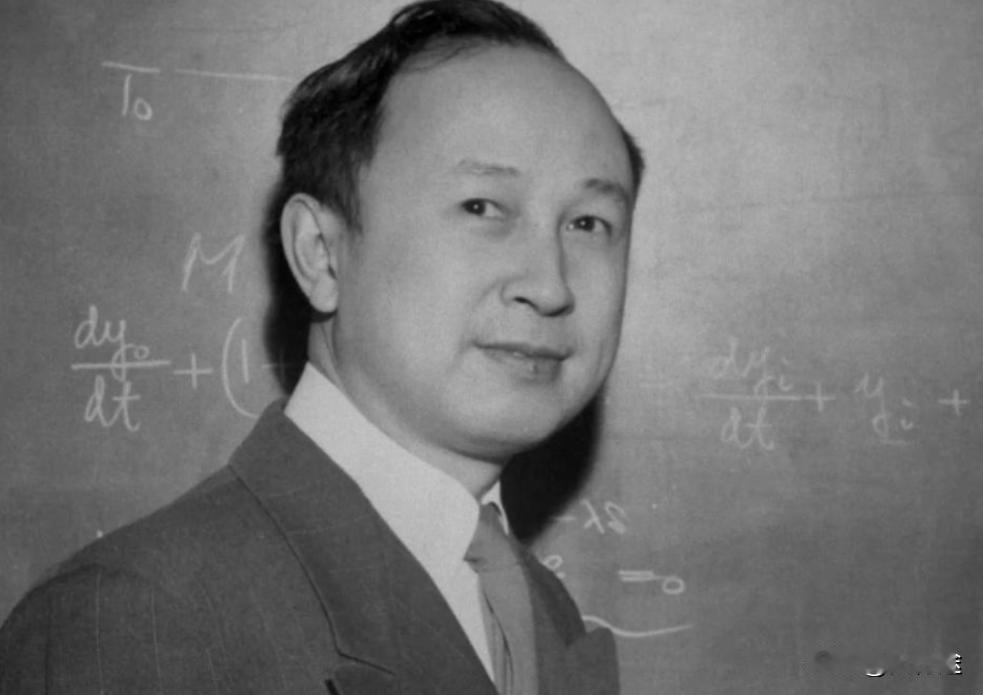1986年,65岁的火箭专家杨南生娶了29岁的张严平,张严平的父母不同意,不料,当她父母知道杨南生的身份后,惊呆了。 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年头,一位头发花白的航天老专家和一位刚入行的年轻女记者,本来只是工作上的点头之交,怎么就搅和出一段跨越三十多岁年龄差的姻缘?父母一听,火冒三丈,直呼不靠谱,可当他们挖出那层隐秘身份,顿时傻眼了。这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家国故事? 杨南生1921年出生在福建海澄一个书香门第,受舅父萨本栋影响,从小就对科学着了迷。1943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没几年就考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专攻塑性力学,1950年拿到博士学位。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让他回国报效。他二话不说,辗转印度香港,谢绝了国外高薪,回到祖国。先在汽车工业干起,帮着搞“解放牌”卡车的材料研究,后来钱学森点名要他,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就这么干上了。 1956年,杨南生挑头搞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那会儿条件苦,设备简陋,团队从头摸索。他负责力学计算,确保火箭稳稳升空。成功那天,毛泽东主席亲眼瞧见了,夸这事儿干得漂亮。从那以后,他转固体火箭,1964年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当副院长,带队扎根内蒙古戈壁。那里条件更差,风沙大得能把人埋了,可他就这么守着,一干就是好几年。探空火箭批量生产了,为防空预警立下大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第三级发动机,他把关推力,卫星准时入轨;“巨浪一号”导弹的预研方向控制系统,也少不了他的份儿。这些年,他档案上就写“高级工程师”,从来不张扬,甘当无名英雄。 1978年后,杨南生调到西安,继续带项目。戈壁的日子让他身体落下一堆毛病,可他总说,航天事业是国家脊梁,得咬牙顶住。到1984年秋,他已经63岁了,北京的《科技日报》编辑部里,27岁的张严平接了个采访任务,就是找他聊聊火箭技术。张严平那时候刚入行不久,手里攥着问题单子,以为会碰上个严肃的老科学家。谁知一聊,杨南生不从专业术语入手,先问她读没读过拜伦的诗。两人从文学扯到历史,又聊到哲学,三个钟头一晃就过。他临走时,还塞给她一张纸条,抄了句诗:“她走路像静夜,微笑如黎明。”张严平拿着那纸条,采访的框框就这么破了。 一周后,他们又见,杨南生讲起自己的求学生涯,从战乱里的西南联大,到苏联深造,再到归国投身火箭。他描述戈壁试车,推进剂配比反复调,火箭点火时地面直颤。张严平听着听着,笔记上多了些生活片段。采访完,书信就来了,杨南生的信总从科学说起,末尾带点人生道理。张严平回信,字里行间透着对这种对话的喜欢。到了1985年春,杨南生在信里提结婚,说自己岁数大,她年轻,不知能给她多少日子。张严平回,年龄是数字,心灵相通才算数。俩人就这样,隔着信纸拉近了距离。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掂量,尤其是张严平告诉父母时。那是1985年底,北京胡同的老屋里,饭桌上她一开口,父亲筷子就放下了,直摇头说岁数差太悬殊,日子没法过。母亲也抹眼泪,觉得女儿正当年,他快退休了,未来咋整。父亲还追问职业,她说是个工程师,父亲叹气,说年纪一大把,能有什么指望。亲戚们听说,也上门劝,年龄差摆那儿,生活磕绊肯定多。张严平夹在中间,难受了好几天。父母甚至说要断绝关系,家里气氛跟锅里的粥似的,搅和不开。 转机来得突然。一个雨夜,张严平跟父母补了句,杨南生在西北戈壁为国家火箭项目干了半辈子,一直低调,从不提那些事儿。父母听着,还在摇头。偏偏那晚电视播航天纪录片,镜头一转,荣誉墙上杨南生的名字跳出来,旁白介绍他固体火箭的奠基贡献。父亲的茶杯砸地上,碎了,他盯着屏幕半天说不出话。母亲捂着嘴,泪水直流,低声嘀咕,原来是这样的人。屋里安静下来,只剩雨声。父亲长叹口气,说国家这样的人才,确实不一样。从那天起,父母的态度软了,虽还有顾虑,但不再硬拦。 1986年春,北京一个小礼堂里,俩人办了场简朴婚礼。没大排场,就几家亲友见证,杨南生65岁,张严平29岁,年龄差36岁,可他们就这么走一块儿了。婚后,杨南生还得驻陕西基地,张严平在北京上班,两人两地分居。一次火箭发射前,基地缺物资,她背着压缩饼干和罐头,坐火车颠了两天赶去。到了那儿,杨南生和同事们连轴转了72小时,眼都熬红了。她帮着分东西,基地的日子虽苦,但俩人挤出的时间,总聊些往事。 杨南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胃溃疡旧病复发,腹主动脉瘤也来了。张严平一咬牙,辞了工作,专心照顾他。每天早上,她扶他下楼晨练;去医院检查,她记下每项指标;夜里疼起来,她守到天亮。外人看不明白,说她本可以过更轻松的日子。张严平总说,她嫁的不光是个人,还有他的那份家国情怀。2013年,杨南生走了,按遗愿,她把骨灰撒进大海。收拾东西时,她在书堆里翻出尘封的证书和奖章,那些金字记录着他对两弹一星的贡献,从没跟她显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