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同居8年后,巩俐卑微地向张艺谋说:“结婚吧,我给你生三四个孩子!”谁料,张艺谋却回绝说:“婚姻就是一张纸,我们不需要!”巩俐听后,泪如雨下…… 1995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厂房里,巩俐坐在张艺谋对面的木椅上正在翻看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本。 她望着眼前这个一起走过十年的男人:“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三四个孩子。” 可他却说:“婚姻就是一张纸,我们不需要。” 同居八年,竟只换回这一句话么? 1987年,拍摄《红高粱》时,27岁的张艺谋刚从摄影师转型导演。 而22岁的巩俐是中戏大二学生,她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扎着麻花辫,站在玉米地里试镜“九儿”。 这次的拍摄,算是两人的初次接触。 巩俐把“九儿”演活了,《红高粱》拿了柏林金熊奖。 庆功宴上,巩俐举着酒杯站在张艺谋身边,笑着说:“是你让我看见,原来女人可以这么活。” 张艺谋也笑,没说出口的是,他早就在镜头里沦陷了。 他爱她演戏时的投入,爱她对艺术的较劲,爱她身上那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 接下来的十年,他们成了中国电影的“黄金同盟”。 《菊豆》里,她演被命运碾压的杨金山媳妇,他拍出了封建礼教的窒息。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她演争宠的颂莲,他把宅斗的残酷拍成了诗。 《秋菊打官司》里,她裹着棉袄追着村长要说法,连皱纹里都带着股子“较真”。 张艺谋说:“巩俐的每一个眼神,都是戏。” 巩俐成了威尼斯影后,张艺谋成了“第五代导演的旗手”。 记者问“你们的默契从哪来”,巩俐笑:“他懂我演的每一个眼神,我懂他镜头的每一个角度。” 他们是彼此的“事业光”,没有张艺谋,巩俐不会这么快站上国际舞台,没有巩俐,张艺谋的电影里少了最鲜活的女性灵魂。 外界说他们是“最佳拍档”,但生活不是电影。 矛盾是从1987年埋下的。 那时张艺谋刚和肖华离婚,这位陪他从插队走到北电的妻子,在他的口袋里翻出一封给巩俐的情书。 肖华在《往事悠悠》里写:“我把信烧了,没和他吵。我知道,这个男人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 可张艺谋对婚姻的抗拒,远不止是“移情别恋”。 他是家里的长子,从小被教育“要扛事”。 结婚意味着要分精力照顾家庭,要应付亲戚的人情,要给孩子找学校。 这些“琐碎”,对把事业当命的他来说,是种束缚。 他跟朋友说:“我拍《红高粱》时,连肖华生孩子的电话都没接。对我来说,电影比什么都重要。” 巩俐不是没察觉。 拍《秋菊打官司》时,她看见张艺谋抱着女儿张末的照片发呆,小心翼翼问:“要不要给女儿找个新妈妈?” 张艺谋沉默了半天,说:“我对婚姻,已经没什么期待了。” 巩俐没再问,可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 她是传统的女人,她想要的只是“一个温暖的家”。 1990年,巩俐的二哥来北京看她:“你和张导什么时候结婚?我不想你老了后悔。” 那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要不我们结婚吧,我想给你生个孩子。” 张艺谋却抬头皱着眉:“婚姻就是一张纸,我们俩在一起,比结婚管用。”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巩俐心里。 她开始明白,张艺谋的“不需要”,不是不在乎,是根本不想给。 他要的是“自由的爱情”,不是“被婚姻绑住的陪伴”。 1995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拍摄进入尾声。 有天深夜拍外景,巩俐突然说:“我不想拍了。” 张艺谋回头:“你想怎样?” 巩俐说:“我要结婚,我要一个家。” 张艺谋沉默了很久,说:“我们不合适。” 这部电影拍完后,两人彻底分开。 巩俐搬出了张艺谋的公寓,张艺谋继续拍他的《有话好好说》。 后来有人问巩俐:“后悔吗?” 她笑着说:“不后悔,至少我试过了,我要的,是一个明确的‘我们’,而他给不了。” 分手后的第二年,巩俐嫁给了新加坡商人黄和祥。 婚礼上,她穿着白纱,笑得很幸福。 这一次,她终于有了“家”。 后来她和黄和祥离婚,又和法国男友在一起,不管怎样,她始终在寻找那份“被需要的安全感”。 张艺谋则继续拍电影,直到1999年遇到陈婷。 他和陈婷在一起,2001年生下大儿子,2004年二儿子,2006年小女儿。 2011年,他终于和陈婷登记结婚。 不是因为“爱”,是因为“传宗接代”的责任,是因为“给孩子一个名分”的需要。 2013年,张艺谋超生事件曝光,他在公开信里道歉:“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家庭。” 可他没说对不起巩俐。 现在再看1995年,巩俐的眼泪和张艺谋的拒绝,其实都藏着各自的执念。 他们曾经互相成就,把中国电影推上国际舞台。 也曾经因为一张纸,分道扬镳。 这不是谁的错,只是两个人的“需求代码”,从来都不兼容。 主要信源:(央视网——张艺谋默认当年和巩俐分手原因 不想旧事再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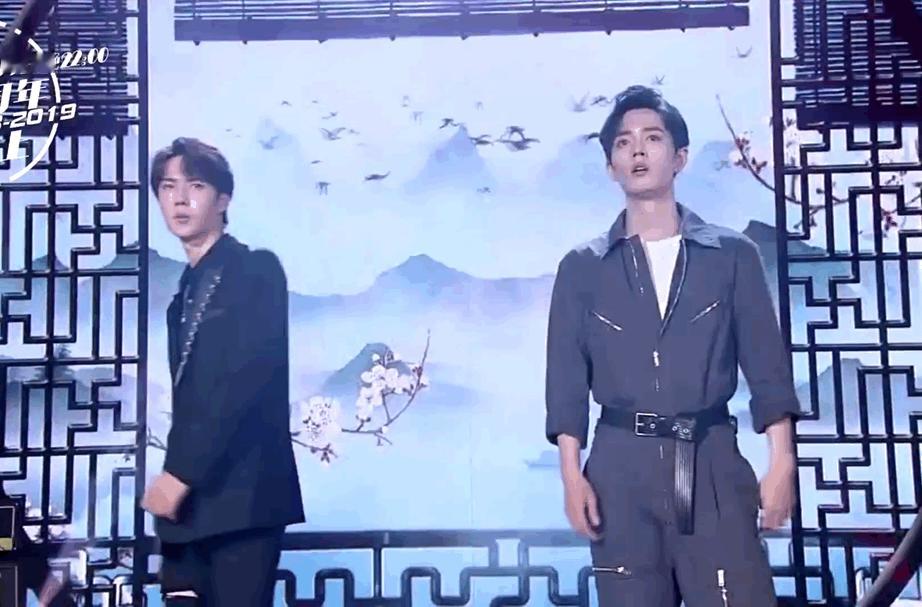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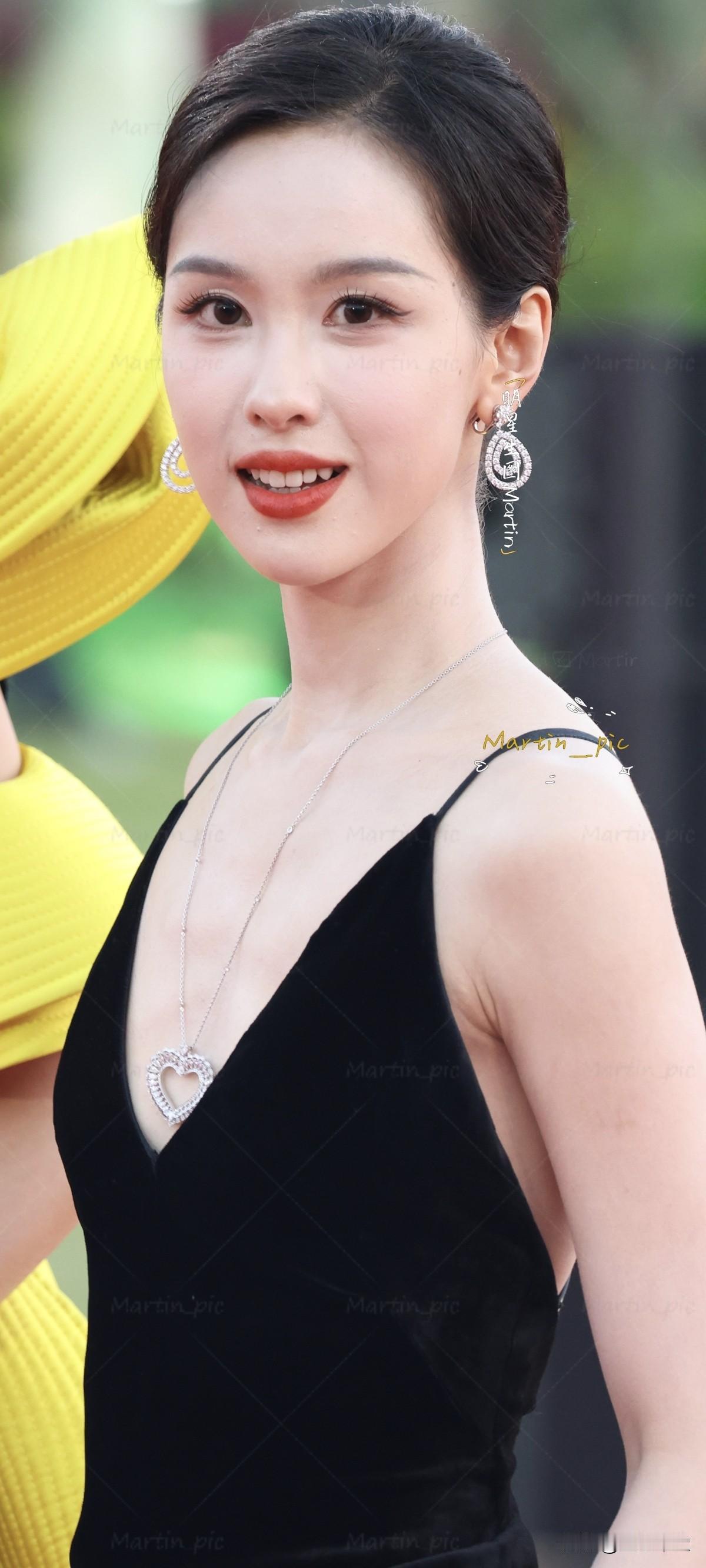

白云
艺哥总结,我有才趁年轻多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