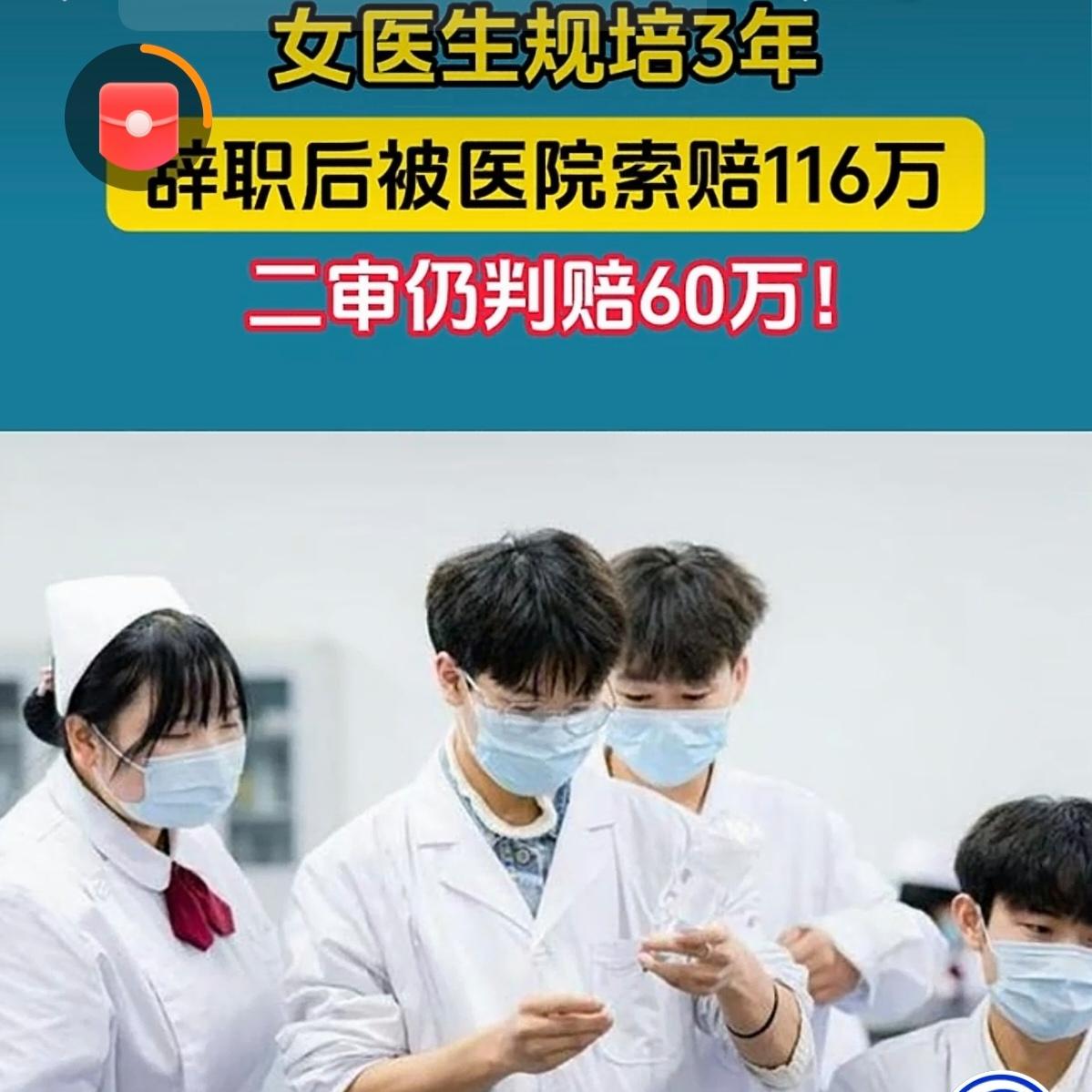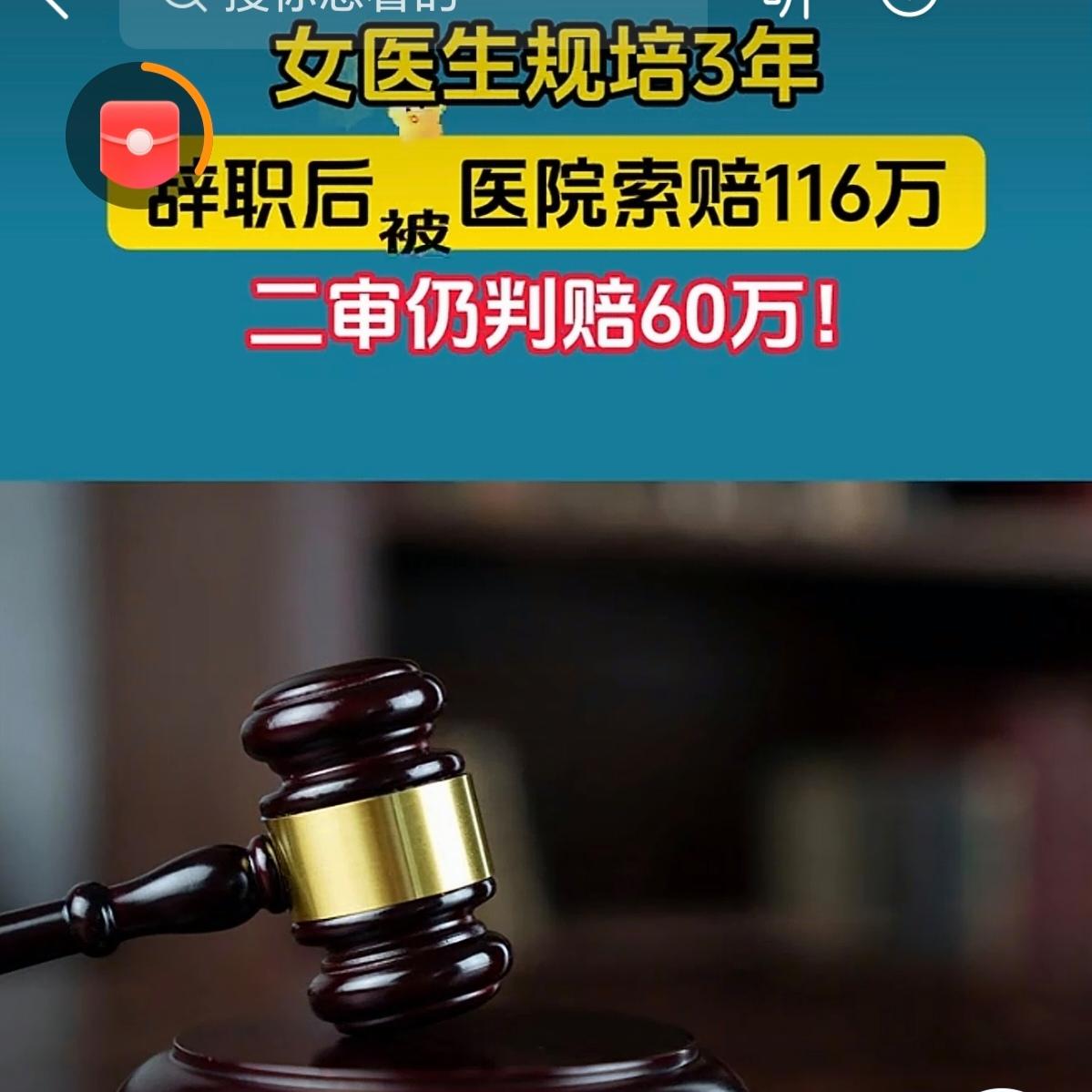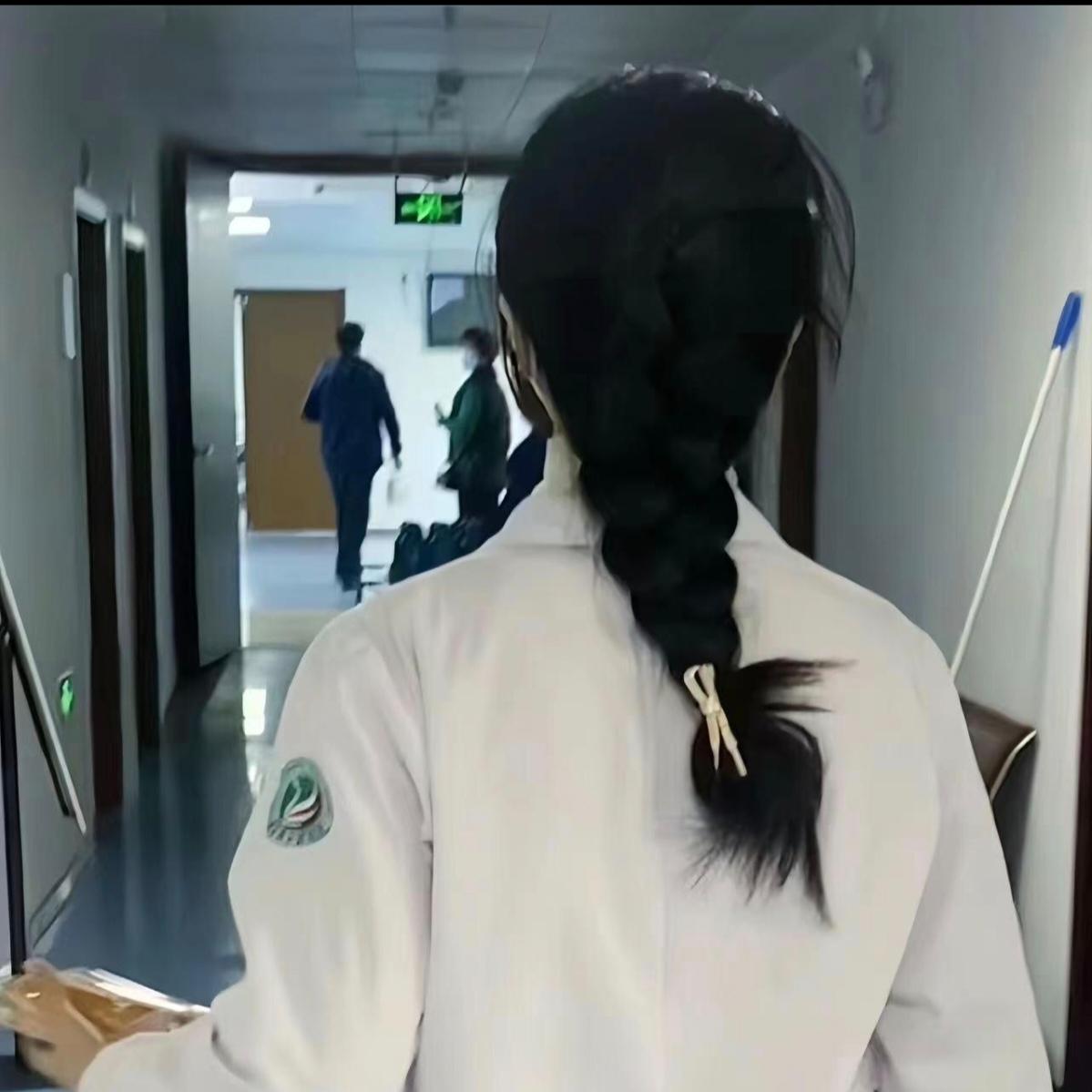四川凉山,年轻女医生和一家县级医院签下了规培协议,医院出资,女医生去省城参加3年的规培,培训结束后,女医生要为医院服务满8年。结果规培刚结束,女医生就违约,医院将女医生告上法庭,并索赔116万,最后法院判了。 2020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唐某与医院签署了一份协议。医院出资,唐某去省城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三年;培训结束后,她承诺回院服务满八年。 协议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若违约,须退还全部费用并支付高额违约金。彼时的唐某,刚从医学院毕业,对未来充满憧憬。能拿着工资去大医院进修,是许多同龄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她几乎没多想,就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三年过去,医院为她投入了36.5万元,包括工资、社保与绩效补贴。唐某顺利完成培训,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凉山。但没人想到,仅仅第7天,她就向人事科递交了辞职信。 医院的领导惊愕地看着她:“你是认真的?我们花了三年培养你!”唐某平静地回答:“我已经决定了。” 院方拒绝批准,认为她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并以合同为据将她告上法庭,索赔总额116万元,其中包括36.5万元培训支出与80万元违约金。 庭审现场的气氛凝重。唐某辩称,规培期间的工资是劳动报酬,不属于培训费用;且八年服务期过长,约定的违约金远超实际投入,应当视为显失公平。 而医院的代表则态度坚决:“她的离开,让我们3年的培养投入付诸东流。我们缺医生,不是缺培训经历的人。签了字,就该履行!” 案件由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法官查阅协议后指出,这份合同中确实存在“服务期约定”,属于《劳动合同法》第22条所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按照这一条,违约金原则上不得超过36.5万元。但案件出现转折——法院认定唐某并非普通劳动关系,而是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本案属于人事争议,适用的法律并非《劳动合同法》,而是《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 这一认定,成为判决的关键。根据该办法,事业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的服务期协议,违约金可由双方协商确定。法院可根据单位性质、损失程度与违约人过错酌情调整。 法官认为,医院属于二类公益事业单位,唐某系受聘医生。医院出资三年培养她,属于典型的“带薪深造”。唐某培训结束即辞职,不仅未履行服务义务,也造成医院人才培养计划落空。 法院最终裁定:唐某无需退还36.5万元工资,但须支付60万元违约金。这一金额既未完全支持医院主张的80万元,也体现了对唐某严重违约行为的惩戒。 唐某不服,上诉。她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按《劳动合同法》处理,违约金应限于实际培训费用范围内。二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理由是:唐某属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合同中违约条款合法有效。 这意味着,唐某败诉,必须支付60万元。 这场“规培纠纷”迅速引发社会热议。有人认为,医生签字就该履约,医院培养一个人才不易;也有人质疑:八年服务期太长了,60万元违约金远超实际支出,是“变相捆绑”。 其实,这场官司的背后,是医疗体系中一个更深层的现实矛盾——基层医院留人难,青年医生走得快。 在很多地方,基层医院为了留住人才,会选择“带薪培训”的模式。医院支付费用,医生获得深造机会,看似互利,实则暗藏风险。一旦签下协议,医生的职业选择权便被限制多年。 唐某的案例提醒所有年轻从业者:任何“好机会”,都可能伴随“沉重代价”。 医院的愤怒,可以理解;唐某的离开,也非全然无理。八年服务期,对一个年轻医生而言,意味着职业选择几乎被封死。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下,基层待遇与成长空间的确有限。 法律约束能留住人,但留不住心。当制度与激励脱节,违约金就变成了“铁笼”,而不是“保障”。 很多专家指出,人才政策应当以吸引力为核心,而非惩罚性约束。基层医院要想真正留住医生,靠的不是合同条款,而是合理的薪酬机制、晋升渠道和职业尊重。 这个案件的判决,既是对契约精神的肯定,也是一记警钟。它告诉年轻医生:签约之前要看清每一条款的后果;也提醒医疗机构:培养与留人并非靠惩罚,而在于制度优化。 唐某的60万元,或许不仅是一笔违约金,更像是一堂昂贵的法治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