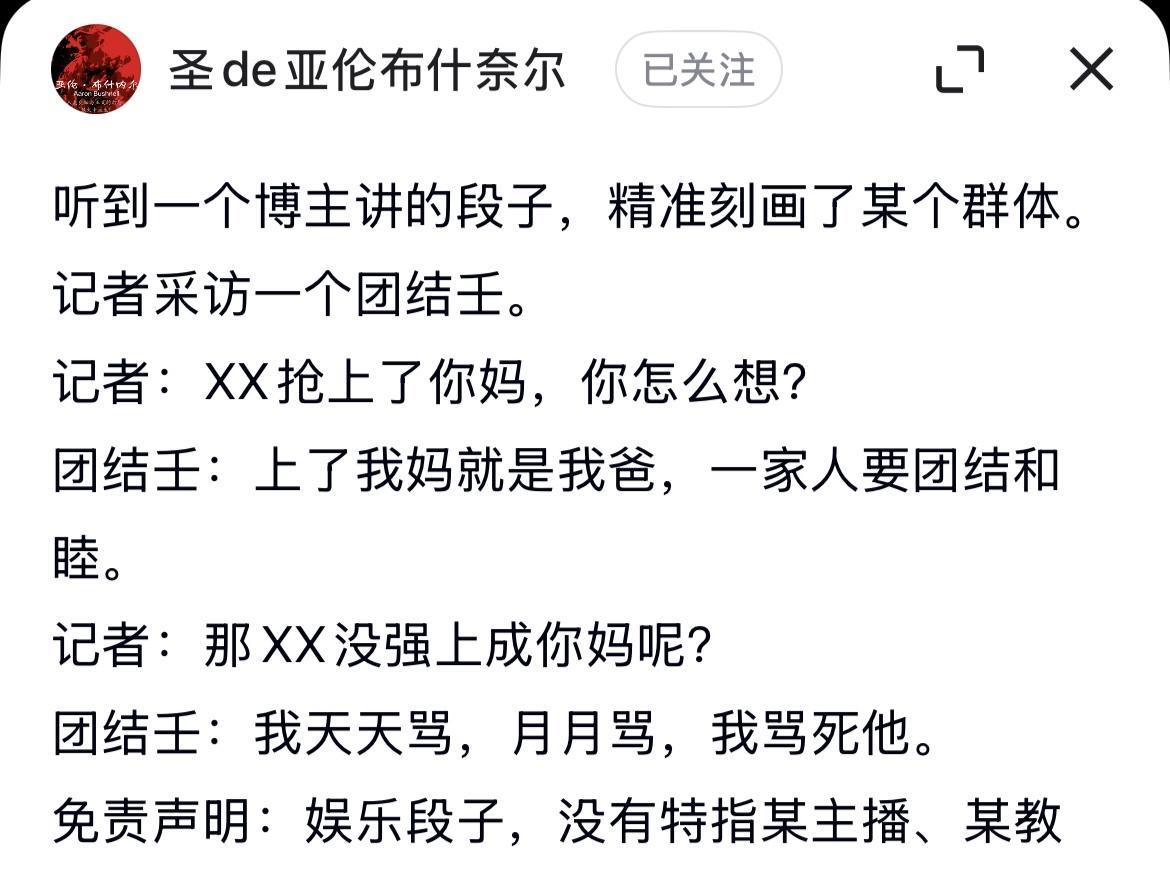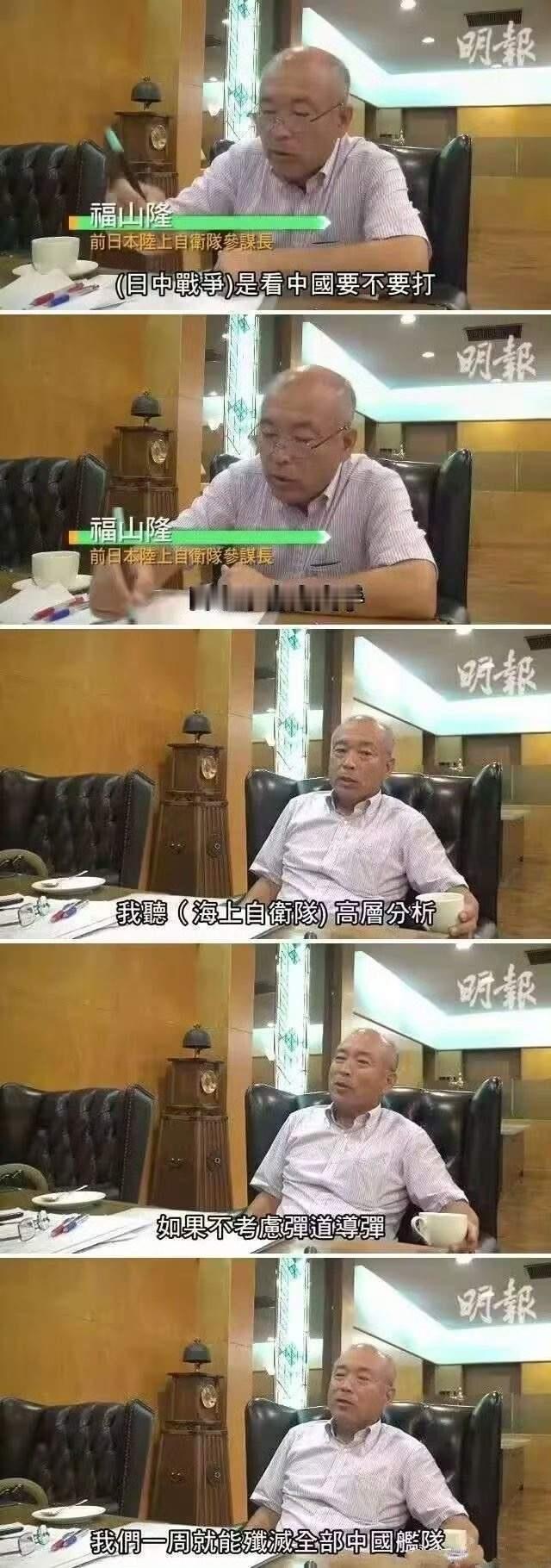1949年,国民党中将刘昌义去找汤恩伯时,忽然听见蒋纬国的声音传来:“副座,我当连长时就认识你了,现在家父处境难,还得靠副座您这样的西北名将帮忙啊!” 那年5月22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走廊里,刘昌义正准备敲汤恩伯办公室的门。 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声音还挺熟:“副座,还记得当年在西北军、打台儿庄那时候的事不?” 刘昌义转过身,看见是蒋纬国。蒋纬国穿着笔挺的军装。这位总说自己是 “连长” 的蒋家二公子,这会儿眼里的焦虑,跟他的年纪一点不搭。 蒋纬国接着说:“现在家父处境难,还得靠副座您这样的西北名将帮忙啊!” 刘昌义听了,只淡淡笑了笑,并没有立即给出答复。 他心里很清楚,这 “帮忙” 根本是让他带第 51 军 —— 这支本来就不是嫡系的杂牌军,去苏州河北岸当 “肉盾”,给汤恩伯的嫡系部队撤去吴淞口争取时间。 那时候的上海,早就形势不对劲了 —— 能隐约听见解放军的炮声,苏州河南岸的老百姓正慌慌张张收拾东西。 而国民党守军的士气已经尽了。 当天深夜,汤恩伯在密室里偷偷弄他的撤退计划。这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心里清楚大势已经没了。 他立刻命令亲信陈大庆、石觉,带着嫡系的第 75 军、54 军这些部队,连夜撤去吴淞口。 至于第 51 军,这支刚重建没多久、军长王秉钺又被俘虏的部队,就被 “安排” 去守苏州河以北的防线。 陈大庆拍着刘昌义的肩膀,假笑着说 “辛苦刘将军了”,然后就赶紧登上往吴淞口去的军舰。 刘昌义站在指挥部的窗前,看着夜色里隐约能看见的苏州河。 他比谁都明白,这所谓的 “防线”,就是汤恩伯扔过来的烫手山芋。 但他心里早有别的打算 —— 早在几个月前,他就通过民革的元老李济深,跟中共上海地下党接上了秘密联系。 现在就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准备了好久的起义办了。 第二天早上,刘昌义以 “稳定军心” 为理由,把 51 军的高级军官都叫到北四川路赫林里。 会议室里,几个参谋长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愿意接这明摆着 “必死” 的差事。 刘昌义见这情况,突然站起来掀开地图,手指重重戳在苏州河北岸:“各位知道不?共军已经过了南翔,汤恩伯的军舰正往吴淞口开呢!” 这话一出口,满屋子人都惊住了。 他接着抛出重磅消息:“我已经决定了,带部队起义!各位愿意跟我,就马上准备;不愿意,也可以自己找活路。” 这话跟炸雷似的,在座的军官都愣了。 21 军的参谋长最先开口:“与其当替死鬼,不如拼条活路!” 其他人跟着纷纷同意。 刘昌义马上派副官刘凤德,通过地下党员田云樵,秘密联系解放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的政委罗维道。 为了防特务盯梢,他特意让刘凤德绕路去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 —— 那里就是解放军的临时指挥部。 同一时间,解放军这边也在为和平解放上海做最后的努力。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早就定了 “瓷器店里打老鼠” 的规矩,要求部队尽量不用重炮,别把城市毁了。 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接到任务后,马上想到找王秉钺的同学王中民去劝降。 他可不知道,这时候 51 军的军长早就换成刘昌义了。 5 月 25 日天刚亮,王中民举着写着 “和平谈判” 的白纸板,一个人闯进国民党的阵地。 子弹在头顶嗖嗖飞,他却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 因为他身后,是成千上万上海市民的安危。 等他被带到刘昌义面前,两人对视一眼,居然一起笑了:“老弟,你晚了三天啊!” 原来刘昌义早就通过地下党知道了王中民的身份,这次见面,就跟天意似的。 谈判从早上一直谈到下午。 刘昌义提的条件很明确:保留部队编制,保证官兵安全,保护上海的工厂、学校不被战火影响。 解放军代表罗维道则强调,起义和投诚不一样,关键看是不是主动。 谈了三个小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刘昌义带部队撤出苏州河以北的阵地,解放军接防,并且保证他们部队能安全改编。 当天傍晚,刘昌义亲自去了虹桥路二十七军的军部。 第二天凌晨,51 军两万多人往江湾开,官兵都把枪口转了方向。等解放军进北岸时,没看到战场,只看到百姓摆的茶水摊。 这场看着突然的起义,其实早有准备。 刘昌义早年跟着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时候,就跟共产党员宣侠父来往密切,对共产主义早有认同。 抗战期间,他更以 “假意投敌” 之计,歼灭日伪军六百余人,洗刷 “汉奸” 骂名。 此次起义,既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更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情守护 —— 他深知,若强行抵抗,不仅部队覆灭,更会让这座东方明珠沦为焦土。 历史证明,刘昌义的选择是明智的。 上海解放后,原 51 军官兵多数加入解放军,参与保卫大上海的各项建设。 而他本人,则在 1950 年代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服务人民。 1994 年,这位传奇将军以 89 岁高龄辞世,临终前仍喃喃道:“那日的苏州河,映着夕阳,真美啊……”